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我主要讲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我关注的最大的风险是什么;第二个风险的根源是什么;第三个怎么化解。
最近出现股债汇三个金融市场的联动,恰恰是这样的联动,让我们看到更多的系统性风险的隐患的源头。
最大的根源,就是来源于二次大战之后建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失序。已然高度全球化的现在,需要加强全球经济和政策协调的情况下,协调的机制却失灵了。新的协调机制短期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来,是因为缺乏信任的基础。
对全球的协调机制,要保持开放态度。化解办法有两个,一是政策还是市场都要转变思维;二是我们要更加重视第三产业的供给侧的改革。
未来可能面临的情况是,经常账户顺差没有了,可能还会出现逆差,未来资本账户在中国的国际收支中的影响会不断上升,这将在未来至少带来5个思维变化。
第一,汇率要变得比过去更灵活,需要和利率协调推进。
第二,资本账户的开放。我们看到更多的国际投资人对中国的资本市场越来越有兴趣,他们对于中国资产的配置低于目前中国在全球的配置,趋势上有增配的需求。国际投资人更多地进入中国市场,从而为缓冲我们在国际冲击面前的压力提供了基础,资本账户的开放和国内资本市场的改革要跟上。
第三,货币发行机制要跟上。我们本币的资产抵押品,利率品够不够,如果利率品不够怎样让信用的产品能够更便利地成为抵押品。
第四,央行抵押品的机制要改变。
第五,货币中介目标的变化。从单纯数量方法的调节,转到数量和价格并重的调节。
2012年之后第三产业的增速非常稳定,一直都在7%以上,好的时候还可以在8%左右。这就意味着我们能够以供给侧改革的思路,更多释放第三产业的潜力,中国的经济就能够比现在更容易稳住,也不需要你以更多的财政办法去解决它。科教文卫领域现在还有很多还叫事业单位,不叫企业。靠财政拨款不以赢利为目的,这也是政府负担比较重的原因。如果让一部分这类企业更多地市场化,那么政府的负担得以减轻,市场的潜力得以释放,中国经济也能更好地稳定。
(作者系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本文摘编自作者5月26日在以“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开放”为主题的2019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的发言)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鲁政委世界观 ”微信公众号
文章作者

打破“西方垄断”!农夫山泉进入2025全球软饮料品牌价值排行榜前三

“跑鞋界苹果”仅用两年实现业绩翻倍,但品牌高速增长背后也有隐患
On昂跑在中国市场表现强劲,公司通过“欧美稳健增长,亚洲高速突破”的全球化策略实现业绩快速增长。不过,从业绩来看,光鲜背后是增收不增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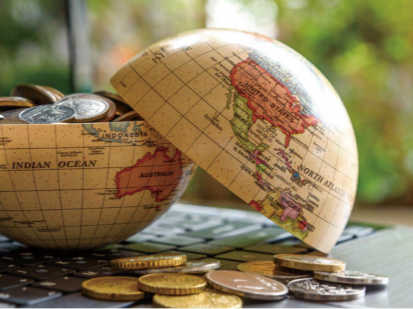
特朗普冲击下的全球化何去何从
相比于过去的“意大利碗面式全球化”,今天我们面临更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和更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全球化的碎片化趋势可能正在向着更具封闭性、分化特征的方向升级。

730政治局会议的八大重点信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如何理解近期资本市场?建议把握好风险收益比
面对短期风险资产的快速上涨,建议投资者理性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