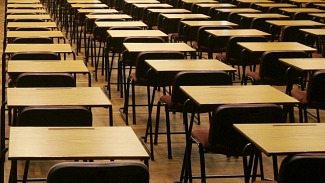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aisd}}
AI生成 免责声明
“华盖建筑师事务所”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在民国时期,“南华盖、北基泰”是中国建筑设计机构的南北翘楚,代表了“建筑海归”一代的声望。其中,基泰工程司由关颂声1920年创办于天津,杨宽麟、杨廷宝、朱彬等先后加入,现存代表作有天津市百货大楼、上海第一百货等;华盖则由赵深、陈植、童寯于1932年在上海创办,以合伙制运作,现存代表作有上海大上海电影院、上海黄浦剧场、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旧址等。
对建筑专业人士而言,这些前辈建筑师的业绩闻名遐迩,他们对中国建筑业现代化转型的贡献有目共睹,他们的经验和思想以建筑作品、教学方法、行业准则、文化遗产、文艺作品乃至逸闻传说等方式流传至今。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建筑师在一般公众的历史记忆中,却是一个相对次要的角色。提起建筑师,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就那么几个:古代的鲁班、李冰、“样式雷”,近现代则不外梁思成、林徽因、贝聿铭等。
也许是建筑曾被认为只是一种专业技术,不像一些广为人知的科学研究的战略性那么强;也许是建筑自身比较复杂,建筑师工作的细节比较难被人们了解;也许是建筑师们恪守专业精神和“乙方姿态”,较为低调,缺乏“星味”,留下的史料不多且不成系统……总体上看,对近百年来中国的国家发展与城乡建设曾起到过物质奠基作用、在清末民初学成归国知识分子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现代中国建筑师们,“露脸”的机会不多。

《烽火中的华盖建筑师》
张琴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21年8月
《烽火中的华盖建筑师》是难得地为那一代建筑师“说话”的小书,以华盖建筑师事务所的三位合伙人赵深、陈植、童寯为主要对象,兼顾同时代的其他建筑师及相关人士,从1920年代写到1950年代。时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先后展开,烽火连天之际,华盖建筑师们天各一方,赵深立足抗日大后方云南昆明开展新业务,陈植留守上海维持本地项目,童寯投身于紧张的抗日工业建设工作,并在贵阳运营分所。
他们一方面坚信中国必胜,主动参与抗战,克服艰苦条件和巨大的不确定性,先后设计了百余栋各种功能的建筑,包括住宅、学校、工厂、办公楼、文化设施等,并设法维持事务所的存续;一方面被动应对战时的动荡,忍受与家人的分离之苦,在复杂的人际交往中与各方势力保持合理的距离,抽出精力甚至付出财力指导学生、后辈,与其他建筑师和学者们共同推进中国建筑学的研究和传播工作。
站在数十年后的视角回看,“二战”的特殊时代背景给了我们更好地看待华盖建筑师及其同代人的角度,“华盖三杰”的事迹也能够吸引我们再一次认真细致地了解那个年代。《烽火中的华盖建筑师》一书以区区200页的短小篇幅完成了启发式的叙述,作者张琴坦言写这本书是“做笔记”,很多内容都来自建筑史研究、寻访知情人、阅读资料、查找和比对档案的漫长过程,一边探索一边记录。
张琴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师从阮仪三教授,多年从事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古村落调查等工作,现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合作研究员。她的丈夫童明是童寯之孙,现为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创办了梓耘斋建筑工作室和织城网络。张琴的第一本书《长夜的独行者:童寯1963-1983》就是以童寯最后20年的工作和生活为主题,《烽火中的华盖建筑师》延续前作风格,有一定的“前传”色彩。
书中写到的一些事件,张琴也并非事先知道,而是在阅读、记录中偶遇。比如全书开头所写的1941年3月昆明大逸乐影剧院坍塌导致重大死伤案,因社会影响巨大,由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亲自下令严厉追责,直接导致赵深入狱、被追回设计费并处以大额罚金。如张琴在书中所分析的,该案对赵深的处罚明显过于苛刻,可能有当时社会舆论的特殊原因——次日发生在重庆的隧道惨剧引发“举国同悲”,赵深是因氛围被迫“背锅”;而昆明大逸乐影剧院和重庆隧道的事故都是由日军飞机轰炸导致,赵深曾多次主动查看大逸乐影剧院的受损状况,第一时间拿出修复方案,影院老板不愿停业出钱整修才是酿成大祸的真正原因。

赵深负责任的举动铁证如山,很快为他赢得了声望,此后反而为他带来了云南省内的大批项目委托,龙云和时任滇南边区司令卢汉都很认可他,先后多次成为他的委托人。华盖和赵深的名望,就像这次影院坍塌事件一样,在烽火年代与大后方地区紧紧地绑在一起。可惜的是,由于后来的历史变迁和城市建设,相关的记录并不多,很多建筑也因地块改造而消失,或因转换用途和业主等而变得面目全非,建筑师的事迹和他们所经历的种种沧桑也随之封印。
童寯是中国现代建筑师中非常具有思想性的一位代表性人物,他一辈子都执着于研究,不仅有高超的设计技巧和卓越的绘图能力,也是学贯中西、重视著书立说的专家。在华盖,童寯长期负责图房,是技术负责人。当然,赵深、陈植与童寯同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优秀学生,他们非常认可彼此的水准和风格,在合伙共事期间虽因性格、专长不同而各有侧重,但技术共识是他们的基础。一个项目无论是三人中的哪一位具体做的设计,他们都共同署名。童寯担任过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教授,长期搞学术研究,在园林方面有《江南园林志》等多部代表作,对古建筑研究者和爱好者来说都是必读。但在《烽火中的华盖建筑师》一书中,我们能看到童寯的另外一重风采。
在“苦与乐其实是一回事”这一章中,张琴写了1938年童寯应叶渚沛之邀去重庆,先后设计了多座战时工厂的不凡旅程。叶渚沛是海外华人、冶金学家,时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冶金研究室主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回国工作,曾任中科院化工冶金研究所首任所长。资源委员会原为“国防设计委员会”,负责重工业发展和工矿企业管理,下辖121个总公司、近1000个生产单位,涵盖钢铁、有色金属、机械等十余个工业部门,在抗战期间实际成为国民政府的最高经济领导机关,以统筹建设、推动生产的方式为抗战“输血”。
华盖与资源委员会早有合作,于是童寯接受叶渚沛的邀请,两人在香港会合后辗转多地,驾车飞驰千里抵达重庆。童寯先后完成了化龙桥重庆炼铜厂工房、四川綦江纯铁炼厂工房、四川资中酒精厂工房。这些工厂快速投产后,对抗战军需物资起到重要的支持作用,对我国后来相关工业的研发与生产也有重要意义。
其中,留德化工学家张季熙主持的资中酒精厂生产的“无水酒精”供给中国空军用作战机燃料,直接助力抗日,尤其是在沿海港口被占领、滇缅公路被切断失去外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以求打通大陆交通线等特殊的战争态势下,对孤岛般的大后方维持战事而言,可谓金子般珍贵。
童寯当时的工作环境艰苦而危险,他的工作场地经常很偏远,工程能使用的材料也相对简单;他在重庆的居所里空空荡荡,仅靠两三张绘图桌、一支笔、一张纸而全力以赴地画着。有的建筑师在执行相似的任务时遭遇空袭殉国。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人则不断地被迫迁居,大多要在贫苦中坚持工作,有人则要忍受病痛。
以华盖为代表的这一代建筑师,往往都出身于较好的家庭,受到正统、规范的欧美建筑教育之后,怀揣专业理想与振兴国族的抱负回国创业,无论工作还是教学,面对业主、同行、学生或是公众,他们都以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思想格局来要求自己。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战火、社会动荡及历史的考验先后无情来临,最重要的品质仍要全力以赴去坚持,尤其是对工作抱有热情,对家人亲友真诚地施爱。对于时代变迁带来的一切不确定性,他们以建筑师之名,去勇敢地承受未来才会降临的公允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