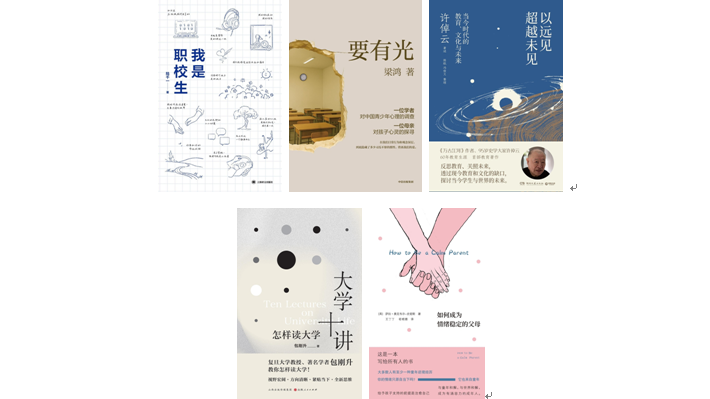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aisd}}
AI生成 免责声明
Q1:中国的教育是以公立教育为主,但是公立教育的资源配置是基于身份的,农村户口只能接受农村教育,城市户口才能接受城市里的教育。这就天然地会带来城乡教育巨大的不平等。基于这样的资源配置设定,如何才能缩小城乡的教育不公平?
Q2:中国人口除了生育率不断下降,年出生人口从20年前的2000万掉到现在的1000万,同样有一个城乡差距问题。如果解决城乡不平等的办法是增加对农村的教育,这在未来会不会成为浪费?因为农村人口出生率也在下降,同时还有城市化率提高,人口不断进城,怎么既协调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又避免未来的浪费?
姚洋:两个问题都是关于城乡差距的。中国是以公立教育为主,要缩小城乡差距,当然还是得国家想一些办法。
第一,我觉得应该取消按照学校的归类拨款的机制,这本身就不公平。为什么农村的学校归为四类,拿到的生均费用就低?按理说应该拿到的更高一些才对。
第二,应该加大对到农村教书老师的工资奖励,提高他们的收入,让他们能够安心在农村教学。有些省份做得不错,比如说北大对口扶贫的云南省弥渡县。我们去看了一些学校,学校里很多老师非常安心,就是因为云南省对老师的工资是100%保证,而且工资水平相对较高。这是很好的榜样。
关于现在的投入将来会不会造成浪费,我觉得中国已经过了(要开办更多学校)那个阶段,现在再到农村开设新学校肯定会造成浪费。农村学校数量在过去20年大幅下降,基本上十几、二十里范围就一所中心小学,孩子们三年级以上都住校,所以目前并不存在校舍浪费问题。目前人员的问题也一样不用担心,人员可以流动,如果这里不需要老师,就调到别的地方。总的来说,当前还不存在对农村教育投入的浪费问题。
Q3: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的高校、985高校与三四本高校的拨款机制确实问题比较大。现在所谓的鼓励双向流动,其实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优秀师资的流出更大,流入很少,造成贫富地区的教学资源更不均衡,这应该怎么解决?
我们去对口扶贫地区云南弥渡县调研,发现这里尽管是贫困县,但教育内卷也非常激烈。我们跟县委书记交流,他说自己现在最大的压力来源不是扶贫,而是教育。因为弥渡周边的大理州出现了几个规模较大的民办中学,高收费,给教师付的工资很高,这样就开始出现“掐尖”现象,这些学校把周边各个县的好学生都“掐”走了,本县的教师资源也流失严重。
这种“超级”学校的出现,尤其是对于农村地区的教育是致命的。好学生都走了之后,中等学生就变差了,因为剩下的学校不太可能有学生考上985的高校,要想考上,就得去超级中学,但家里没钱,也就没有希望。
所以这位书记最想提给我们的任务是能不能从北京引一个好中学过去。但我们都知道,如果这么做,等于在这个县里又造成一个新的不均衡。事实上,绝大多数孩子还是只能上一般的学校。
所以,我们恐怕要在思路上做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中小学最好去除选拔机制,实施平均化教育。这个目标并不是不可实现,日本就做到了。美国基本上也是这样,除了极少数的私立中学,美国不少州都把公立的、选拔性的高中全面取消。
我认为,高中之前的均等化教育应该成为中国的发展方向。
如何定位和发展民营大学
Q3:我想提的问题是给姚洋老师,现在对于民营大学的政策好像又要有变化。请问在解决教育问题的过程中,民营大学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姚洋:这些民营大学在过去20多年的的确确对公立大学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但因为从国家那里得到的支持很少,所以收费不得不弄得很高。现在高收费的学校基本上是这一类,还有就是三本。
我在想,如果要有一个根本性的改革,恐怕还是要调整高校的学费系统。学费最终应该反映学校的教学质量,然后通过奖学金制度来奖励那些贫苦家庭的孩子,这样才能把关系捋顺。去上那些三本、四本的学生大多来自贫困人家,为了让孩子去读大学,必须交很高的学费,其实是对这些家庭的双倍打击:不够好的教育+高昂的价格。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但我自己有亲身经历,一个亲戚的孩子就因为学费原因不想上大学。那是十多年前,一年的学费就要2万多,这孩子就想去广东打工,后来我让他回来读了大学。虽然只是大专,但也非常管用,他如今在城市里生活得很好。我们可能并没有注意到这些事情,但实实在在地说,这个群体并不是很小,很多农村和城市贫困家庭的孩子因为学费太高而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
如何看待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
Q4:我想请教关于职业教育的问题,姚洋教授最近经常谈到中考分流问题。国家这几年在大力推行职业教育,“职业教育20条”也对此有了定性,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今年我接触到一些人,他们说国家已经强制执行一种政策,即中考之后学生五五分流,一部分上中专,一部分继续接受普通高中教育。有些地区甚至只有30%的学生能进入普通高中,70%要走职业教育。
请问老师们对于职业教育现在的发展、国家执行的政策以及人才教育公平方面的看法。
姚洋:对职业教育,我本人还没有相关研究。我们马上要做有关中考分流的研究,会去保定考察。总体而言,我觉得14岁就让孩子分流的做法不好,特别有些地方还三七分流,更不应该。
现在的大学入学率已经接近60%,却先让70%的孩子连读高中的机会都没有,这不合理。很多人都说德国从10岁就开始分流,我们应该学德国。其实德国的制度在其国内并不受欢迎,也有很激烈的争论。
但德国为什么还能坚持分流?有两个原因:
第一,德国保守势力太强大,他们坚持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觉得10岁的孩子就能看出来;
第二,德国的职业教育是真正的职业教育。我去德国看过,那些学生两天在工厂里学习,其余三天还在普通高中里读书,依然在接受高中教育。而且做了工人以后将近一半的人还能再考上大学。如果我们真要让孩子们早一点分流,要学德国,那就学到底。
中国今天的分流是让孩子们早一天做工人,以后还能读大学的比例极低,而且绝大多数人做了工人以后不想再考大学,因为他们全要靠业务时间学习,太难了。这是对人才的浪费。在我看来,14岁就让孩子分流不可取。
有人说,中国现在需要大量的工人,所以要加大职业教育。其实我们现在对这种简单劳动工人的需求并不大,很快会被AI替代掉。未来的工人至少要能开数控机床,要有大学毕业证才能做到。
因此,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中考的分流都是不对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