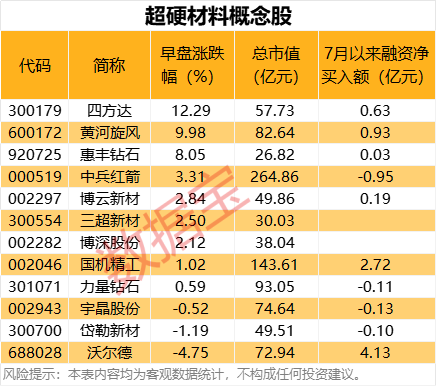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aisd}}
AI生成 免责声明

本期嘉宾:
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如何应对稳增长挑战?
第一财经:稳增长是今年经济的关键词,稳增长的思路是什么?
刘尚希: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提供了一个整体的思路,要针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这三重压力做文章。这三重压力是一个整体,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实际上相互影响,要让它们形成一种良性循环,避免负反馈。如果负反馈,相互影响,相互收缩,下降得更快,而正反馈就是相互促进,这样经济就增长起来了。核心的问题就是预期,预期转弱不是一下子造成的,有一个积累的效应,也有多方面因素的叠加。所以要扭转预期转弱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但从民营经济的角度来切入会有很好的作用。
第一财经:您认为关键的切口应该是民营经济?
刘尚希:对,因为民营经济在整个经济中占比很大,而且是就业的主渠道,就业影响收入,收入影响消费,消费影响内需。新的增长点更多是在民营经济。怎么稳定民营经济的预期?不仅是市场的预期,还有舆论的预期。对民营经济不要戴“有色眼镜”去看,“两个毫不动摇”要落实到体制上、机制上、政策上,落实到政府各个部门的行为上,也落实到舆论导向上,多方面发力。如果民营经济有信心了,也就是说广大人民群众都愿意创业了,都愿意去积极地配置资源、创造财富,老百姓的话都愿意去发财、挣钱,这个经济就活起来了。人民群众有积极性了,何愁经济不增长呢?
稳增长,财政政策如何发力?
第一财经:今年稳增长,财政政策可以从哪些方面发力?
刘尚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有一个共同的条件,就是有效性,也就是乘数效应,或者讲杠杆效应,老百姓说的“四两拨千斤”,就是取决于预期要改善。如果预期不改善,政府冲在前头,后面没有人跟进,政策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如果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说采取措施了,那等于说跟打仗一样“同志们冲啊”,后面跟着上来了,那肯定打胜仗。政策有效性,首先一个大的条件就是预期改善。在预期改善的条件下,怎么实施好财政、货币政策很重要。财政政策现在大家期待很高,一方面是规模性、组合式的减税降费,另一方面还有政府的投资、公共消费、人力投资。首先还是要从统筹财政资源上下功夫,花钱的部门很多,每个部门手里可能掌握一点钱,有时候就是撒胡椒面,这样的话就形不成合力。要把预算资金统筹,比如说四本预算,至少三本预算,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要统筹。在统筹了这个的基础上,对支出结构要优化、要调整,这对提高财政政策的效率是至关重要的。支出结构的调整也牵涉到各方面利益,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也需要改革来推动。要有风险思维、风险意识。所以财政政策强调超前发力,要跑到风险的前头。跟打仗一样,你知道敌人在哪儿,如果敌人在哪儿都不知道,乱放炮,那不是浪费子弹吗?这个时候要精准分析。
第一财经:要精准防范风险,有具体所指吗?
刘尚希:认知水平的提高,尤其在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对风险的认知是关键。政府怎么防范化解这些公共风险,降低宏观的不确定性,这个至关重要。其实所有的政策都得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乘数效应、杠杆效应才会出来。不是说政府去上一些项目,上一些大项目,经济增长就会稳住了。在110万亿经济体量下,政府几万亿怎么能稳住经济?所以政府的钱实际上是一个引子钱,引着其他的钱、其他的投资跟进。就像抽水机一样放点引水,然后再一带动,这个水“哗哗哗”就跟着上来了。财政的钱就像过去老式抽水机搞引水是一样的道理,你要启动它。
基础设施投资如何“适度超前”?
第一财经:今年以来,我国各地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它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是怎么样的?
刘尚希:过去讲“超前”是讲社会基础设施要先行,要适当快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才能够为国民经济发展创造条件,比如说高速公路。在新的条件下,就是宏观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这个“超前”的含义实际上变了。比如说基础设施建设落到项目上,跟规划,跟人口的布局分布、人口的流动关联在一起,不能静态地按照过去传统地理的概念,不考虑人去分布这些项目,那可能导致不是超前,而是可能滞后了。
第一财经:您认为人是一个关键?
刘尚希:对,要跟着人走。比如市民化,更多的人进城,有更多的学校、医院的需求,要提前布局。等到市民化,农民进城了,就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如果人进来了,需求满足不了,赶紧去搞这些公共设施的建设,这就是晚了,就没超前。还有一个是数字化。传统的基础设施要转型升级,再重复旧的,拿着旧传票去登船,估计是登不了船了。发挥不了作用,纯粹浪费资源。所以现在要发挥超前的作用,必须要瞄准数字化这个大的趋势。新基建很多是虚拟的。比如数据库、各种数据中台、城市大脑,实际上都是在虚拟空间里。这些建设要完全靠政府是办不到的,必须是政府做规划、指方向,更多是靠市场。在疫情防控中那些健康码之类的哪儿来?实际上很多企业已经搞起来了,所以数字基础设施离不开民营企业。不断技术迭代,然后得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政府更多的是在规划,要创造条件。让大家规划可预期,政策可预期,政府讲的话可预期,在这种条件下,大家就有信心去干了。条件创造了,我想增长自然就稳住了,经济自然就活了,创新也就出来了。总有一些企业是有些战略眼光的,会去超前布局,他们可能看得比政府还远,5G不是说政府规划出来的。其实市场的力量就是人民群众的力量,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所以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那不就实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发展最终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当前的经济政策真正依靠人民群众,这些政策的效果就能发挥出来,就好办了。
如何提升减税降费的效果?
第一财经:近几年来,减税降费的举措力度是比较大的。但还是有很多企业感觉到压力很大,成本很高,如何提高减税降费政策的效用?
刘尚希:这几年一直都在减税降费,但是大家感觉到成本压力很大,为什么?企业的成本压力不仅是税收,原材料价格、其他各种不确定性,比如疫情带来的成本,减税降费很难一下子就对冲的。还有比如“双控”、减污降碳、绿色低碳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标准不断进行调整,导致企业的沉没成本很高,要重新搞。其实企业的成本压力是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转化而来的,加上现在老龄化,人工成本也在上涨。但是政府努力在想办法,减税降费就是想办法想得最多的,也是时间最长的,力度也是最大的,来给企业减负,应该说效果也很明显。这个明显就是说宏观税负是在下降的,看得出来它没有加重,2020年的宏观税负只有15.2%,15.2%在全球来比都是偏低的,至少这些年每年都在下降。成本压力来自于方方面面,不能单靠减费降税,其实还有金融,怎么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如果流动性出问题,一个好好的企业一口气上不来就憋死了。财税方面的减税减负,这些年应该说下了很大功夫,怎么跟其他方面的政策形成一种协同效应,实现“1+1>2”?所以政策的协同在当前来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房地产业改革要抓住哪些关键环节?
第一财经:房地产行业上下游产业链非常长,对于经济稳增长,对于地方政府的税收影响还是非常巨大的。在转型期,房地产行业应该承担怎样的角色?
刘尚希:房地产改变了几个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变了,企业的资产里有不少就有房产、写字楼。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变了,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变了,有人做过调查说居民的资产80%都是房产,居民的负债好多也是与房子有关,比如按揭贷款。它还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地方政府的负债有的就是通过土地融资。房地产业的发展深度切入到企业、银行、居民家庭和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之中,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稍有变化,对哪种资产负债表,实际上可能都是不可承受之重。就像一个大的复杂的外科手术一样,房地产业的转型发展就必须要审慎。你看看哪根神经、哪根血管,要摸清楚了。所以首先顺着资产负债表的脉络去理房地产业,它到底带来什么样的问题,风险在哪儿。
更大的问题要放在更大的范围上去考虑。住房商品化改革是城里进行的,发展到今天,毫无疑问应该把农民考虑进来。首先要把农民工考虑进来,然后把在广大农村居住的农民,他们的住房怎么市场化再考虑进来。住房制度改革的视野要扩展到全体,而不能再仅仅就城市的住房来谈房地产业的发展、转型、升级。现在的改革要触及农村、农民,要从全民的住房制度改革的角度去考虑,去深化产权制度改革,解决国有土地、集体土地二元所有制的鸿沟,进一步解决生活在集体土地、国有土地上的这些社会成员的社会身份的不同,以及带来的权利和义务的不一样。这是一个更大的题目,但是必须要做了。共同富裕的命题提出来,就意味着这是绕不过去的。如果仅仅通过一些政策,可能解决的是一些眼前的问题,解决的是运行平稳的问题,但真正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还是要以改革的办法来解决积累的这些问题。有的是经济改革,有的是金融改革,有的是财政改革,有的是社会改革。也就是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真正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那我们就更有底气了,所以还是怎么样利用现在的机会、良好的环境加快发展,这是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