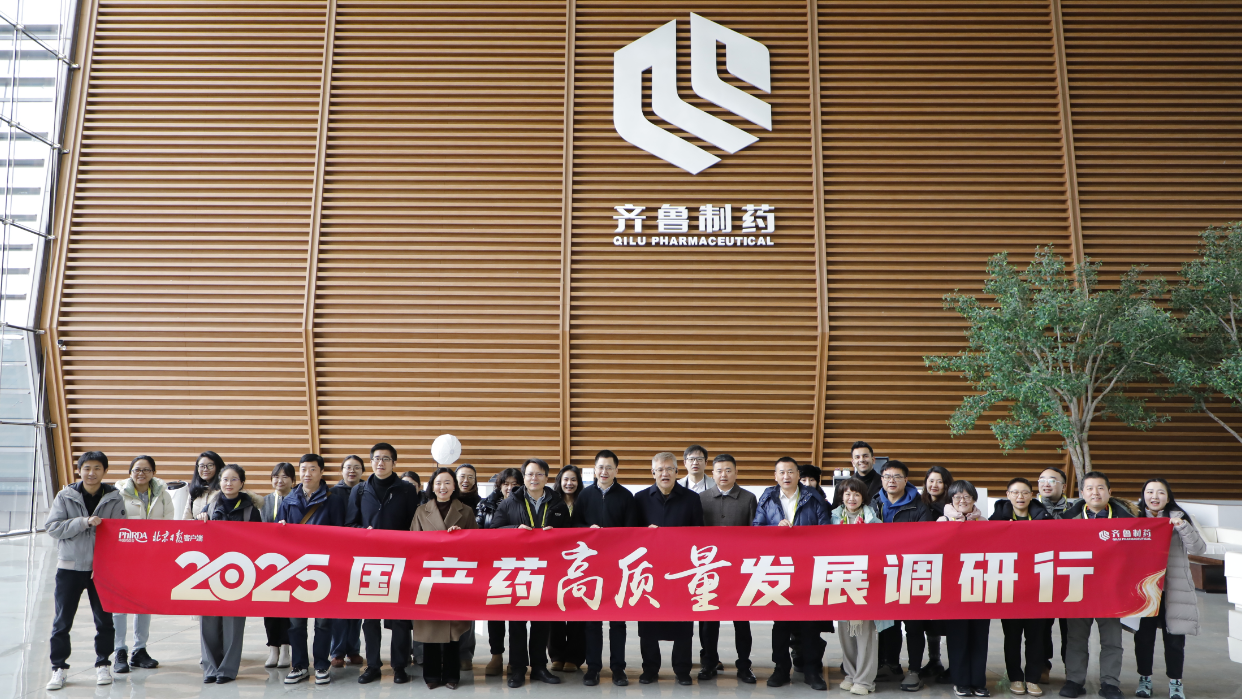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aisd}}
AI生成 免责声明
国家药监局近日在部署2025年药品监管工作时明确,要对集采中选药品、委托生产药品等重点领域加强“风险监测和稽查执法”,与此同时,将“加快构建全国一盘棋工作机制”。
但在现有的药品监管体制下,全国监管一盘棋的实现无疑颇具挑战。我国现行药品监管体制为中央和地方分级的属地化监管。长期以来,省际以及省、市、县三级药品监管部门之间存在机制不健全、衔接不紧密、能力差异大等问题。
“在一个强有力的监管体制下,哪怕是属地化管理,也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但问题在于,尽管中国拥有比欧美多国更严的药品监管法律法规,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长期存在。这些问题在属地管辖中被放大。”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昊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称。
他还提到,目前,社会公众对于仿制药的理解有一些误区。其一,通过一致性评价仅仅是确保仿制药有效、安全的最基础的标准;其二,“原研药药效优于仿制药”的说法没有依据,但需要正视的是,原研药企可能是对该款药品生产工艺“理解最充分”的企业;其三,一款仿制药过评,或某批次生产的这款药依据真实世界数据证明与原研等效,并不足以为该制药企业的生产“背书”。目前,国内部分制药企业包括一些规上企业,仍缺少高标准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体系以及监管自律。
全国药品监管“一盘棋”的掣肘
建立药品监管“全国一盘棋”,并非一个新提法。
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力建设的实施意见》。为健全国家药品监管质量管理体系,该意见明确,要落实监管事权划分,形成“药品监管工作全国一盘棋格局”。其中,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落实药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与此同时,创新完善适合药品监管工作特点的经费保障政策,通过专项转移支付支持地方药品监管工作。
“一盘棋”意味着执棋者需要统一标准、协调地方资源,也意味着局中棋子要摒弃地方保护主义。而前述条件的达成,在陈昊看来,并不容易做到。
“比如,如何处理央地关系,划分事权责权?如何匹配地方资源,让各地具备相近的监管能力和行政环境?这些问题都悬而待解。”陈昊说。
陈昊认为,之所以我国药品监管体系还没有达到公众普遍信任的程度,问题并非出在药品标准上。近些年,无论是《药品管理法》还是《药典》都几经修订,我国药品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已经高于欧美很多发达国家,GMP(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良好生产规范)标准也已力争达到与海外同步的水平。
“关键问题在于缺少执行标准。”他进一步解释说,现阶段,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药监资源均存在严重不足。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改药品生产的一次性监管为动态监管,即取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认证和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认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随时对GMP、GSP等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尽管政策初衷是好的,但地方监管能力难以相匹配。
“而企业缺少诚信自律又进一步放大了监管不足带来的风险,导致药品生产中的风险叠加。”陈昊表示。
2019年《药品管理法》修订后,明确全面实施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MAH)制度,但在陈昊看来,我国MAH制度步伐迈得可能有些快。
回顾来看,较多B类药品生产许可证持有人此前为研发企业、经营企业等,这些企业或存在质量管理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如若药品持有人涉及跨省委托生产时,生产监管风险可能再次加大。
“理论上,药品生产的最终责任主体为持证人,共同责任主体为委托企业,而持证企业和委托企业应该分由各自的属地药监部门监管,这就会涉及跨区域监管协调。受地方经济利益、产业发展等因素影响,属地保护主义难以消弭。此外,持证企业和委托企业也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等和能力不对等的问题。”陈昊说。
陈昊认为,当谈及属地监管时,一个重要前提是中央监管资源无法覆盖需求。但从市场需求来看,中国未来可能仅需要三、四百家仿制药企。随着医药产业集中度提高,监管部门有能力做到垂直管理,而垂直管理可以更大程度上规避地方保护问题;如果维持现有监管体系,相较于其他采取属地管辖的行业,我国制药企业规模整体可控,且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持下,地方监管效能逐渐提升,“全国一盘棋”的目标虽难但亦可实现,目前应尽快形成共识并拿出方案。
如何确保集采仿制药高水平安全
当前,社会公众对于药品生产质量和疗效的担忧主要集中在国产仿制药上。
主流业界观点认为,仿制代替原研,是全球的总体趋势。在中国,纳入集采的仿制药,前提是通过一致性评价,后者为确保仿制药有效、安全的关键措施。重点需要关注的是,仿制药企是否在内卷中存在非理性降价,以及中选降价后,能否维持药品质量稳定并确保生产合规。
为回应公众关切,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央和地方监管部门,多地医疗机构相继组织对集采代表性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开展真实世界研究,结论是中选的仿制药与原研药临床疗效和安全性相当。
“建议加强药品上市后监管,推进药品再评价工作,尤其是进入医保集采的药品。”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松蹊为今年全国两会准备的《关于加强药品上市后监管和监管能力建设的提案》中如是建议。
陈昊提出另外三点担忧:其一,“过评”只是确保仿制药疗效的最基本要求,而要实现“仿制药与原研药疗效相当”则是更高阶的要求。如果以最基本的要求作为行业标准,则监管侧和企业侧对于药品生产质量的把控,可能停留在及格线边缘。
“中国有个特殊的国情——不少仿制药是在早年国内GMP标准缺失或者说与国际主流标准不同步背景下获批的。当前,尽管我国相关药监法规逐渐与国际接轨,历史原因导致需要对此前批准的仿制药进行再评价。换句话说,一致性评价是‘补课’。目前,我国仿制药过评的药品还很少,而过评只是最低要求,药企还应该进一步提升生产工艺,这就需要监管之外的行业标准、企业标准。”陈昊说。
他提出,假如制药企业严格执行了法律法规和注册标准,并且严格按照GMP及相关标准从事生产,其生产的药品不用检验、不用评价,都能够达到质量要求。“这就是所谓的‘参数放行’”。
其二,过评后,在药品生产工艺发生重大变更时,地方监管执行力度可能不足。
2月中旬,有业内人士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信息称,其分析了国家药监局2019年至今的超过16万条药物补充备案后发现,过评仿制药广泛存在过评后生产环节变更。其中,集采仿制药发生供应商变更和生产工艺变更的比例分别达到45.7%和16.4%,超过非集采药的28.2%和9.6%。
根据《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企业可以根据变更的性质、范围、对产品质量潜在影响的程度将变更分类(如主要、次要变更)。其中,改变原辅料、与药品直接接触的包装材料、生产工艺、主要生产设备以及其他影响药品质量的主要因素时,还应当对变更实施后最初至少三个批次的药品质量进行评估。
而根据《药品管理法》,属于重大变更的,应当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其他变更应当按照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备案或者报告。
“GMP实施细则施行清单式管理,即清单之内的为‘重大变更’,反之为‘非重大变更’。但企业和地方监管部门在执行质量监管时,‘重大’‘非重大’‘主要’‘次要’等之间,存在模糊地带。”陈昊说。
其三,陈昊认为,“过评”是对仿制药而非仿制药企生产质量的肯定。依靠外部监管和事后监管,始终是一种“猫抓老鼠式”的监管,无法穷尽对每一批次药品、每一款药品的质量把关。
“比如,假设某个企业有100个产品,只有一款产品过评了,其他99款产品未过评。那么,这剩下99款药是生物等效性不达标?还是企业自身的能力问题?再如,当监管部门通过抽查、真实数据研究,验证100批次药品与原研等效,对于101批次药品仍然无法确保到百分之百合规。”陈昊称。
站在药品成本的角度,陈昊说,尽管批量生产可以降低药品生产成本,但要想确保整个药品生产质量体系安全、可靠、可持续,需要企业长期投入大笔资金去维护,也需要地方监管意识、能力和资源相匹配。
根据《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建立药品质量保证体系,履行药品上市放行责任,对其取得药品注册证书的药品质量负责。
“如果药企没有建立起完备的药品质量保证体系,就始终无法证明其生产的任何药品都值得信赖。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国内企业自身还是监管部门,对该体系的重要性均缺少认知。”陈昊说。
在陈昊看来,前述所提及的药品生产符合GMP要求,也仅仅为“及格线标准”。目前,离国产仿制药的“高水平安全”仍有一定距离。从与国际接轨监管的角度,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对现代制药工业体系,包括药品研发到生产的全流程,提出了更高的软硬件要求。我国已加入ICH多年,但国内对ICH的标准执行和行业自律水平还远远不够。此外,中国制药企业如若想获得国际市场认可,让国产仿制药获得“出海”成功,企业自身的药品质量体系管理标准还应该“更拔高一层”。
如需获得授权请联系第一财经版权部:banquan@yica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