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近千年来,地处江西南部的赣州尽管频遭暴雨侵袭,但依旧安然无恙。赣州人说,这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个袭用千年的地下排水系统——福寿沟。而且它至今仍在正常地为赣州近10万人的老城区服务。
近年来,一拨拨参观者来到赣州,试图揭开谜底:福寿沟到底是个什么沟?7月22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也造访了福寿沟。
老城区的“大肠”
“你们这里有过水涝吗?”在赣州老城区,如果这样问一个在这里生活了足够长时间的人,那么他在摇头之后就会以诧异的眼光看着你。
56岁的“老赣州”王展麒从小就踏着福寿沟之上的地面长大,当被问及福寿沟时,他马上张开双臂,蹦出这么一句话:“没有福寿沟,赣州就不会是现在的赣州。”
在王展麒看来,福寿沟就是赣州老城区(宋城)的“大肠”。只要福寿沟存在,老城区就能健康地“消化”和“排泄”。
从气候看,赣州地处亚热带,常年多雨。在地形上,赣州形如一只沉睡的乌龟。但与乌龟凸起的背部不同,赣州地形高低错落,易于积水,加上它东依贡江,西傍章江,历史上曾经屡遭水患。
赣州的水患,直至北宋熙宁年间(公元1068年~1077年),曾经当过水利部门高官都水丞的刘彝到当地(时名虔州)任知州之后才得以解除。
“刘彝到赣州后就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破除迷信,督促人们有病就医;第二件就是对福寿沟进行整治和扩建。”赣州市博物馆文博局书记、研究员万幼楠对本报记者说,在刘彝来赣州前,福寿沟就已经存在了。
在赣州不到四年,刘彝在福寿沟既有的基础上,根据赣州地势西南高,东北低的特点,通过分区排水的原则,建成了两个排水干道系统。因沟形走势如篆体的“福”、“寿”两字,故得名“福寿沟”。
福寿沟是以排雨水为主、雨污合流的下水道,即“寿沟受城北之水,东南之水由福沟而出”。主沟完成之后,刘彝又陆续修建支沟,形成了“旁支横络”、“纵横行曲,条贯井然”、主次分明、排蓄结合的排水网络。
古人治水,多靠疏导。福寿沟走势依地形而变,凭借地形的高低错落,通过疏导,使市内的雨水、污水自然流入江中。
而在城外,由于赣州三面环江,若遇雨季,高涨的江水常涌进城内,从而形成江水倒灌的现象。于是,刘彝再次依据地形在城内的出水口处打造了十二个窗口。万幼楠介绍说,这些水窗结构由外闸门、度龙桥、内闸门和调节池四部分组成,依据水力学原理,若江水上涨,则利用江水水力将外闸门自动关闭,而当水位下降到低于水窗时,即借水窗内沟道之水力将内闸门冲开。
福寿沟只是整个赣州排水防洪系统的一环。万幼楠说,在福寿沟的基础上,刘彝又修建了坚固的防洪堤坝,并将福寿沟与城内那些星罗棋布的水塘连接起来,以利于调蓄,“这好比长江流域鄱阳湖、太湖、巢湖对长江所起的作用,它们就是福寿沟的调节系统。”
消失的水塘
在赣州市城管局市政工程管理养护处一位相关负责人看来,福寿沟和水塘已经是老古董了,“古人排水主要是靠经验,而我们现在是以更科学更规范的原则进行建造。”
现在对赣州来说,福寿沟只是一个需要保护和维修的排水沟,“更科学更规范”的排水系统则在赣州的一些新城区建设和使用。
这位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表示,赣州已在地下埋下巨大的钢铁管道,其中最大的直径达2米。他还说,如果赣州发生严重水涝,在管道无法及时排水时,水泵将会派上用场。
不过一些赣州人说,“更科学更规范”的水道并不能解决一些新城区雨后积水的问题。“前几年,一个新城区的广场上,还不是一样的大雨过后就积水吗?一些汽车都被泡坏了。”王展麒说,“这在老城区是不会有的。”
上述负责人就此解释说,那是因为这些新城区还没装上更大的排水管。他说,赣州正在对一些还没埋设大口径管道的新城区进行规划。“要装上大管道。”他说,这将比古老的福寿沟和自然的水塘更强、更好。
一旦被问及赣州城内以前有多少口水塘,当地人都会说:星罗棋布。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冯长春一篇题为《试论水塘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及利用途径——以赣州市为例》的论文中称,1984年,赣州城内的水塘面积约0.6平方公里,占整个城市用地的4.3%。
“一些较大的水塘,面积比两三个足球场还大。”在万幼楠看来,水塘和福寿沟是一个完美结合的防洪防涝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水塘填了,福寿沟也就等于死了一半,甚至更严重。
赣州如今剩下多少水塘?一位受访者说,目前剩下不到四五口了,而且面积还在不断缩小。他说,几乎灭绝了水塘的老城区,在两年前的一场大雨中,一些地方竟然出现了他几十年来未曾见过的积水。“都到这里了。”他把手放在小腿上,示意水的深度。
大量水塘消失在楼房和道路之下。和其他城市一样,赣州正在一天一天变大、变高。不少担心福寿沟会随之受到破坏的人建议万幼楠将福寿沟上报申遗。但他说“这太难了”。
万幼楠说,直至现在,依然没有人知道福寿沟的地下走势究竟是怎样的,也没人知道福寿沟和那些原先星罗棋布的水塘的连接口究竟在哪儿,“你怎么拿出材料来申报?”
简单维护 照旧运转
整个福寿沟呈拱形结构,以砖石整齐地砌成。记者刚进入光线暗淡的福寿沟时,仅需稍稍猫着腰便可前行。但走入愈深,沟道便越来越窄小。在记者走过的这段约50米的沟中,最宽处约0.8米,高约1.4米,最窄处仅可一人行走,行走时腰需弯成近90度。
万幼楠说,现存福寿沟最宽处约1米,高近1.8米;最窄处宽、高各约半米。
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因为这是根据地形而构建的,为的是让水的冲力最大化,以便更好地排水排污,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整齐划一。”万幼楠解释说,“这告诉我们,刘彝用心良苦,在不该浪费的地方一点都不会浪费,而在需要的地方他则一点都不怕‘浪费’。”
在万幼楠看来,刘彝整治和扩展福寿沟源于一个简单的出发点,就是让百姓能长久免遭洪水的危害。
福寿沟能存在至今,又经过多少次大修?据万幼楠回忆,福寿沟的上一次大修是在清同治年间,当时曾引起了很大争论。人们担心这样的大修会超出库帑的承受能力。但知县却力排众议,他的方案是:在福寿沟经过的公共之处,维修资金由政府出,而与私宅相连处的维修费用则由私人承担。结果,大修的成本只有预算的一半不到。
经历了千年洗刷的福寿沟,一些砖石已经受到破坏,但大部分地方依旧保持完好,缝隙之间只容指甲插入。维护人员告诉本报记者,当时砖石之间的黏合剂主要是黄泥、沙子、桐油加上水和在一起,不断踩碾而成,黏性极强。
福寿沟的建筑材料主要是砖头。万幼楠说,砖是一种可更换的材料,不像水泥和钢筋那样难以更换,“砖头坏了可以拿出来换,就像修复文物一样进行修复。”
经过同治年间的一次大修后,福寿沟只在上世纪50年代进行过一小部分的维修,直至今日,赣州人只需对沟里的淤泥进行定时清理及局部修补,这条长约12.6公里的千年之沟就能照旧运转。
“每当一些地方遭遇水涝的时候,人们就会想到赣州。有一年,北京市政系统十多个人专门来这里考察。从那以后,全国很多地方的市政部门都来过人,但这些城市至今还不是一样被水泡吗?”一位研究福寿沟的专家说,“这还是机制的问题。”

千年荔枝“省”到长安,平安信用卡的三省服务“破圈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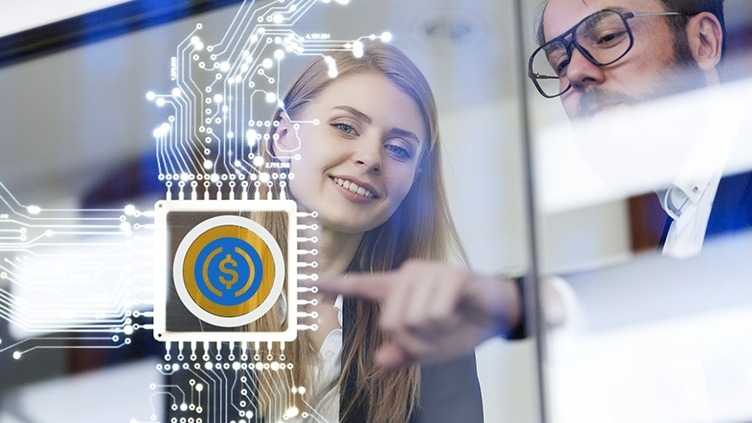
沈建光:美参议院通过稳定币法案的四大意义与启示
中国如果不发展离岸人民币稳定币将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所以应该考虑鼓励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稳定币。

全球非遗传承人齐聚上海,探索千年技艺的现代之路
2025年(第十三届)国际(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于6月5日举办。

景德镇就像活着的工艺实验室,千年窑火被带到上海
“设计上海”策划了“Made in JDZ”特别板块,邀请20多个品牌用年轻的创意与手工艺碰撞,产生新的花火。

“苏超”爆红给足球产业带来哪些启示?哪些省份可以复制?
大量中小城市缺乏精彩的、足够吸引人们入场观赛的足球赛事。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优质体育赛事的供给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