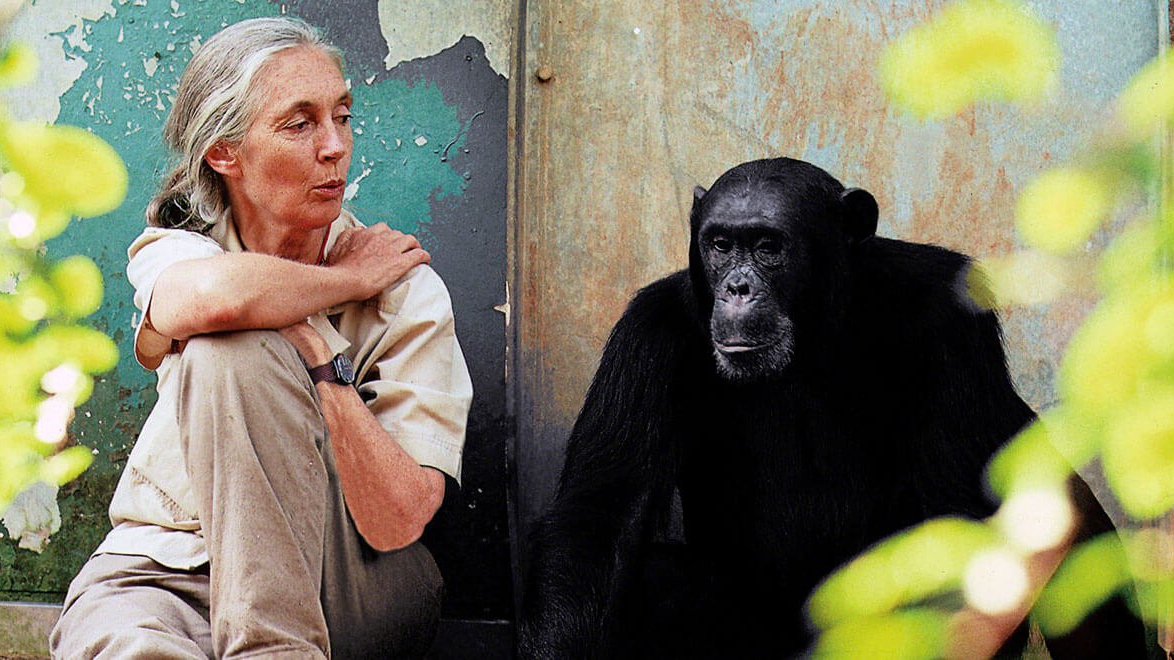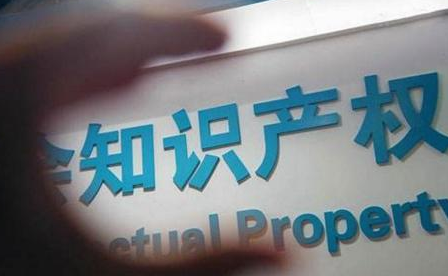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俄罗斯知识分子对中国人来说,可能是熟悉的陌生人。说熟悉是因为近代中国跟俄国有很多难解难分的关系,包括20世纪50年代后的思维模式、思想反省等都受到俄罗斯方面影响。”谈到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东欧史专家金雁的新著《倒转“红轮” :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一书,《读书》杂志前执行主编王焱用“熟悉的陌生人”暗示了此书的镜像意义。
在这部以俄国思想知识分子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专著中,金雁将几十年积累的涵盖了俄国思想史、制度史与宗教史的材料融冶一炉,用由近而远的倒叙方式,把俄国历史上几个典型的知识群体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予以抽丝剥茧般的解释。其中对两个不同时期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索尔仁尼琴和高尔基——进行的个案研究,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还原为对具体的人的思想与内心的考察,借此完成了从国家、民族、历史路径到个人选择的立体的史学叙事。
前言部分,金雁谈到写作的初衷:“我希望人们在走近真实的俄国知识分子时,少一些个人情感的臆想,多一些经得起追问的历史推敲,把它放在俄罗斯历史发展长河的背景中去考察,便会对各个知识群体‘自我选择’下的路径依赖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俄国知识分子经由“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开创的“大文学”,作为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变革、缔造社会思想的重要传统,为世界文学贡献了独特价值,而中国读者对俄国思想文化的总体印象与其文学成就有深刻关联,囿于此,许多认识流于浪漫化或模式化。接受记者采访时,金雁谈到:“希望做一个带着很多年的思考、能澄清一些问题的研究,最主要的还是希望客观、真实地反映在这样的制度下,知识分子思想上发生了哪些变化,我要反映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平民知识分子和贵族知识分子——他们之间到底为什么有隔阂和裂痕,最后成为角力的两个方面?”
忏悔的条件
第一财经日报:这本书以对索尔仁尼琴的研究为开端,这样的安排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金雁:既然是倒叙模式,当然要从近往远说。索尔仁尼琴在当代的俄国知识分子中比较有代表性,国内对索尔仁尼琴的解释我认为也不够准确。什么“悔过”之说,都是不了解这个人的心理历程的“表面文章”,他是从斯拉夫-东正教传统的角度反抗苏联体制的,他的主要的激愤矛头对准的方向始终没有变化。索尔仁尼琴反专制的确很坚决,但他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他提出的构想太过“乌托邦”,其实是没法落实到现实中的,像迁都西伯利亚等等,都是没法操作的。
日报:我们很容易用俄国知识分子的救世情结与中国知识分子做比较,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担当小了。
金雁:中俄两国知识分子的比较并不是我书中的要表达的内容,它们的产生和成长的社会背景有较大的差异性,至于俄国知识分子也不是一个统一体。我在第六章第三节,“多面的狐狸:贵族知识分子的特点”和第八章第四节“两种知识分子的比较”中对不同类型的知识群体有一个总结。所谓“弥赛亚”就是“天降大任于斯”的民族、“是通晓上帝真理的民族”,很多俄罗斯人认为自己的国家要优于其他国家,它曾经拯救了欧洲甚至可以说拯救了全世界,从“第三罗马”创建以来,这个命题已经深入俄罗斯人的内心,它是为了突出民族性的东西。由于俄罗斯民族演进道路上的特点,“超大型国家”的整合难题,它造成的可以轻易“分散开来”对俄罗斯的民族认同形成很大的挑战,俄国一直饱受国土面积和人力资源的不匹配导致的紧张和不安的困扰,在这种“焦虑综合征”下,他们格外看重民族性对俄罗斯民族的重要意义。而这样的民族性也是具有两面性的。
日报:从对苏联史、东欧史和东欧转轨的研究,转向对俄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是基于怎样的考虑?想解决什么问题?
金雁:这本来就是老本行,不存在“转向”的问题。梳理俄国知识分子是我长久以来就有的想法,积累了不少东西。蔡定剑等人的故去,让我感到一个人的学术生命也许真的不像想象的那么长,有话说还是趁早。
我感觉已有的东西一是较平面,不够立体化,或者浪漫想象有余,严谨的研究不足,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按照文学家的创作方式去想象俄罗斯。比如,很多人都在质问“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忏悔?”这样的诘问本身并无可厚非,理由就是说,俄国知识分子有忏悔的习惯,我在本书中交待了,俄国贵族集体忏悔的举动是由于他们使用白给的劳动力合法性不足,而用忏悔的举动求得心理平衡,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贵族知识分子的特点。而中国并不具备这样的社会环境。
中国这方面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社会史和思想史脱节,俄国思想史上一代又一代人的较量是建立在社会制度方面一层又一层的因果关系中,我希望人们在走近真实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时,少一些个人情感的臆想判断,多一些禁得起追问的历史推敲,多一些历史感悟,多一些历史透视。把它放在俄罗斯历史发展长河中去考察,便会对各个知识群体的“自我选择”下的路径依赖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索翁说,我和写作有一种神圣关系,我的写作是在履行某种义务。我没有那么高的境界,但是我能意识到全景展现俄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思想界的重要性。我也懂得别尔嘉耶夫等人一遍遍不厌其烦地清理激进主义、揭示俄国共产主义的发展逻辑,就是不希望后人重蹈覆辙,从而促进社会的自我认识。对高尔基的大起大落背后的人格悲剧让人们看到,就像科赛所说的,“要想成功地在掌权者手下扮演一个参与者或温顺的专家角色,就必须以知识作为祭品,以此前积累的名望作为敲门砖。至于第三种知识分子的努力,对建设中国社会有借鉴意义。而我们这些搞苏俄历史的人、搞思想史的人如果不能真实地把这一切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就是我们的失职。这种责任感我还是有的。我想写的这三本书是一个相互有机联系的姐妹篇。”
文学庇护所
日报:读《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的问题。写作的时候是否有中国意识?
金雁:很多人说我有中国意识,有读者打电话说,你说的俄国的思想界和中国的非常相像。我只能说,这表明这一类国家的确是有共性的。至于展现出来的俄国思想界发展历程,我是在大量阅读史料的基础上得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恰恰是不能有任何预设的想法或者先入为主的“影射”的。
这本书的特点是时段长、涉及问题比较多、除了两个个案以外,把这一百年里两个轮回的(狐狸型知识分子和文化保守主义——刺猬型知识分子和列宁主义)遗传关系和对立原因都展现开来,而且还要对人们印象中的一些常识进行更正。比如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这个跷跷板,你高我低和我高你低的相互轮换,需要放在长时段进行观察的问题,视野过窄很难看清全貌。但如果做一个以百年为时间段的研究,就能看出问题背后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希望客观、真实地反映制度与思想界的相互关系。
日报:在关于索尔仁尼琴的章节中,提到了中国的梁漱溟,但是没有展开,能否深入谈谈他们之间的关联性?
金雁:我在第四章专门谈了把俄国保守主义和中国保守主义做比较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不是我这本书所要承担的任务。对人们比较关心的文化保守主义,我的学生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他们深刻我们肤浅?为什么他们能上升到一个宗教哲学的高度,而我们却有很强的功利实用考虑。我想没有体制的约束、不去端国家的饭碗、相对自由的环境以及宗教资源的坚定性和大视野都是原因。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以自己的研究交换什么东西,没有任何人从这种坚守中得到过任何世俗的好处,这和拿课题领经费搞研究完全不一样。与世俗隔断的前提是他们深邃的原因之一,断不会出卖知识、出卖思想换取实际的利益。这是他们特别纯粹的一面,反观中国知识分子,经得起迫害,却耐不住寂寞和孤独。另外,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等人的努力也使得他们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
日报:形成俄国“大文学”传统的时代条件是什么?
金雁:这是我第六章第三节中的一个重点,也就是赫尔岑所说的,“俄国文学背负起超越自己承载量的重担”。最初是一种无奈,后来变成了路径依赖下的一个显著特点。
“十二月党”起义之后,知识分子不能谈政治,“文学的独大”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有人说“俄国文学从来都是和沙皇的政治制度格格不入的”,其实准确地说,是因为沙皇时期的政治生态使得知识分子只能在文学领域表达自己与“沙皇制度的格格不入”。赫尔岑在提到“文学中心主义”的时候说:“从彼得一世起,俄国的历史便是贵族和政府的历史,贵族阶级中包含着革命的酵素,它在俄国没有别的舞台,那公开的、流血的、街头的广场,它有的只是文学的讲坛,我们在否定方面比其他人走得远”。这个路径依赖使俄国的文学一枝独秀,这种文学并不是现在谈的“纯文学”,因为政治高压下“文坛”是最后一个庇护所。沙皇尼古拉一世看得很透彻,他说,在这伙人那里,“教育”一词就等于“自由”,而“智力活动”指的是“革命”,“哲学”几乎就是煽动造反的代名词,连沙皇的官吏都知道,“不要期望哲学家是为我们服务的人”。政治缺席以后,大家都只能在“文学”中寻求各自思想的尖锐性和深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