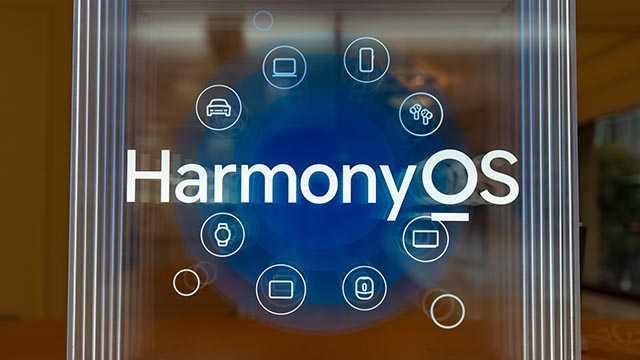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1906年10月4日,日本《国民新闻》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清国人志于洋画》的报道。其中讲述了一个名为李哀的“清国”年轻人,留学日本,考入东京美术学校(现名为“东京艺术大学”),而且“专学洋画”。
这个“清国人”就是李叔同——二十世纪的传奇人物,在古诗、曲词、书画、篆刻、西洋音乐、西方戏剧、文学、油画、美育、佛学等领域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年之后李叔同学成归国,回到上海,著书、写文、办报刊,积极推广西洋美术教育,大胆地在教学实践中首开人体写生课,成为“中国西洋画传播第一人”。
这位艺术界开先河者只留下极少数的美术作品,一般认为仅有两至三件,鲜为公众所知。去年初始,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一幅藏品“2011-甲”被研究人员发掘出来,经鉴定为李叔同的代表作《半裸女像》。借此机会,该馆于近日举办了“芳草长亭——李叔同油画珍品研究展”。展览将持续至4月25日。
“这件在众多中国现代美术史书籍中刊出,但是都不明其收藏处的李叔同代表作,就在中央美术学院库房里静静沉睡了半个多世纪,”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在展览前言中写道。“可谓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
画作右上角的玄机
展馆的墙壁被刷成豆绿色,同中央悬挂的那幅画作有着相类似的雅致氛围。画中是一名斜靠在扶手椅上的年轻女人,披散着长发、裸露着上身,仿佛热天刚沐浴出来想小憩片刻。在光影对比之中,她的脸庞、手臂和胸脯都显出柔和而细腻的质地。
女人是那么生动,仿佛观画者只要弄出点响声就会惊醒陷入梦幻的她,下一秒就会像小鹿一样抱起衣物跳开。
“李叔同的绘画技巧是很高的,”典藏部副主任李垚辰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说,“首先它的尺幅很大,当时日本通用的标准自画像、风景画是12号画框,而《半裸女像》是50号,接近真人大小。”
叶圣陶曾经在《刘海粟文集》的序言中提到过:“我国人对人体模特写生,大概是李叔同先生最早。他在日本的时候画过一幅极大的裸女油画……”那个年代,少有大规模、大空间的展览,画家作画多半会挂在家中,因此今天看来只是中等画幅的作品也可谓“极大”了。
“其次是他所使用的古典技法:即铅白打底、彩色晕染。”李垚辰解释道,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通行的传统画法,画家直接用铅白油画颜料在画布上厚涂一层,等完全干燥之后再开始进行正常的绘画上色工作。“他的画里运笔潇洒,画面看着一点都不‘紧’。而且形体结实,空间感强,构图也很讲究。色调雅致,很静。”
25岁出国的李叔同,接触到完全迥异于中国画的画法,从最初始的透视法、素描、色彩、写生一一学起,到最终毕业归国。创作出这般大尺幅而精致传神的作品,俨然已成上流画家。
同《半裸女像》一同展出的还有另外一幅同期创作的作品《自画像》。后者来自东京艺术大学的收藏,是该校在20世纪10年代到40年代之间,近百名留日中国学生的毕业作品之一。同《半裸女像》的冷色调不同,《自画像》明显借鉴了西方当时最时髦的“新印象主义”画风,用明显可见的彩色点状笔触遍及全画,希望可以通过精细排列的原色来展现光影色泽。
在李垚辰看来,所有这些毕业作品里,确是李叔同的这一幅最有大成之风。
《半裸女像》最早出现在1920年发行的《美育》杂志第一期,该画下端注明了“《女》(油画,上海专科师范学校藏)李叔同先生笔”。杂志的主编吴梦非曾经是李叔同的学生,建国后,他在1959年发表过《五四运动前后的美术教育回忆片段》一文。文字插图便是这幅裸女图,但图片来源有过更新,且文中提到“李先生曾做油画‘裸女’一幅,此画现尚存于叶圣陶先生处”。
原来,李叔同在他39岁出家前夕,把这幅画作送赠与挚友夏丏尊。建国之后,夏家亲属又托叶圣陶代送给了中央美术学院。但这也都只是后来的研究者们在故纸堆中找到的回忆文字。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众多的专业书籍每每介绍国内西洋美术史时必提李叔同,用的附图都是这张《半裸女像》,但是使用的题名都不一致,且都没有注明该作品现藏何处。
直到2011年。“馆长说在整理库藏的时候可以留心看看,也许有呢。”李垚辰忆起发现的过程,就好像是考古挖宝一样。他在史料里看到了那幅模糊不清的影印图,跟馆藏的这幅匿名作者画像非常相像,于是就开始了一步步地探究、考证过程。
经过X光射线检测,该画作右上角的花瓶底下还有一层画着大束的花朵,显然是作者经过构图思考做出的涂抹修改。“临摹者是不会改动的,只有创作者才会这样做。”李垚辰说,“这是最终确定《半裸女像》是李叔同原作的关键。”
从翩翩公子到美育导师
这位25岁出国游学的“清国人”,在留日之前便已是才学广博,喜爱吟诗作赋,又交游广泛,在当时的上海文艺界小有名头。他看到了明治维新的文化成果,不仅仅只专注于西洋绘画,而是开始全面攻读西洋艺术,绘画、音乐、文学、戏剧等等无所不包。
归国之后,李叔同便把自己融汇中西的才学全部倾力推出。任教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期间,“翩翩公子”收起全套旧绅、西洋派头,穿上黑布马褂,严肃又严谨,当时才十七岁的学生丰子恺形容老师的形象为“温而厉”。
“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以及他的教课笔记簿、粉笔。钢琴衣解开着,琴盖开着,谱表摆着,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我们的眼中。”他写道,“在这样布置的讲台上,李先生端坐着。坐到上课铃响出,他站起身来,深深地一鞠躬,课就开始了。”
在丰子恺的描述中,因为李叔同个人的缘故,使得通常不受大家重视的音乐课、美术课反而最有分量。同期的国文老师夏丏尊对他也极为尊敬,曾称赞他说“因为他教图画、音乐,而他所懂得的不仅是图画、音乐;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这好比一尊佛像,有后光,故能令人敬仰。”
博学宽厚的夏丏尊,后来译出《爱的教育》,成为一代教育家;丰子恺后来成为中国漫画的开创者,同时写得一手幽默风雅的散文,更不用提音乐艺术家刘质平等,这些人都深受李叔同的人格“光芒”影响。
李叔同在他39岁时断然了结所有尘世牵绊,出家为僧,静心研究佛法。丰子恺说,他“从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做得十分像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青衣象个青衣,起老生象个老生,起大面又象个大面……”
而这一切,都仿佛在他29岁时创作的这幅浑然天成的裸女画中,盈盈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