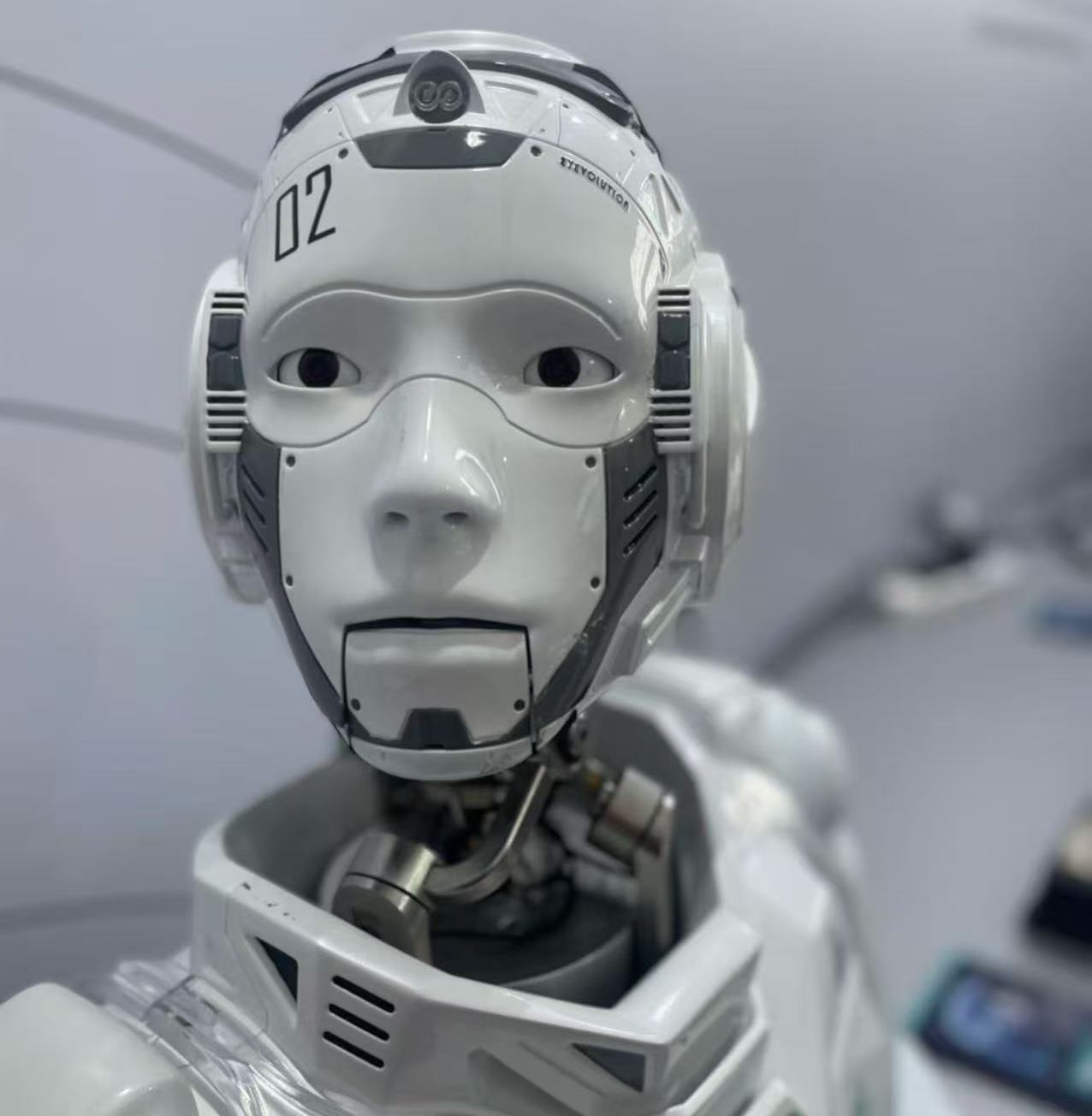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乔·史塔威尔是信奉政府之手有助于经济发展的。而且,他提出的3个关键干预措施,都要求政府给予目标性极强的干预;同时,要求政府拥有极强的规划和自律——当然也要有极大的权力。
作为在东亚地区做过20年报道的资深记者,作者乔·史塔威尔深入研究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越南、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这些国家及地区的经济情况。他以深入浅出的文字,展示了发生在亚洲这片土地上的真实情况。
在他的上一本书《亚洲教父》中,乔·史塔威尔已经试图在探索东亚运行的逻辑。他说:东亚奇迹的主角,不应该是那些在《福布斯》富豪榜上出没的“亚洲教父”,而是那些拿着低工资在制造业工厂中工作的女工。因为是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创造了东亚经济发展的奇迹,而不是教父们热衷的房地产和资源性行业。在2013年出版的《亚洲大趋势》(英文版)中,乔·史塔威尔延续了他在《亚洲教父》中对亚洲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
乔·史塔威尔的发现可能不为一些经济学家所喜爱,尤其是奉行自由市场学说的学派。他的开宗明义之词为:“本书论述了亚洲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成败得失,指出了政府可以采取3个关键的干预措施来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这也表明乔·史塔威尔是信奉政府之手有助于经济发展的。而且,他提出的3个关键干预措施,都要求政府给予目标性极强的干预;同时,要求政府拥有极强的规划和自律—当然也要有极大的权力。我们得承认,能满足这3个条件的政府本身就很少见。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而言,它们也只是拥有极大的权力罢了。
这3个干预措施是:采取土地改革政策,实现农业产出最大化;引导投资和企业家进入制造业;干预金融部门的运行,让金融业服务于小规模集约型农业及制造业的发展。
在乔·史塔威尔看来,正是这3个方面的措施,导致日本、韩国、中国内地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正是在这3个措施上的实施不力,导致了东南亚的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经济发展后劲不足。
土地政策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在一个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国家里,往往有75%的人口在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依靠土地谋生。”土地改革最显而易见的好处是,它可以解决大量就业,提高土地的单位产出。第二可以减少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这会为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减少阻力。第三个好处是,农产品的充裕可以为下一步工业发展提供动力。此外,农业产出的增加带来了农民收入和购买力的增加,这会创造出一个农村市场,并激活农民中企业家精神的觉醒。经济学家黄亚生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内地绝大多数后来发展成为大型公司的民营企业,正是在边缘的乡村地区开始崛起的。
在乔·史塔威尔看来,“土地分配不公和农业效率低下”,已经成为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面临持续恐怖活动和叛乱活动的问题根源。但这些国家和地区仍然以靠不住的自然条件原因和政治借口抗拒出台土地政策。这“是狡猾的、用心不良的,至少表明这些国家无法控制它们自己的发展命运”。
但乔·史塔威尔是在对这些政府提过高的自律要求。他自己在菲律宾的例子中也指出,这个国家的执政者背后都是大庄园主。一些知名的大庄园主,都是总统的亲戚或挚友。“菲律宾的统治精英为了自身利益而无所不用其极地阻扰真正的土地改革,阻挠手段之多同样堪称亚洲之最。”
在乔·史塔威尔绘制的经济起飞路线图中,土地改革是第一步,接下来该轮到工业政策。“土地改革与其他农业改良措施虽然能带来一定的红利,但经过10年左右,这些红利就会逐步弱化,因此处在崛起过程中的经济体必须过渡到另一个发展阶段。”这个新的发展阶段“是围绕着制造业展开的”。
第一个干预措施,需要借助一场“革命”,如中国内地那样;或者外力的干预,如日本和中国台湾那样。第二个干预措施,需要的是一个对经济发展有强烈动力且权力最好不要受太多制约的总统或执政者集团。
它要求政府做的是:第一,对本国的制造业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给予财政补贴和政策帮助—它要求政府要无私,否则就是裙带主义的温床;第二,这一条听上去对企业家们没有那么美妙了,要实行严格的出口纪律。出口纪律指的是,“政府连续性地评价、检验那些获得政府保护与补贴的本国制造企业,迫使企业发展出口贸易,参与全球竞争,依据企业出口业绩的高低来决定支持谁不支持谁。”在乔·史塔威尔看来,全球贸易是最好的试金石,可以验证政府扶持起来的是一个靠吸食财政和税收来谋取利润的公司,还是真正具有竞争力可以为国家赚取外汇的公司。
乔·史塔威尔要求政府对私人企业施以强干预,并非他不相信“企业家精神”。他的逻辑是,首先政府不能绕开私营企业自己进入各行各业,因为这已被证明是效率低下之举。但是,“政府必须运用自己的权力,尤其是控制国有资产、商业许可、银行信贷以及稀缺外汇的权力,引导企业做一些产业发展所需的事。”原因是,“政府对企业家的看法必须现实一点,不能对其道德水准抱有幻想。国家必须逼迫他们把本企业的逐利行为与实现国家整体发展目标结合在一起。”
在这方面,韩国的例子从过程来看有点吓人,但从结果来看堪称榜样。
1961年,朴正熙依靠政变上台执政。政变成功12天之后,朴正熙“以违反控制投机倒把的特别措施为由逮捕和关押商人”。朴正熙宣称,“自由贵族”时期结束了。这些“自由贵族”指的是依靠同李承晚政府的裙带关系谋取私人利益的企业家。新任总统要求这些被捕的商人同政府签署协议,协议中写明:“当政府需要我的财产开始国家建设时,我愿意全部捐献出去。”听上去像是个贪婪的独裁者的口吻。好在朴正熙不是为了谋取个人利益。
朴正熙并没有野蛮到要没收这些商人们的财产,他想要做的是,迫使这些商人进入出口制造业。三星和现代这些今天看来具备了全球竞争力的韩国制造企业,正是在那一时期开始转型。
回到《亚洲教父》。东南亚国家显然就没能产生如现代、三星这样的公司,虽然这些地区产生了如郭鹤年、林邵良这样知名的福布斯富豪。乔·史塔威尔说,原因在于,“在东南亚国家里,主流的企业家在能力方面绝不逊于其他国家的企业家,但政府没有引导他们从事制造业,也没有对他们实行出口纪律。”
第三个干预措施,则是要使金融部门的政策目标同农业和制造业的政策目标紧密结合。乔·史塔威尔的这番话显然不对一些经济学家的胃口:“对于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国家而言,并不适合推行自由主义改革,不适合放松金融监管,不能让银行自发寻求回报率最高的投资领域,最好还是对金融体系长期维持严格监管,使其服务于国家整体发展目标。”
使韩国走上工业发展之路的总统朴正熙的观点是:一个妥善管理的银行体系必须具备两个要素,一个是必须接受政府的管制,另一个是必须满足发展重工业的融资需求。
这要求政府不能轻易放松银行管制。轻易放松的结果,就是“亚洲教父”们控制了银行,然后使银行变成了自己公司的输血机。
总结完东亚经济奇迹的政府因素之后,乔·史塔威尔以一种戏谑的口吻说:“贫穷国家必须学会撒谎,一方面公开赞成富裕国家推崇的自由市场理论,另一方面则继续采取干预政策,先让自己变富裕,再考虑效率。”
当然,史塔威尔并不认为干预措施可以一直延续。他是一名记者,他认为有效的理论必须来自于对现实的总结。和所有的记者一样,他也认为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措施。在经过了起飞阶段之后,政府就必须在土地政策、工业政策和金融政策方面再做变化,变得和“富裕国家”一样赞扬自由市场理论。
《亚洲大趋势: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未来》
作者:[美]乔·史塔威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年05月
定价:68.00元
乔·史塔威尔,《中国经济季刊》创办人、《经济学人》知名撰稿人,曾出版《亚洲教父》中文版,畅销10万册以上,长期担任《经济学人》驻北京记者,《金融时报》称其为有关亚洲商业为何以及如何发展的“流言终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