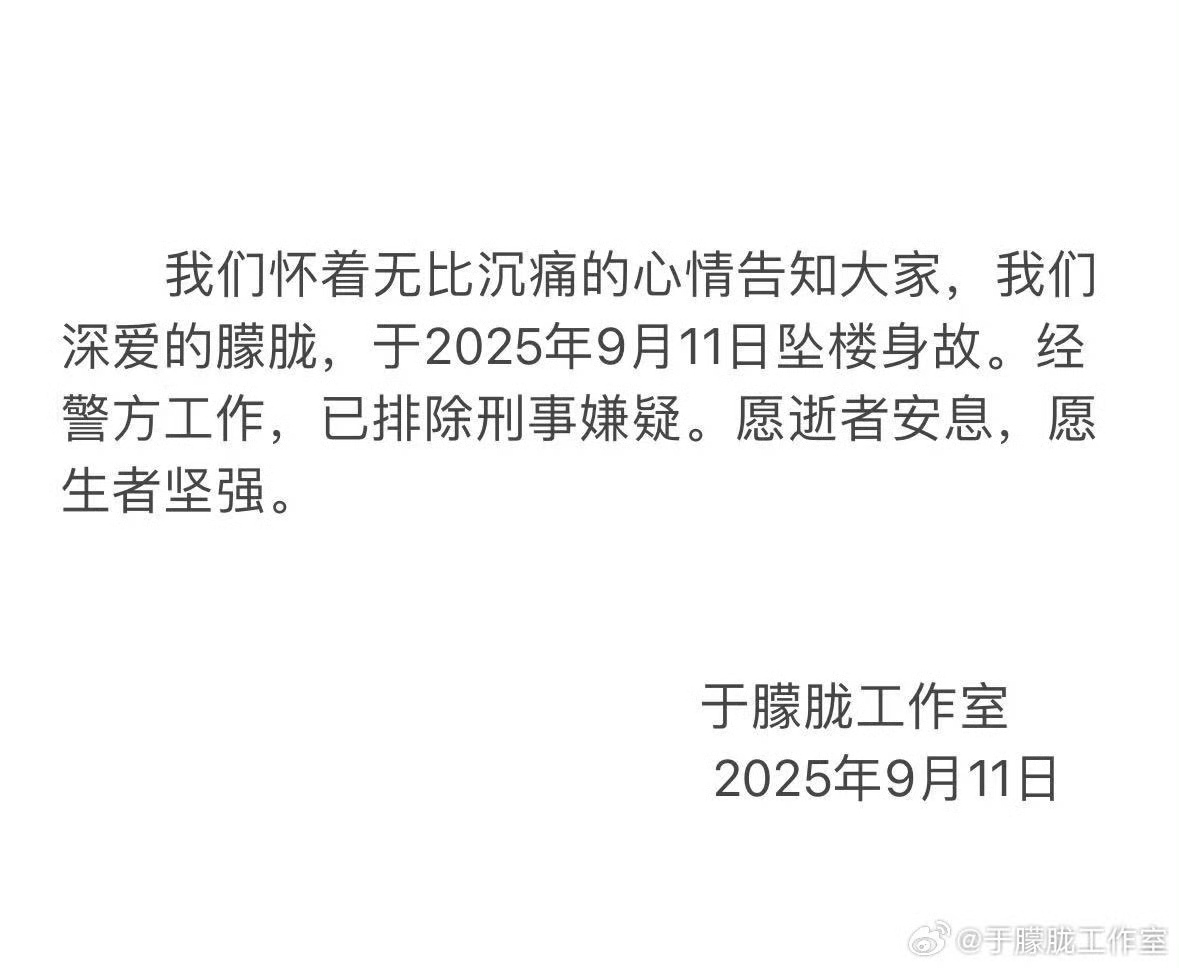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1986年,22岁的安德烈·萨金塞夫刚从俄罗斯陆军部队退伍,从家乡新西伯利亚搬到莫斯科,去俄罗斯电影工业的中心城市实现自己的演员梦。
从1992年到2000年,他拿着两份表演文凭,艰难地在影视圈混迹挣扎,为了养活自己什么戏都演,任何机会都不放过。最窘迫的时候,他“穷得连一张公交车票都买不起”,却仍然籍籍无名。36岁时,他决心转行导演,2003年拍摄了第一部小成本电影《回归》,一举横扫包括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在内的多项国际大奖。
多年后的今天,俄罗斯人把他称为“新时代的塔可夫斯基”。54岁就去世的俄罗斯导演塔可夫斯基在他充满哲学与宗教意味的电影中始终关怀着人类精神世界。在外媒眼中,萨金塞夫是个低调神秘的导演,从不愿对外界解读他电影中的复杂隐喻。
受邀担任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主席,萨金塞夫多少有点忐忑。在他之前,担任主席之位的是汤姆·霍伯、让-雅克·阿诺、吴宇森、丹尼尔·博伊尔这样的国际大导演。只会说俄语的他,在社交场合显得有些沉默寡言。在电影节开幕的第四天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独家专访时,这位含蓄的导演不肯透露他对几部参赛片的印象,倒是对自己的电影生涯和电影观念滔滔不绝。
1964年生于俄罗斯新西伯利亚的萨金塞夫,只拍过四部电影,却已成为世界电影界的焦点人物——除了一鸣惊人的处女作,他的《将爱放逐》(2007年)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并获最佳男主角奖,《伊莲娜》(2011年)获戛纳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去年,一部影射俄罗斯强权政治的《利维坦》更是一举奠定他在世界影坛的地位,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并斩获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
身着蓝色棉质衬衫、白色长裤的萨金塞夫走进房间转身坐下时,粗黑框眼镜背后的温和目光让人想到费里尼电影《八部半》里那个英俊、焦虑而聪慧的导演。
“我的第一部电影上映的时候,我已经39岁了。”萨金塞夫说,他从不认为这个年纪对一个导演太晚,相反,他认为做导演不能太年轻,“如果一个人太年轻,生活中没有失去过什么,没有犯过错误,没有体会谅解的含义,人生就不够宽阔,对社会的看法也太稚嫩。对导演来说,经验是很重要的,人生经历不只是你在书本上读到的,而是你真正在生活中感受到的。我对年轻人的建议是,不要急于去拍电影,你应该先累积技术层面的经验,先去了解演员、摄影是怎么工作的。”做过十年职业演员的萨金塞夫,体会过很多生活艰辛。他的作品总是观照普通人的家庭生活,却由此折射出整个俄罗斯社会在变局中的动荡不安。
“当今俄罗斯社会是‘金钱至上’的,俄罗斯追求的繁荣不是精神上的,而是人们钱包的繁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性一定会扭曲、改变。”萨金塞夫那部广受争议的《利维坦》,故事原型来自他听到的一则美国新闻,“一件发生在美国的事情,一个男子与政府发生冲突,开着拖拉机推倒了政府办公大楼。这件事让我想了很久,它恰巧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一滴水可以映照整个太平洋。”萨金塞夫说,他的电影都是两三个人、一个家庭内部发生的故事,反映的却是世界各国都共同存在的问题。他的故事不仅是俄罗斯社会强权政治的写实,对其他国家也有震撼人心的批判力。就如英国《卫报》的影评所言,《利维坦》“融合了霍布斯、契诃夫和《圣经》,充满非凡的影像和对应性。一部令人敬畏的恢宏之作”。吊诡的是,《利维坦》这部揭露当局腐败的电影,得到了俄罗斯文化部和国家电影基金会的资金支持,电影上映后,俄罗斯文化部部长公开批评萨金塞夫的导演意图。面对来自官方的指责和压力,萨金塞夫显得很淡然,“政府的支持和一位文化部部长的发言,我认为是两回事。他有权发表批评意见,我也有权在电影里表达我的观点。我们只是打了个平手而已。”
萨金塞夫的新片正在筹拍中,等上海电影节结束,他就会回到俄罗斯开拍第五部电影。他谈到对压力的态度,似乎就像他电影中的人物一般倔强、刚毅,“我个人没有感觉到任何压力,我也不知道《利维坦》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将来的工作。如果我的下一部电影没有得到政府支持,那么他们应该有一个合理的理由来拒绝我。”
“我不会选择票房和商业都引人注目的大片。一个演员一年能演一部至四部电影,而我这样的导演通常要花三四年才能完成一部电影。”萨金塞夫笑着说,“我只想把所有的时间拿来拍我想拍的电影。”
萨金塞夫:下一部电影,我还是会坚持自我
第一财经日报:做导演之前,你做过很长时间的演员,付出了十年的努力。这段经历对你后来做导演有什么帮助?
萨金塞夫:我16岁考上新西伯利亚戏剧学院表演系,在那儿上了四年学。当我看到阿尔·帕西诺的电影,被他的表演震撼了,难以想象一位演员的演技可以达到这样的高度,这些显然是在学校里不可能学到的。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决定离开话剧舞台,去莫斯科重新学习,只有在莫斯科才能实现我的梦想。
到莫斯科后,我又去国立莫斯科表演艺术学院学了四年,所以我相当于上了两个大学。在莫斯科念书期间,又有一个深刻影响我一生的事情——我看了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1960年的电影《奇遇》,这部电影让我真正爱上了电影艺术。那时候我的梦想还是要成为一个出色的演员,特别希望能够遇到一个像安东尼奥尼这样伟大的导演,他能指导我如何去表演。在毕业之后,大概12年的时间,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漫长的等待,我不断在进行自我定位、自我寻找,直到2003年,才拍摄了第一部《回归》。
日报:在漫长的等待中,你如何一步步从演员转向导演的道路?
萨金塞夫:在毕业之后的几年里,我经常去跑电影院,经常去电影博物馆,我当时就很相信,自己有能力去拍摄30秒之内的广告。所以这12年对我来说是一个等待,同时也是过了非常不规则的12年。
我出生在前苏联时期,当时,整个社会并非自由社会,一个人的社会职业的选择、人生道路的发展,都是按照一个固定的渠道、固定的路线来进行的。在前苏联,一个学表演的人如果想要去拍摄、做导演,都是实现不了的。之后苏联解体,整个社会秩序发生巨变,变成一种自由的社会体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导演的梦想才能够实现。
日报:你的电影都是小人物的故事为主题,都是围绕普通家庭的悲剧故事,然而每一部小成本制作的电影都获得各大电影节的青睐,引起全世界观众的共鸣。
萨金塞夫:我倒不觉得成本是什么太关键的事情。坦率地讲,成本可能是我在考虑拍摄一部影片的时候,最后一个才要考虑的问题。
我也不是特别喜欢“选题”这个词。很多时候我想拍摄一部电影,就是突然间有了一个愿望或想法,然后我就想办法实现。比如《利维坦》,其实就是一个突然出现在我脑海中的想法,我想去抨击在我们世界上存在的一些不公平的现象。我并没有刻意去找一个题材能够打动观众或吸引市场。普希金的诗里有一句话,大意是,“如果你对一个女人表现得越是淡漠,她对你的爱将会更加炽烈”。如果你刻意讨好女人,她反而不会喜欢你。这种关系同样适用于导演和观众,如果你刻意迎合观众的口味,反过来观众与市场不会很好。因为刻意的讨好,意味着丧失你个人的、独特的观点。至于说家庭题材的影片,我经常听记者这样提醒我,但我自己真的没有意识到。
日报:《利维坦》上映后,在全世界范围里都引起了讨论和争议,在俄罗斯出现了不少反对你的声音,对于这种超出电影之外的反响,你怎么看?
萨金塞夫:这是完全没有办法的事情。一部电影引起这样的社会反响、这样的讨论,可能是关于政治层面的,甚至关于我们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但对我来讲就像天要下雨一样,只能让它下了。这样过度的、电影之外的讨论,可能会干扰到一些观众对电影本身的理解,但还是那句话,我对此没有任何办法。
我也同意这种说法,电影本身,我想要表达的含义,比我现在在媒体上看到的所谓的讨论,要更广阔、更深刻一些。《利维坦》所反映的事实、含义,不只是针对今天的俄罗斯的社会制度,我想要表达的是小人物在庞大国家机器面前的无助,个人利益和国家机器发生冲突,小人物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电影毕竟是在今天拍摄的,观众或媒体在讨论这个电影时,的确很难跳出今天俄罗斯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在俄罗斯,有政治家,也有普通人,他们说这部电影的作者应该站到莫斯科市中心的红场上去,面向克里姆林宫,向全体俄罗斯人民道歉,像这样的言论难道还能说是对电影的讨论吗?我觉得,这已经偏离了对电影本身的讨论,偏离了围绕艺术这个话题开始对话的初衷。反过来也说明,这部电影确实反映了非常深刻的社会现实。
日报:《利维坦》之后,你觉得自己的导演空间是更大还是需要更谨小慎微了?在拍摄下一部电影时,你会更关注自我表达,还是会考虑外界的评价?
萨金塞夫:俄罗斯有一句俗语,“一只狗在那里狂吠,但火车会继续往前开”。火车不会因为狗的叫声而受到影响,我也不会过多去考虑外部评价、外部讨论,这对我个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利维坦》这部电影,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它是一部真实的电影,它的的确确表达了我对这个世界的一些看法。我敢说,这部电影中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为什么还要去过多地考虑别人的说法。我的下一部电影是否应该引起更广泛的社会影响,这我不会过多考虑,我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社会学家。
下一部电影和《利维坦》没有太多关系。《利维坦》在俄罗斯乃至全世界引起了很多争议,但我没有必要继续或重复这样的争议。我只能说,下一部电影,我还是会坚持我自己独到的观点。一切顺利的话,这部电影在7月到8月就要开拍。至于拍什么,很抱歉我现在不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