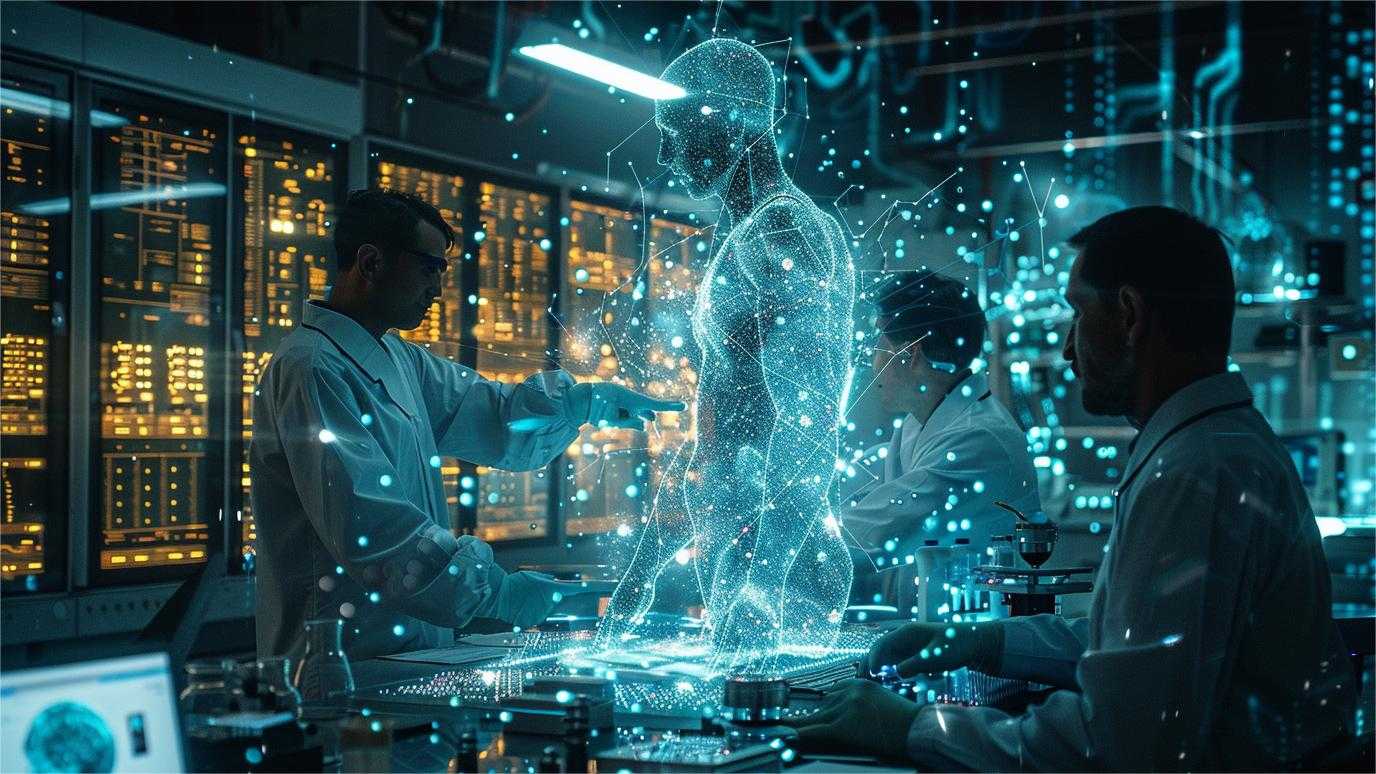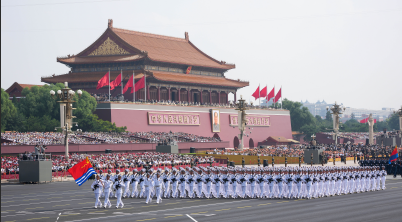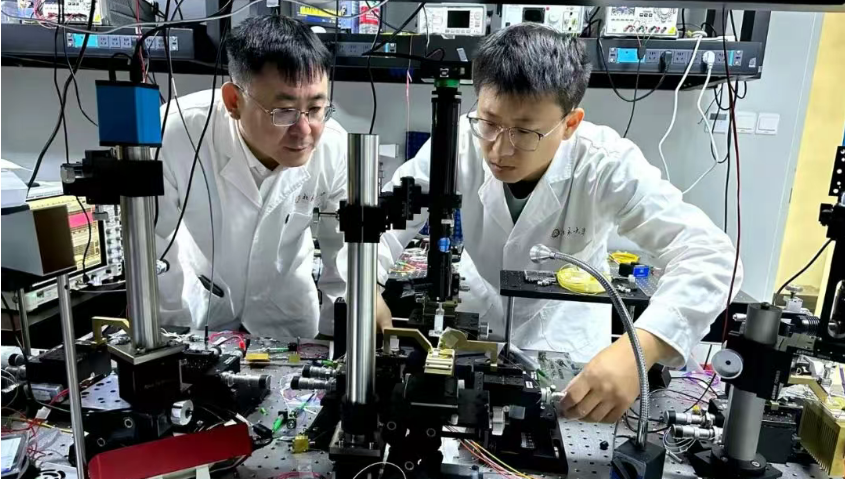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因为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屠呦呦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无博士学位和留洋背景是“文革”前的历史条件所致,落选院士则值得探究。据了解,前些年屠呦呦曾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但均未当选。
像屠呦呦这样做出国际认可的重大科学贡献而落选院士的,在我国并非个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比袁隆平晚一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中科院上海系统所研究员李爱珍,享誉海内外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饶毅……
这些人是因为学术水平不高、科学贡献不大而落选院士吗?答案显然不是。从上述几位“落选院士”的治学为人风格中,人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示。袁隆平至今仍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扎在水田里研究超级水稻;李爱珍数十年如一日呆在实验室里搞研究,如果不是因为她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恐怕还不为社会所知;屠呦呦除了“不善交际”,还“比较直率,讲真话,不会拍马,比如在会议上、个别谈话也好,她赞同的意见,马上肯定;不赞同的话,就直言相谏,不管对方是老朋友还是领导”(屠呦呦的老同事李连达院士语,笔者注);饶毅则是出了名的“敢讲话”,研究之余还在自己的博客和国内外媒体上撰文,批评中国科技体制的弊端、教授不听讲座的浮躁学风等。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中国农大原校长石元春、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虽然因涉嫌学术造假而屡遭检举、质疑,却依然稳坐院士的宝座;相当比例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顺风顺水地当上了院士,风光于政、学、商诸界。
作为“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两院院士的评选无异于风向标、指挥棒,具有无可替代的引领、示范作用。其评选是否客观、公正,不仅事关院士群体自身的尊严和公信力,更影响着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方向和工作热情,甚至海外留学人员的来去选择。
默默工作、不善交际、敢讲真话、贡献卓著的落选院士,涉嫌造假、擅长公关、有权有钱的却顺利当选、风光无限。两相比照,向社会传递了怎样的信号?给公众造成了怎样的印象?
是该检讨、改进两院院士的评选标准、方法和程序的时候了。
本文刊发于2011年10月人民网
早前报道:
屠呦呦获拉斯克奖曾引争议:集体工作为啥只颁给一人
2015-10-05 18:19:24中国青年报
“拉斯克奖评委会很聪明,我觉得太聪明了。”李真真兴奋地有些手舞足蹈。
这位中科院专事科技政策的研究员指着一篇刚看到的文章,为其中一个细节击节叫好——本年度拉斯克奖评委会问候选人:“如果你获得了这个奖,你认为还有谁应该获奖?”
候选人不约而同在自己名字后添上了屠呦呦及其他有贡献的人。“这是基于同行认可的选择过程。”李真真说。
李真真感慨于这一环节设置的智慧,当游戏落幕,屠呦呦一人登上了领奖台。
伴随着屠呦呦斩获国际大奖的欢呼,国内的质疑声同样强烈,一时“誉满天下,谤满天下”。
无数人纠结于这样一个“悖论”:一边是这样重大的成果往往是一个团队合作的产物,是集体贡献;一边则是重大的国际科技奖项一般都是颁给个人。
而在李真真看来,屠呦呦争议折射出了中西方评奖文化冲突,其背后,则是我们长期以来对科学家个体原创思想的忽视,而这恰恰是科学创新的本源。
我们的传统是讲集体主义,西方是突出个体
“这是集体的工作,为什么给她一个人?”
“为什么大奖只颁给一个人?我也做了重要贡献。”
……
连日来,在科学界知名网站科学网上,类似的疑问所激起的讨论跟帖络绎不绝,一句“屠呦呦能获得大奖,是一个团队努力多年、经过190次失败的结果”的总结回顾,更是被各方广为引用,这一话题也引起不少大众媒体的关注。
在李真真看来,出现这些质疑主要是因为大家对西方评奖制度不了解,“我们的传统是讲集体主义,特别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强调的是集体而不是个人,‘成绩是大家的,功劳是集体的’;至今,国内科技评奖依然主要是奖励项目,科学家的名字多是以一个集体的形式呈现。”
西方的科学传统恰恰与此相反:大多奖项都是突出个体,科学奖励源于对科学发现优先权的承认,这是来自于科学追求独创性的内在逻辑。首先就是奖励“优先权”:即关注在重大的科技成果中,谁第一个提出思想或者方法路径。
李真真就此阐释,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学科细分,现代重大的科学成就,往往都必须凝聚集体力量和智慧,但西方之所以一直坚持把重大奖项给予个人,“就在于这是对一个基本科学理念的回归,科学的进步缘起于独创性的思想。”
屠呦呦这次获奖,拉斯克奖评奖委员会的三点评奖依据为此提供了最佳注解:一是谁先把青蒿素带到523项目组;二是谁提取出有100%抑制力的青蒿素;三是谁做了第一个临床实验。
“美国人不会把奖颁给一个具体做事的人,而会颁给告诉你做这件事的人。”在李真真看来,拉斯克奖评委所宣扬的这一理念,国内还有一个熟悉和接受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屠呦呦争议’也提供了一次科普的机会”。
事实上,获奖引发争议不仅仅出现在中国。
李真真介绍,这种状态在全球科学界很正常,诺贝尔奖的奖励中也同样出现过不少争议。
然而,西方更多争议的是“优先权”的认定,到底是谁先提出创新的思想路径。比如日本去年获得的诺贝尔奖也曾引发学术界讨论,其中争议的正是与德国科学家谁来占有“优先权”。
“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一种科学发明完全出自一个人,为什么到了中国,类似的重大奖励就必须摊到每一个参与者身上才算公平?”一位学者撰写的反思文章激起了不少共鸣,“我们仍然对过时的平均主义、平衡观念心向往之,仍然没有树立起成熟的获奖心理。”
多奖励个人才是国家创新的源泉
对于个人获奖,一个普遍的忧虑是,太强调个人会导致科学界在研究中不合作不共享?
李真真的答案直截了当:西方一直强调“优先权”,但事实上,众所周知的是,他们的合作与共享却做得很好,贝尔实验室等一个单位产生若干诺贝尔奖得主早已是科学界的佳话。
多年来,李真真对国外科学奖励运行模式多有研究,她发现,西方科学界打破这一“怪圈”的秘密就在于:研究中每个人的贡献都得到了承认和回报,比如他们的工作在晋级和薪酬有体现,而相关论文也同样被接受。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别敦荣教授对这一观点表示认同。
别敦荣教授认为,“屠呦呦获奖引发争议背后,暴露出的是我国多数科研团队中都可能面临的问题。”
在别敦荣看来,国内的科技大奖获奖署名一般都是多人组成,所以对于核心贡献认定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被包容了,而如果一旦只奖励给一个人,冲突大多就会显现。
“根源就是‘官学不分’”。别敦荣教授对此一针见血。
别敦荣教授分析,当下,国内科技界极少数有职有权的专家垄断着大量研究课题和巨额经费的现象早已广为诟病。有高教研究学者就曾向中国青年报披露过一个典型案例:973首席科学家七成头衔带“长”。
别敦荣教授说,很多成果中,组织者、主持人并不一定是原创思路的设计者和提出者,主持人的思想不足以创新或者他根本没有时间创新,需要由其他参与者来提供,原创性的思想得不到重视,学术至上的氛围难以出现,形成的必然是扭曲的导向机制。
这也正是不少人担心的问题:强调个体价值,或将成为某些行政领导和学术权威攫取学术资源、学术成果的正当理由。
一位科学网网友就此留言,我的导师在课题中贡献最大,但是辈分不够,原本可能在国内大奖报奖署名中排在后几位,如果仅仅奖励个人,那只有等待出局的命运。
“如果不能打破官学不分,简单地照搬个人授奖模式,屠呦呦争议的各类畸变仍将存在。”别敦荣教授说。
李真真则建议,应该建立制度化的规则来认定谁占有“优先权”,“科学研究必须承认和奖励提出原创思想的科学家,多一些奖励个人的,这才是国家创新的源泉,关键是设定合理规则选出让人信服的那一个。”
李真真说,谁占有优先权的确认,在国际上有通行的标准,比如奖励需要科学共同体来认可,发表论文的通过论文引证就可以追溯;或者在学术会议上谈论一个思想或者技术路径,都有严密的记录可以查阅。
她曾对美国建筑师学会评奖进行过专题调研。
该学会所有奖项中最高级别的是金质奖章,设立于1947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金质奖章每年最多只能有1位获奖者,以奖励对建筑理论和建筑实践有深远影响和贡献的人。
李真真介绍,在该项评选公开发布的评奖规范中,对于谁提名、谁推荐和谁接收、谁评审,均有着清晰明确的标准、回避制度。对于利益冲突,政策文本甚至包含了这样的细节:推举者不能是被提名者所在公司的雇员或上级。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