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文/袁志辉
汇率名义上是两种货币的比价,但本质上是两个货币所分别依托的实体经济宏观投资回报率的差异,而港币对美元的汇率又将中国大陆牵扯其中,则将演绎三种货币、三个经济体的经济和金融系统相互缠绕的复杂局面。在国际金融经典理论“不可能三角”基础上,港币在生出第四个角。
美联储加息预期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移,推动2015年开始人民币强烈的贬值预期,最近一波贬值从11月以来累计幅度接近5%,直到1月中旬央行在香港干预离岸人民币汇率及同业拆借利率,贬值势头才被止住。但随后急躁的空头将矛头转向了港币,于是出现了近期港币对美元的快速贬值,乃至引发市场普遍的对香港金融系统的担忧。
1月6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暂停;同日,港元对美元汇率贬值开启。不到半个月,已累计贬值0.65%,在香港严格执行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下是幅度较大的。港岛笼罩在一片金融恐慌中,让萧条的经济环境雪上加霜。
香港联系汇率制的由来已久,是港元与其他货币挂钩的制度。1983年9月,出现港元危机,港元兑美元跌至 9.6港元兑1美元的历史低点,为挽救香港金融体系,港府于10月15日宣布联系汇率制度,港元正式与美元挂钩,汇率定为7.8港元兑1美元。此后稳定下来,联系汇率制度一直实行至今。
作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快速崛起的亚洲四小龙之一,香港以经济和金融系统的开放性著称,挂钩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极大增强了香港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且极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对于国际贸易和跨境资本流动提供便利性,是香港经济和金融继续繁荣的重要制度保障。但是也并非没有缺点,也将面临小型开放式经济体共有的难题。
在国际金融领域,有一个著名的“不可能三角”,即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独立货币政策不能同时存在。具体到香港的制度基础,在国际收支账户完全开放的情况下,施行固定汇率制度的港元,必然要付出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代价,即香港的利率主要由美国货币政策和国际投资者对香港(连带中国大陆)发展前景预期共同决定。
理论上讲,香港经济的开放性非常高,其经济周期波动应该与国际主流经济体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周期基本同步,实际上过去几十年的实践中大部分时段也是如此。所以,如果香港和美国的经济周期具有一致性,那么对应的两个经济的货币政策也具有高度契合度,这样香港并不需要独立的货币政策,联系汇率制度的运行也近乎完美。
但是一旦香港与美国的经济周期背驰,那么货币政策、固定汇率都将面临挑战。比如,当美国经济处于上升周期,在泰勒规则指引下,美联储货币政策处于紧缩周期,利率及美元指数有上行动力。而在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影响力下降,美国GDP占世界GDP比重从1970年代的70%持续下降至如今的20%当世界经济比重持续下降,香港经济受到美国经济的影响程度也在减弱。如果受到其他经济体的猛烈冲击,香港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并与美国经济周期形成错位,在宏观投资回报率走势反向的背景下,市场预期将驱动资本自由流动来实现实际上的港元对美元贬值,并对此前稳固的“不可能三角”施压。
一个经典的案例在于亚洲金融危机时,索罗斯对港元的攻击。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外部经济形势恶化,日圆持续贬值,东南亚国家货币贬值和经济衰退、中国大陆出现通货紧缩,香港经济急转直下,而港府坚守7.8的美元对港元固定汇率,与实际上强烈的内生汇率贬值需求严重不符。索罗斯在汇率、股市双线作战,携带数万亿美元资本金,并带动数倍的国际游资,高杠杆下注,攻击香港金融体系和汇率制度,逼迫港元崩溃。
当时与之类似的经济体,比如泰国果断放弃了固定汇率,并导致汇率和金融危机。港府不足1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根本抵挡不住,所幸在大陆强力的外储支援下,港元躲过一劫,并最终使索罗斯亏损8亿美元。
其次,信用周期的伸缩调整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固性。联系汇率制度较为僵硬,政府需在立法权限下维系汇率水平,限制了政府利用汇率和利率政策来进行逆周期调控的能力。尤其是危机期间,国际储备下降,商业银行放贷能力减弱,信用周期处于收缩阶段,联系汇率下货币发行受限,经济体缺乏足够的廉价资本,结果导致经济进一步衰退,从而加剧汇率内在贬值压力;反之,假如经济过热,国际储备上升,信用随之扩张,货币发行量加大,经济进一步繁荣,从而加大汇率升值压力。信用周期在内外生动力冲击下,偏离均衡状态,但是央行固守联系汇率,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最终也构成了一个非稳态。
这样的案例来自前不久刚汇率崩盘的阿根廷,但事情确实2001年的旧事。货币政策的国际实践中,联系汇率的使用并不广,阿根廷是香港之外另一个少有的代表性经济体。20世纪的90年代的10年里,阿根廷的出口年增长率为15%左右,而进口年均增长率高达28%,严峻的贸易逆差削弱了阿根廷的国际竞争力,也严重制约其外汇储备的收集能力,这与当时央行为保障自由汇兑需要200—260亿美元外储的现实矛盾。2001年金融危机大爆发前,阿根廷国际储备逐年减少,货币发行量随之剧烈下降,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供应量短缺,总需求严重萎缩,导致经济衰退加剧,甚至出现了历史上很多年没见的通货紧缩。央行被联系汇率制度完全捆绑,被逼发行代币债券来代替比索在市场流通。
由于缺乏有效及时的逆周期宽松信用供给,经济加速恶化,并于2003年初爆发了全面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国民经济陷入崩溃。面对比索贬值和经济崩溃的无穷压力,总统被迫宣布放弃已实施11年之久的联系汇率制度。
将视野重新回到目前香港的具体情况。如今香港经济对大陆的依赖性日益增强,在中美经济、货币政策反向的大背景下,香港再次面临与美国周期背驰的困境。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称,至少到2012年时,美国经济对香港经济周期的影响还超过中国内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香港经济已被逐渐吸引到中国的轨道上来,其最明显的标志便是大量的现金和游客从内地涌入香港,内地投资占香港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份额从上世纪90年代末不足1/10,上升到今天将近50%。但是自2015年开始,大陆赴港游客数量,以及香港零售额都已出现明显下跌,香港的房地产价格也从2015年三季度三季度开始出现较大幅度下跌。
随着大陆经济结构调整,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香港经济总需求剧烈下滑,香港经济乃至广义人民币资产都面临资产回报率下降的强烈预期。经济周期背离下,也有信用周期的巨大反差,美元进入加息周期,且居民和私人部门杠杆恢复到接近危机前水平,信用重新进而底部抬升的扩张周期,但是港元却维持短期利率不变,说明传统意义上,外汇流出导致金管局回收港币流动性已经超出以往“不可能三角下”的解释范畴,独立货币政策已经接受挑战。
当然港元的处境显然远比1998年时好,空头的狙击力确实也远弱于当时,但是在中国成长为大国经济体后,且香港经济日益依赖中国大陆的情况下,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尴尬可能会长期存在,因为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的多轨运行,改变了“不可能三角”下制度设计的初始环境。
极端情况下,参考国际上可比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实践,以及资本流动的理论推演,联系汇率制度的未来都是崩溃。“不可能三角”看似组合出了一种相对稳固的平衡力状态,实际上其内在隐含着“第四角”的不稳定因素,当第四角生出,即对这种固有的历史形态构成猛烈的冲击。
(来源:人民币交易与研究微信公众号,获授权发布;本文作者袁志辉,人民币交易与研究论坛成员,现任职安信证券固定收益部。)

超4小时流畅对战!《三角洲行动》深度适配HarmonyOS 6,摸边更持久,猛攻更流畅

破局医保“不可能三角”,商业健康险需从“边缘补充者”到“生态协同者”
这一转变,需聚焦三大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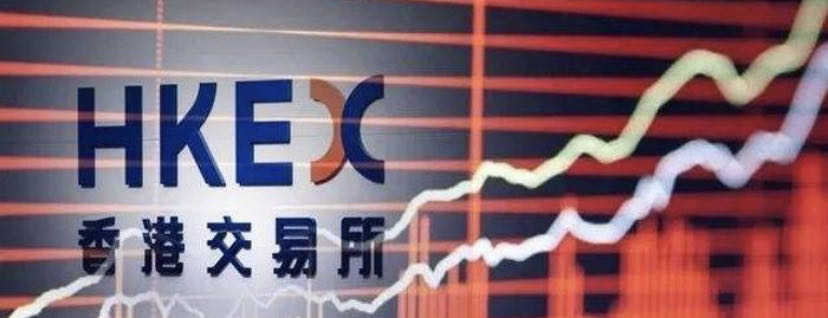
创年内新高后意外回落,港股“日历效应”将如何演绎?
节后首日港股倾向于下跌,一周内“日历效应”将逐渐消散。

美联储重启宽松周期,历史高位的美股将如何演绎?
高成长板块和小盘股能否迎来新机会。

未来赢家不可能是关税壁垒最高者
全球关税战未见终局,但贸易格局已不可逆转地走向“碎片化”。未来的赢家未必是关税壁垒最高者,而是能在安全与效率、保护与开放间找到平衡的经济体。对中国而言,突破围堵的关键在于:以市场换空间,以技术换时间,以开放换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