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aisd}}
AI生成 免责声明
“这是A问题,不是B问题”、“没有问题”、“没有访谈”……对于一个习惯于担心对方不适而迂回给出答案的中国式对话的人来说,神经生物学家饶毅频繁使用否定句式的直率回答令人惊讶。
好在,在第一财经首席顾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力奋对饶毅的访谈中,后者始终态度平和,语速平缓,嘴角常常上扬,带着自然而温和的微笑,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解释不仅逻辑清晰,还非常详细,有耐心。
如果只是看到直率的回答方式,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过去数年间饶毅在中国科学界会树立一种“斗士”的形象。而若是将他回答的态度和内容加上去,你会发现,他是真正的“问题解决者”。
作为2015第一财经·中国最佳商业领袖奖“年度思想家”获得者,评委会评选饶毅的重要理由是他智慧地放弃——美国顶尖学府终身教职、放弃再次提名中国科学院院士、放弃连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智慧地坚持——推动教育体制改革、研究科学史并推荐屠呦呦(最终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作为科学家的精深研究,以及不懈地进行科学传播。
因为渴望恢复中国传统中对知识和智力的欣赏,享受全人类的知识传承和智力成果,2015年,饶毅与神经生物学家鲁白、社会学家谢宇共同创办移动新媒体平台《知识分子》,将科学传播的工作进行得更加深入和与时俱进。
放弃的勇气
2007年,距离饶毅第一次从美国回国已经十余年。其间,他保持了每年一次或者两次回到中国的纪录,到了第十次的时候,饶毅作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他宣布放弃自己在伊利诺伊州西北大学(NorthwesternUniversity)的终身教职——医学院神经科教授,以及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的职位,回到北京大学担任讲席教授以及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一职。
与饶毅同时期回到中国工作的,还有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后者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席教授,回国时放弃了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授予的1000万美元研究经费。饶毅与施一公先后回到中国,被认为是中国科技界吸引力增强的表现。
在很多不同的场合下,饶毅提到了“归属感”:“我认为自己是有归属感的,我意识到自己有归属感。”饶毅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肯定地说。而他承认和接受归属感的方式,就是回国工作。
在作出这个决定之前,饶毅对自己未来所处的环境进行了评估,他确信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样的院校做自然科学的研究,硬件方面的条件与美国相差无几,甚至在某些地方还优于后者。这确保了他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始终能够实现在最核心的工作即科研上的目标。
不过,饶毅知道,更重要的是软性环境,比如,是不是能有一个更好的学术交流环境支持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因为我们的年资比较高,得到的支持一般来说是够的”,而年轻的科学工作者面临的压力则不一样,“既要满足别人对他的评审,又要探索自己的最高追求”。
这也正是饶毅致力于进行体制改革的动因。2013年,一份官方的总结可以窥见饶毅任职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期间所做的工作——带来了空前的学科发展资源、推动了不同层次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以及教学、科研、人事改革产生的变化。
比如,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采用教授预聘制、实验室交接制等方法,在体制上保证年轻的科学工作者有充分的机会获得支持。饶毅本人很快看到了成效,即便是那些已经在美国获得很好教职的年轻科学工作者,也很可能选择到北大工作。
那份官方总结更是没有吝惜笔墨,“从师资队伍、职工待遇、经费规模、论文质量、学生数量等各主要方面,过去六年都是生命科学学院近40年来增长最多的。”
饶毅又一次选择了“放弃”。2013年9月,他正式卸任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面对张力奋“你对自己任职期间的工作打个分”的问题,饶毅给自己的评价也颇高——“做得相当好”。而他自己的卸任,就是自我满意度高的重要一环。
“体制改革做得好,很重要的是院长产生的方式,”他分析说,改变院长与教师的聘任、评审方式,构成了全套的改革,“我一定要下来,如果不下来,这个改革至少是缺了一半。”
批评为了建设
在尚未回国的2004年,他就与鲁白、生物化学家邹承鲁在《自然》杂志增刊上发表联合署名文章,对中国科技部建议管政策而不管经费。2010年,他又与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在《科学》杂志上联合撰文,批评中国的科研文化。
率直、高调的批判,会让未曾和饶毅谋面的人们天然认为他是个斗士,是个“愤怒的中年”,事实并非如此。
饶毅更愿意将自己定义为“温和的改革派”,他的所有批评都是为了建设。在此前的一个访谈中,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提出来的批评都有解决办法,而且大家都知道有解决办法。”
在一篇主题为中国梦、美国梦的演讲中,饶毅更是援引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不但要问中国还有什么问题,而且要问你可以为中国解决什么问题”。
他认为,回国来参与工作,可以推动中国解决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很明显的问题,即使是解决很小的问题,也是贡献。
饶毅善于利用博客,从2007年6月开始,他在科学网开设博客,且更新频繁,还带动了一批科学家撰写博客。查阅他的博客,所涉及的内容涵盖科学、文化、社会诸多方面。饶毅秉承一贯的直率的性格特征,直言不讳的博客为数不少。施一公就会因为个别时候评论不准、骂错而替他捏一把汗。
说到公开发言、分享的动机,饶毅回溯了早年的研究时光,在迅速掌握了做研究的要领之后,饶毅获得了大量的私人时间。“我从32岁开始,就不上晚班,周末也基本不去实验室,除非有特殊情况。”他用大量时间阅读,之后发现,这是个让自己舒服和愉快的事情,却没有对社会产生价值。
“中国的科学文化比较薄弱”,饶毅渴望将自己的阅读成果中的一部分回馈社会。
2015年,饶毅和鲁白、谢宇共同创办了移动新媒体《知识分子》。三位科学家相信科学传播的力量,他们希望知识分子过上“智识生活”。
鲁白认为,知识分子是更追求智识生活的人,表现在思维具有批判性、具有社会意识和责任感,“觉得应该把社会往前带,这批人必须是敢说真话、有诚信的人,追求真理的人,尊重不同意见的人,要有普世的文化价值观。”
从专访中国诺奖得主屠呦呦开始,其微信公众号连续推出相关文章,其中饶毅对屠呦呦科学成果的解读,阅读量达到数十万,两天之内粉丝增长了2万名。事实上,早在2011年,饶毅就在博客中发布了对屠呦呦和张亭栋从中药中发现化学分子成就的解读。有评论说,正是饶毅等人的研究,推动了屠呦呦的获奖。
“我们用相当强的科学精神在做这个事情”,饶毅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肯定地说,《知识分子》的门槛在于,态度严谨,做的不仅仅是科学知识,而且是整个思想的梳理和批评,“很有趣性,这个可能比一般人做得好一些。”

AI4S科研基础设施路线图亮相,打通科研智能化“最后一公里”
当人工智能与基础科学深度融合,科学发现的新范式正在开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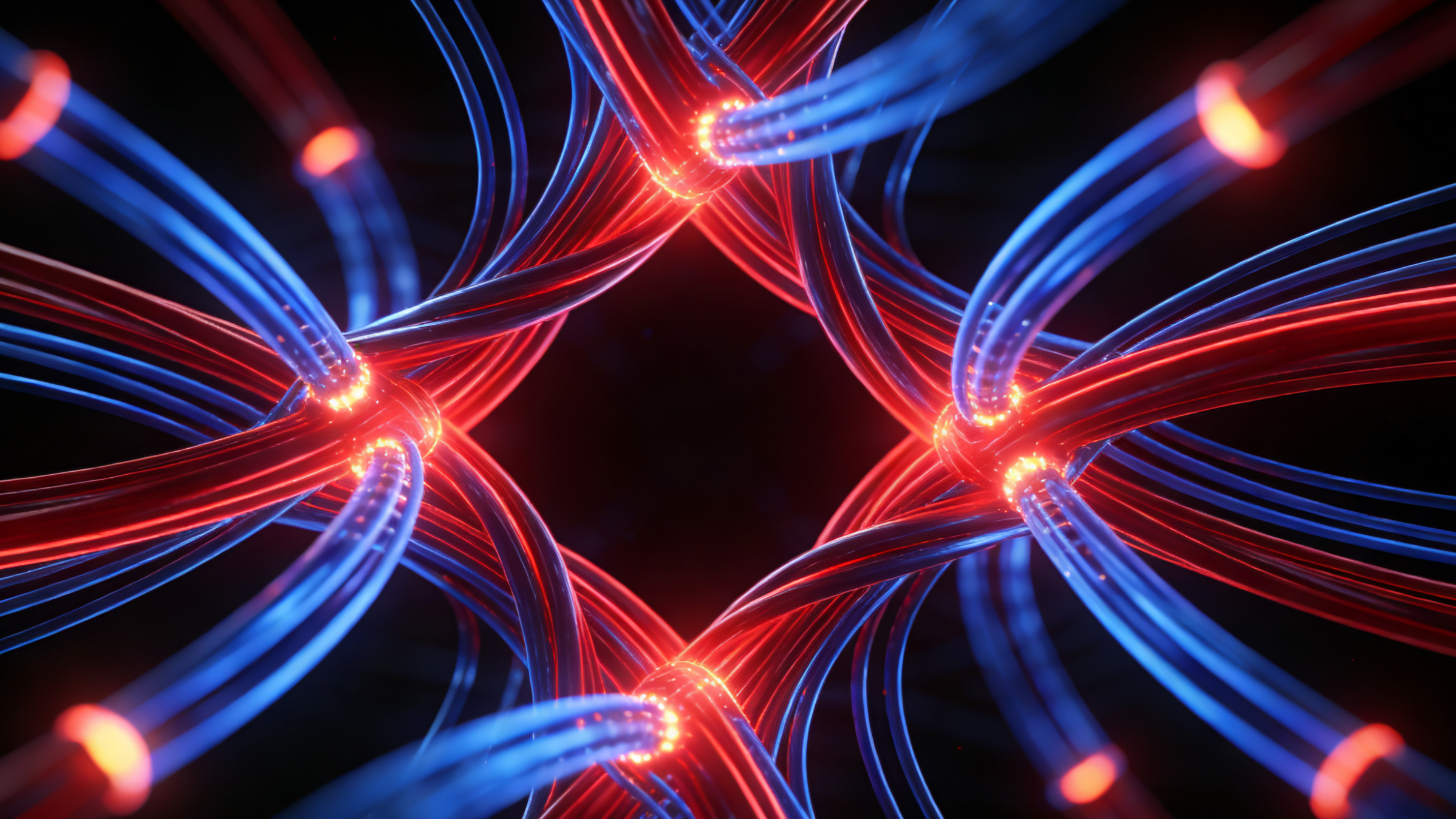
我国全超导磁体刷新世界纪录!这些实验领域将受益
全超导磁体作为现代科学研究的“眼睛”,具有极高的磁场强度,且能耗极低。强磁场已成为材料科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多领域前沿探索的必备条件。

大三甲陷在数据里:AI论文数量飙升、信息科被动转型、半条命交给大厂
三甲医院临床医生的科研重点正从传统药械研究转向真实世界数据、人工智能模型和医疗智能体研究。

报告:全球超半数科研人员科研时间遭行政事务等严重侵蚀
全球已有58%的科研人员在科研中使用AI工具

科研突破只需几小时?美国的AI“创世使命”还面临三道门槛
“钱从哪儿来”始终是计划推进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