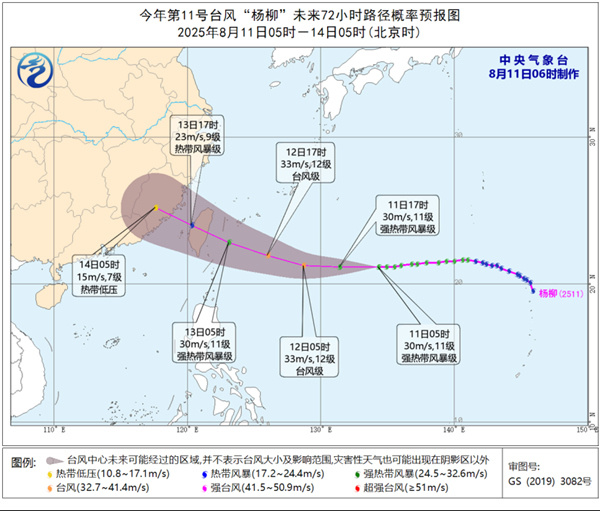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今年上半年,一本台湾“统左派”(主张两岸统一、兼具左派政治主张)人士的回忆录《无悔》频频见诸大陆文化媒体的书评。书的封面上对口述者的介绍是“‘二二八事件’当事人、台湾最后一个政治死刑犯”。籍由此书,陈明忠先生开始为大陆的现代史、台湾史研究界所了解。
年轻时的陈明忠
陈明忠出生于1929年,在日据时代读完了小学和中学。比他年长、不满日本殖民者歧视压迫的台湾青年,之前奔赴大陆求学或参加抗日者多有之。后来当过台湾省主席、台湾地区副领导人的谢东闵,就是在中学时代反感日本教师对中国的丑化、对台湾学生的侮辱(称其为“清国奴”),遂在1925年,即中学的最后一年,借道日本赴大陆求学的。因蓝博洲的《幌马车之歌》一书、侯孝贤早期电影《好男好女》而为大陆读者和观众所知的基隆中学校长、地下党人钟浩东(钟和鸣),中学时也曾因为在课堂上偷偷读大陆作家的作品,被日本老师以“清国奴”辱骂,从此觉醒,后来在抗战军兴的1940年1月,抛下日本明治大学的学业,带着妻子蒋蕴瑜和表弟赴大陆参加抗日。据史料记载,在抗战结束前,在大陆的台胞达到约10万人。
陈明忠出生也晚,等到其民族意识觉醒时的中学时代,日本已将战败。与民族意识同时觉醒的还有阶级意识。作为地主少爷,他觉得佃农对他说话时的巴结态度,与“三脚仔”(“皇民化”的台湾人)对日本人的谄媚没什么不同,因此有了朴素的社会主义意识,“觉得自己也不应该欺负人,甚至,世界上根本不应该有压迫存在”。
光复之后,台湾青年爱国热情高涨。陈明忠回忆说:“街上十字路口旁常有二三十个年轻人,围着一圈弹风琴一起学‘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到处也都有自动教人学国语的小型团体。”
而这些年轻人,后来经历了抛弃国民党、走向共产党的过程——“两年后‘二二八’事件发生,我在‘二二八’最后一役之地的埔里看到了当年教唱国歌的那些人围在谢雪红旁边,听谢雪红指挥的情形。再经过三年,白色恐怖肃清全面展开,我又在‘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里,看到了那些人被枪决前的最后一幕。”这一段概括性的回忆令人动容,也是陈明忠对他这代台湾左翼青年的定论——“这就是那批爱祖国、爱人民的热血青年的下场,我一直没有忘记他们。日据时代反日,光复后反国民党,这样的年轻人都是时代的先觉者。”
陈明忠参与台中地区的“二二八”,虽非核心主事人员,但也保留了一些见闻,可与其他方面的记述形成对照。比如,一部在美国出版的《瀛海悼孤魂——二二八事变真相纪事》收录了“二二八”事件中幸存的外省籍军民的回忆,其中提到驻扎在台中的国民党军宪兵及联勤被服厂官兵共五六十人,在同当地民众相持两昼夜后弹尽粮绝而投降,旋即被全部枪杀,而整个台中被打死打伤的外省公教人员达上百人。
而陈明忠的回忆却大相径庭,他说,台中民众与驻军交战最激烈的教化会馆这一役,是驻军家属哭求之下, 驻军才投降的,投降的有一百人左右,被“带到学校统一管理”。至于打外地人的情况,他说确实有,但属无业游民所为,而他所读的台中农业专科学校学生保护外省籍老师的事例也有很多。
“二二八”遭剿肃之后,台湾本土的左翼青年很苦恼:出路在哪里?之前,大陆出版的《观察》、《展望》等杂志已经对他们的民主意识起了启蒙作用,而大陆上战局的变化让陈明忠们知道“原来祖国有两个,一个是现在欺负我们的、以国民党政权为代表的白色祖国,一个是要打倒国民党政权的、以共产党为代表的红色祖国”。同一时期参加台湾地下党、后来走向“台独”的陈英泰近年也回忆说:“那时候不管有没有参加(地下党),想要寻找一个地下组织,一个能对抗国民党的组织,是很普遍的事情。”
台湾共产党在早期,属于日共的一个支部,这是共产国际在日据时代的安排。台共组织在日据时代曾遭全面破坏。光复之后,张志忠、蔡孝乾等中共系统的台籍干部被派回台湾,与原日共系统的谢雪红等台籍共产党人重建台共,此即中共台湾省工委。
共产党力量在“二二八”事件中就已初露,最显眼的是谢雪红领导的台中“台湾民主联军”和张志忠领导的嘉义“台湾自治联军”这两股武装力量。“二二八”之后,谢雪红潜往大陆,张志忠等人转入地下,徐图发展。
“二二八”时,台湾的地下党人还只有80多人。在“二二八”之后那种苦闷而寻求出路的心情驱使下,大量台湾青年靠拢地下党及“读书会”等外围组织,1948年时地下党员已有400多人;到了1950年国民党实行全面逮捕时,据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后的交代,已有1000多人,而这还不包括很多随国民党军政机关来台的地下党员——后者的关系,未必全部掌握在蔡孝乾手中。
例如,中共秘密战线的重要人物、1949年后武汉首任市长吴德峰的女儿吴持生曾经回忆说:“母亲说有一名我党潜伏人员,在国民党中任中将,由于他身份隐秘,直到被敌人处死也没暴露。所以他死后,妻儿生活悲惨、受人歧视。直到解放后很多年,他女儿想起父亲当年交往的朋友建国后职位比较高,因此怀疑父亲当年是不是共产党的谍报人员。后来她父亲的朋友帮忙找到党内资料,发现里边赫然写着她父亲的信息,还特意提到:‘该同志妻儿失去下落,如果找到,当以烈士家属厚待!’”从被处决时身份仍未暴露这一点看,这明显不是蔡孝乾被捕后供出的吴石、陈宝仓这两名中将,而是以其他原因被处决者。
《无悔》书影
随着国民党1949年5月在台宣布戒严,军法机关开始大规模罗织搜捕,加上当局收紧入境台湾的限制,细化户籍调查,在台地下党人及与其有关联的左翼青年大多被挖出。1950年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就说:“在这个情况(实施入境办法)之下,‘共谍’不独不易渗入,即渗入亦不易隐藏。有时且明知其为‘共谍’而故意让其潜入,以便从而探出其整个组织,而加以全部破获。所以在一九五零年春夏间,中共虽准备得很充分,然终于不敢贸然犯台者,他们的渗透战术无法在台施展,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重大的因素。”(陈诚回忆录)
去年台湾出版的《无法送达的遗书》一书称,省工委领导下的地下党人有95%是台籍人士,这是因为台湾历经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后,台湾民众在语言、文化、生活习惯、思考方式上都同大陆有明显的差别,因此中共即便是在1949年前,也难以像在大陆那样,派遣大量有经验的外省籍干部来拓展组织,而是得全面依赖新入党的本省籍党员作为地下工作的骨干。
而这些在“二二八”之后加入地下党的台湾年轻人,大多没有领教过白色恐怖的手段,没有地下工作的经验,对共产主义也欠缺深刻的认识,很多人一被系狱,刑求之下,难免开口招供或表示“悔改”,或者,在恐怖气氛中不待军警上门,就前去自首。
《无法送达的遗书》收录的燕巢支部案中被枪决的黄温恭、台南市委会案中被枪决的曾锦堂等人就是如此。黄温恭在1951年自首,但隐瞒了自己发展童年玩伴陈廷祥为党员一事,后被查出“自首不诚”,初判15年徒刑,后被蒋介石改为死刑。黄温恭是一名牙医,自首时已有妻儿。其写给儿子的遗书中有“我的心窝儿,乱如麻,痛楚得如刺,如割”这样的表述。而22岁的曾锦堂担任过台南工学院附属工业学校支部书记,在家书中甚至写道:“儿相信神圣的法官不会冤屈一个年轻无知的学生”、“政府对于我这无知的青年学生采取非常宽大的措施,决不会处予什么重的刑罚”。
于今视之,这些纠结、幼稚与求生意愿,都是人性的正常表现。甚至对于一些地下党人刑求之下供出他人之举,被供出、被枪决者的遗属,在台湾“戒严时代”结束后面对先人的这些曾经的同仁,也表示了宽宥。
但陈明忠在“二二八”之后加入地下党的台湾青年中,属于最坚强、最不屈服的一类。由于掌握他组织关系的同志没有招出他,陈明忠不论如何刑求,坚不吐实。坐老虎凳时,砖头一块块往上加,他都不承认参加过地下党。刑求者说:“再加一块,你的腿骨会断。人可就终身残废了。”他就随便说自己参加过一个子虚乌有的“社会革命党”,最后被归入杂案,判十年了事。
陈明忠回忆说,判决前,他在狱中遇到的台中市地委委员、在大陆当过东江纵队团级政委的张伯哲,身份暴露,自知必死,但每天都很平静,好像等待的不是死亡,“我问他:‘你不怕死吗?’他说:‘孔子不是说过吗,朝闻道夕死可矣。’对他来说,‘道’就是共产主义。”陈明忠说,看到冯锦东、钟浩东、张伯哲这些坚定的共产党人临刑前的勇敢与坚定,让他下定决心,要跟他们走下去。
陈明忠后来应侯孝贤之邀,在《好男好女》中饰演蒋蕴瑜之父
但这种信念,若没有理论的指引,是无法坚持下去的。“戒严”时期之初被捕的台湾地下党人,大多并没有深刻的政治认识,多是凭着一股“反国民党”的想法加入了地下组织。其中像陈明忠这样的幸存者,在绿岛监狱时,抛开政治学习课教材《毛泽东思想批判》中的所谓“批判语”,只读那些被大段引述的毛泽东的话来学习共产主义思想;还去偷图书馆里的《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等小册子;陈明忠甚至买来《物理入门》《化学入门》《自然科学辞典》等书来思考辩证法;他还托人高价买到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莫里森·多布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通读三四遍,了解封建主义是如何演进到资本主义的,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这种自我修养,让陈明忠出狱之后,在台共党人的幸存者中成为异类。据他回忆,那些自首者、坐牢后“自新”者,有的后来办养鸡场发了大财,有的做咸鸭蛋也赚了不少钱,但大多不再涉足地下政治。而他还是想搞政治,“只要我生活稳定下来,我不会放弃年轻时代的理想”。他在制药业当职业经理人,事业上升的同时,找资料、找书读,托书店老板买日本左派的书,买日本杂志了解大陆的情况,甚至买复印机偷偷复印资料散发出去,还投身党外运动,最后在1976年,因牵扯进非国民党籍“立法委员”黄顺兴被策动去大陆一事,二度下狱。而这一次的刑求,比第一次坐牢时更为酷烈,但他也未认罪招供。刑讯者说,能熬过刑求四个阶段还不认罪的人,他是头一个。当局原拟以颠覆罪名判他死刑,最后因国际压力巨大而改判十五年,直至1987年获准“保外就医”,1988年减刑,从此之后以“不是蓝不是绿而是红”的统左派身份,再现于台湾政治舞台。
“戒严”时代,省工委各地支部陆续被破坏、十四五万人被捕、近万人被处决后,中共在台的地下组织已经无存。因此,第一次坐牢出狱后,陈明忠事实上已同中共不复有组织关系,他之后的“统左”政治活动,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辨,全属对青年时代形成的信念的坚持和忠诚——而这种坚持和忠诚,在台湾岛上蓝绿变换的光谱中显得特别孤独。
《无悔》一书中还披露了一些珍贵的史料。例如,1952年,国民党军偷袭福建莆田的南日岛,俘虏了800多名解放军回到台湾。大陆史料中记有此事,但没有公开过这些被俘官兵的下落。陈明忠说,其中的军官一开始就被枪决,狱卒甚至剖出其肝脏到面馆去煮了吃;余下的士兵则因谋划暴动抢船回大陆,失败后也有至少上百人被枪决。
(图片来自网络)
如需获得授权请联系第一财经版权部:banquan@yica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