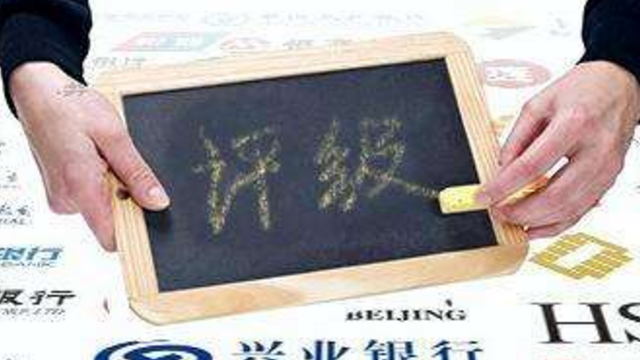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去年以来特别是今年,原来农商行的既有客户被四大行、股份制银行抢走,我们的客户流失非常严重。”华北地区农商行信贷部总经理刘勇智(化名)对第一财经坦承。
面对资源和成本优势明显的大中型银行同业竞争,农商行只能“以退为进”,在既有市场定位基础上进一步下沉,将小额贷款推向更接近农民、居民的地方。在经济下行期,小额贷款反而遭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小。
农商行困境:大中型银行客户下沉
刘勇智所亲历的农商行经营环境变化,正是银行业已经打响的市场化改革战役。
2015年推动了近20年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入“最后一公里”,央行连续五次降息,并于10月24日取消了存款利率上浮管制,自此,利率市场化基本完成,商业银行揽储自由定价、充分竞争。同年5月1日,存款保险制度正式实施,商业银行、农信社、农村合作银行等银行机构须缴纳存款保险基金,这意味着银行不再“大而不倒”。
金融改革急风骤雨对银行经营形成倒逼,商业银行“坐吃利差”的盈利模式倍受冲击。与此同时,在经济下行、结构调整的进程中,实体企业信用风险暴露,银行不良风险持续飙升,截止到今年2季度,银行业不良贷款率1.75%。
诚然,经营环境变化是银行业共同无法避免的“风云变幻”,但在银行阵营中,相对于五大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以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为代表的中小银行经营管理、抗击风险能力更弱。记者多地调研发现,在一地区的客户市场格局,已经形成了四大行服务大型央企、国企、政府平台,股份制银行差异化定位中型企业、特色产业,城商行瞄准地方性国企、小型企业和城市居民,留给农商行和农信社则是被“瓜分”之后的中低端客群。
如今,这一“食物链”却正在重新进行分配。除了银行业普遍经受的经营压力,农商行确实面临更严峻的发展困境。“我们的很多高端客户被四大行抢走,因为他们本身有业务、利率成本优势。”刘勇智说。
自去年利率市场化完全放开以来,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当地四大行、股份制银行的客户策略向下延伸,原来被排除在外的“长尾人群”纳入大中型银行的“盘中之物”,抢走了农商行很多的既有客户群体。
在一家农商行营业部网点,记者随机采访的一位正在等待办理贷款客户表示:“哪家银行门槛低我们去哪儿做(业务),哪家银行方便去哪儿做(业务)。”相对当地四大行而言,在农商行贷款业务的门槛较低,但贷款成本高。
事实上,客户所说的农商行贷款率高也是“情非得已”。刘勇智解释称,农商行由于网点多、人员多,本身运营成本和管理成本高,因此贷款定价要高于四大行,一般客户从农商行贷款利率成本在8%左右,而在四大行利率成本仅5%—6%,对比下来,2%—3%的贷款成本对于任何客户都不容小觑,客户自然选择成本低的银行。
除了来自银行之间的同业竞争,农商行的经营环境更是随着金融主体的多元化而日益艰难。 近年来,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村镇银行等基层金融组织深入农村金融市场,给农民贷款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空间。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崛起,以宜信为代表的P2P平台、网商银行等新兴民营银行专门推出针对农村市场的金融产品,纷纷开拓出以线上贷款技术和大数据风控模型的路子,来破解农村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长期顽疾。
中国农业大学金融系主任何广文表示,在利率市场化的情况下,银行利差收窄,而且农商行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不管是在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除了银行之外还有其他的金融机构,特别是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
农村金融还有多大空间?
面对资源和成本优势明显的大中型银行同业竞争,农商行只能“以退为进”,在既有市场定位基础上进一步下沉,开辟农村金融、社区金融——这些大中型银行触角尚未延伸的空白市场。
事实上,如何进一步开辟农村金融市场,对农商行而言是一个紧迫的命题。从现有的存贷款数据来看,农商行在体量上还不是服务“三农”的主角。截止到今年3月末,农商行涉农贷款余额4.9万亿元,较2007年增长262%。尽管农商行在近十年间涉农贷款以超过20%的年均增速快速增长,但对比银行业整体涉农贷款金额,截止到3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不含票据融资)余额26.8万亿元。农商行在涉农贷款体量还不如整个银行业水平的零头,占比仅为18.28%。
眼下,进一步服务下沉,深耕农村金融市场,已经成为农商行生存发展没有选择的“选择”。
但情况也并不那么悲观,在刘勇智看来,农商行在网点和服务下沉,可以给农户服务更细微,将服务延伸到国有大行不可能覆盖的乡镇甚至村。在农村,村镇银行目标客户与农商行定位有交叉,但村镇银行实力与农商行无法抗衡,不在一个量级。
农商行由农信社和农村合作银行转制而来,由于农信社被定位于主要为农户提供服务的合作金融机构,转制成功的农商行体制机制变化,但沿袭了服务“三农”的使命基因。
小额贷款是鸡肋还是甜头?
既然坚持服务“三农”的定位始终未变,为何有着贷款需求的农民与资金供给方之间总是遥远呢?
一位有着多年农村金融经验的西北农商行副行长对记者表示,第一,获取农村的信用很难,很多农户都是信用的白户,单靠一家银行建立起农村的信用体系非常困难;第二,在农村设立银行经营网点相对于农村的金融密度很低,相较于城市,在农村建立网点的经营成本很高,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
这一问题反映了目前农商行发展农村金融面临的普遍瓶颈。
记者从山东某农商行了解到,对于投入产出问题,该行利用风险评级和业务贡献度的权重对农户贷款定价,其中风险评级权重占比60%,业务贡献度权重占比40%。一名乡村信贷员的人力成本年均5-6万元,在当地农村每2000名村民由一名信贷员维护。在贷款品种上,该行侧重采取抵押、担保方式,保证类贷款占主体。
可现实问题是,一直以来,农民贷款的主要问题是抵押物不足、缺乏信用数据、受自然灾害影响大、现金流不稳定等。银行本身是经营风险的机构,如何在农村信用体系不健全的条件下控制风险,扩大农村市场呢?
“在农村地区,商业银行很难通过一种产品或服务,同时协调贷款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经营成本高、风险大之间的矛盾。”上述西北农商行副行长告诉记者,他所在的西部省份本身土地广袤,有的偏远地区一个信贷员骑摩托车跑一天只能跑一个牧民,如此下来,银行服务年均贷款需求几万元农民的成本很高。而在农村主要以农户开展贷款单位,难以采取规模化、批量化的授信方式。
在农村小额贷款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农户之间的信用担保模式,即农户互联互保,这种经验主要依托于一个小范围内家族、氏族、群族的社会,这种方式天然适用于农村。
以某农商行推出的“农户担保+互助金模式”为例,5名农户之间互相担保并组建互助金,每户根据贷款额度缴纳5%的保证金,签订保证金协议,规定一旦有人发生风险,其他农户共同担保以保证金偿还贷款。
除了针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农户贷款,在城市,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也是农商行另一重要客户群体。大企业贷款规模大、批量化运作,但农商行毕竟很难拼得过成本和资源强势的大行、股份制银行,小额贷款的农户、居民和小企业主类客群更像是农商行门当户对的选择。
“这轮经济结构性调整,信用风险暴露谁也跑不了。”刘勇智告诉记者,银行业的不良压力困扰着农商行,由于经济调整尚未见底,下半年或者明年不良压力持续加大。
不过,硬币的另一面是,小额贷款在经济下行期更耐得住考验。刘勇智解释,本轮经济周期对每个市场主体的影响客观存在,企业流动性普遍收紧,但对小企业影响并不大。而农商行贷款主要是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这些小额贷款群体,一般小额贷款额度20万—30万元,最高50万元,基础产业受经济波动影响相对较小。
如需获得授权请联系第一财经版权部:banquan@yica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