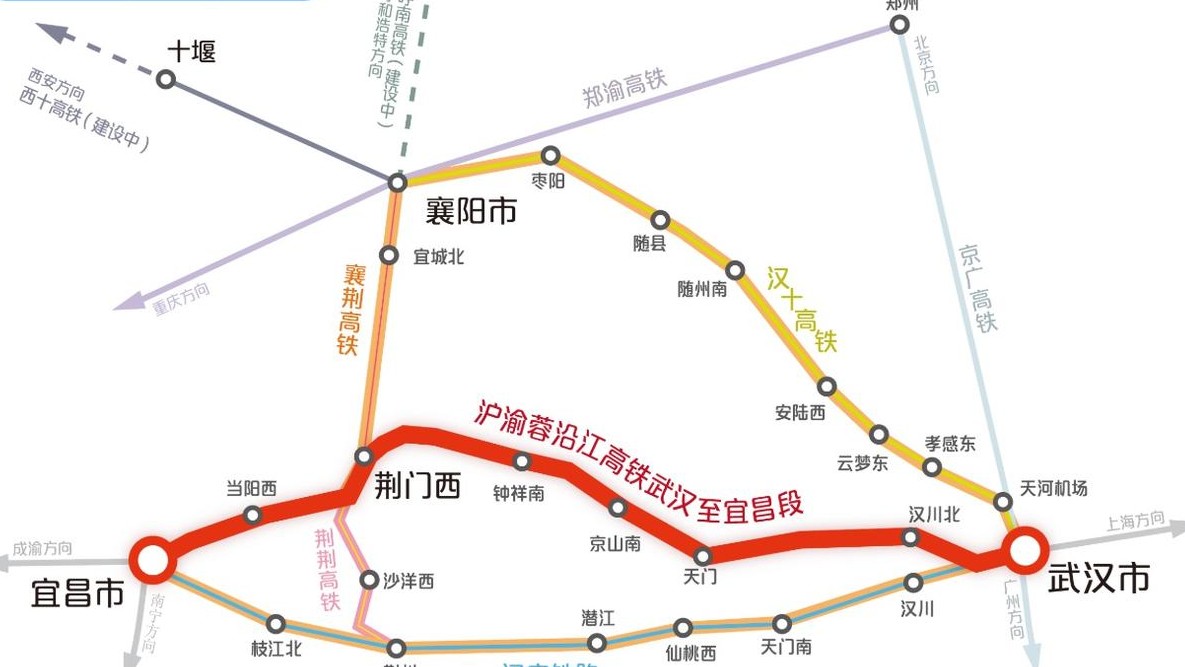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aisd}}
AI生成 免责声明
《长江图》海报
今年年初,《长江图》成了入围柏林电影节的华语片独苗,得到了评审团主席梅里尔•斯特里普的青睐。虽然颠覆叙事的魔幻剧情在媒体场次看睡了不少外国记者,但不妨碍它以重彩水墨的画面斩获杰出艺术贡献银熊奖。
和前年擒熊后大放异彩的《白日焰火》不同,《长江图》没有选择趁热打铁,而是经过又一轮后期,从2K升级到4K版本,尽量还原胶片质感,旁白去掉了三分之二,声效也做了更丰富的处理,一切妥帖了,才在9月8号郑重其事地面见观众。
公映前夕,导演杨超和宣传团队连轴转作影片点映,途经武汉、杭州、重庆、深圳再到上海、北京,放映和讲座间隙扒两口饭,每天醒来都换了一座城市:“我们现在做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这件事,希望一开始排片不要太低,做巨幕也是为了能让更多观众找到它。”
或许是艺术电影的宿命,耗资三千五百万的《长江图》目前排片仍然少得可怜。杨超承认,《长江图》是挑观众的:“和《路边野餐》的清新可爱不同,《长江图》有更重的负担,不管是在文化还是影像意义上,它都是一个疯狂沉重的作品。”
为了这疯狂而沉重的115分钟,杨超前前后后筹划了十年:“长江对我有生理的吸引,直到现在,我还能定定地站在船头看很久很久,缓缓移动中江岸的变化是很有趣的景观。我很难厌烦这件事。”杨超对第一财经说。
侯孝贤御用摄影大师李屏宾操刀影片,呈现了最出彩的胶片画面质感
逝者如斯,不舍昼夜
杨超对河流和船的迷恋,从小时候就开始了。
在杨超的故乡河南信阳,有一条窄窄的河,名叫浉河。它是淮河的支流,不能行船,但可以玩水。杨超小时候长得胖,也不会水,家人严禁他在河边出现。后来,他在离家乡不远的淮滨县看到了淮河的干流,这条平静的河流,能够承载巨大的货船,船进水的时候,几乎是贴着岸缓缓驶过,整个河道都被船身占据。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能行船的深水。
考上北京电影学院之前,杨超复读了两年,第二年快要疯掉。他迂回地先考去武铁电大,在武汉他才真正看到了长江:“武汉是我记忆中最大的城市,长江是我所见过的最巨大、最雄浑的自然的活物。”拍《长江图》和初见长江时的震撼不无关联,杨超说,“那种震撼多次重复,从未减弱。”
站在江边看着浪潮击打岩石,碎成形状不同的水花,每个人对长江的感情也不尽相同。它惊心动魄,是咆哮着奔流和无情地吞噬,它深不可测,是数不尽的险滩和水中的漩涡,它也温柔博大,收藏一切漂泊无依和流离失所。在杨超看来,长江就好像历史本身:“今天的上海和明朝的上海完全不是一回事了,但是今天吴淞口的那些野岸,和明朝长江口的野岸几乎还是一样的,河流很难被人类的生活改变,虽然现在也改变了不少。”
《长江图》并不是杨超第一次拍长江,2004年,他的处女长片《旅程》获得第57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处女作特别奖,其中有两场关于长江的镜头,由于准备地仓促,他对这两个片段一直不太满意:“它让我明白,下一部电影一定要和长江有关,要从入海口一直拍到源头。”
影片中的安陆是偏执而疯狂的修行者
《长江图》里的短诗有十首。杨超说,“高淳压根就是我自己的形象,他写不出顶级的诗歌。”
时间之河,魔幻之河
2006年冬天,杨超带着一台DV在吴淞口蕰藻浜搭上了一条开往铜陵的货船,在长江上漂流了四天。正值岁末年初,两岸万家灯火,鞭炮隆隆,江中一只孤船。杨超把所有衣服都穿在身上,还是觉得冷,“带着水气的寒风渗透到货船每一个角落。”
之后三年,杨超一个人沿江采风。凌晨两点,他站在夜航客轮前甲板看到了长江的另一面,“当眼睛适应了黑暗,能分辨出水纹和远山的铁青色,黑暗被分成了很多层次,大江在你面前展开,然后退去,简直身在银河。”他也曾在渡轮上捕捉到江上的雨雾,“真是鲁迅先生笔下的雨雾,像雾一样的雨,形成的空气的质感超好看,风也够大,江水活了。”
没有故事,也没有剧本,只知道要拍这条河。三年积累的关于长江的琐碎片段最终形成了《长江图》的雏形——《信史四章》,和《长江图》如泼墨山水的画面质感不同,《信史四章》在今天看来极其粗糙,但是隔着银幕,十年前汹涌的风浪堆叠而至,生动而鲜活。
杨超觉得那时候的自己是真的采到“风”了,那是来自古代的风,“我相信这个江河是杜甫、李白笔下的江河,是魔幻的长江。这种相信让我开始拍摄这部电影,不需要去刻意渲染去描述长江的魔幻,而是把魔幻当成日常的事实来拍,这样的水和天,会让人相信所有神奇的事情。”
带着构想和样片,杨超找到了李屏宾。这位和侯孝贤、王家卫、陈英雄等多位导演合作过的摄影大师很快答应了邀请,他在后来的采访中坦言,打动他的最大因素并不是故事本身,而是长江。李屏宾是古体诗重度爱好者,用中国古典山水画的意象来阐释长江的创意令他着迷。他对片方提出的唯一要求是用胶片拍摄,因为“用数字拍摄,只能体现长江五分的美,是一种不尊重。”
电影拍摄过程中经历了柯达公司的破产,数码时代到来,工艺复杂,造价高昂的胶片逐渐成为历史,但它所呈现的光影和温度都难以被数字超越。最终呈现在大银幕上的《长江图》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画,柔和的色彩过渡真实再现了烟波浩渺的长江和沿岸沉淀下来的古代遗迹,让人不时联想到中国古典诗词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亦或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悠远意境。
影片讲述了一个在长江上发生的爱情故事,船工高淳(秦昊饰)从上海出发,逆流而上,乘一条名为广德号的货船,穿越苍茫古渡和巴山夜雨,绕过江中小洲和千年庙宇,在不同的码头上遇到同一个女人安陆(辛芷蕾饰)。在逐渐迷上安陆的过程中,高淳慢慢发现了安陆出现的规律,而他自己逆着女人的一生探索到她的秘密和自己的过去。
在时空交错的魔幻故事里,人们得以从终点到源头,重新认识了不一样长江,目击了那些从未见过的震撼影像,湖州荻港,铜陵和悦洲,鄂州观音阁,三峡大坝,丰都鬼城……开阔的江面,两岸的群山,遗弃的孤岛。
“长江在我们脑海中还是审美河流,是时间之河,并不只是运输水道,并不只有工具属性,中国有这么古老的传统,理所应当有一个这么魔幻的河流。”杨超对第一财经说。
从开机到最终剪辑完成历时四年,在杨超的记忆中,那是一场漫长的折磨和苦役。他需要不断打捞出陷入宏大叙事的自己,删减掉和主体无关的旁根错节,在每一个想要宣泄的地方压抑自己喷薄而出的表达欲望。最终版《长江图》的整体结构和最初那一个完全不同了:“最终成品是最初剧本的投影,就像柏拉图所说的理想世界在现实世界的投影。”
“他在用生命完成这部作品”
按照正常速度拍摄,《长江图》早在2012年就应该完成了。杨超坦诚自己有一股野心,“我们需要的资源太大,这也是我的毛病,总是提出野心极大的计划。”
在杨超最初的设想中,《长江图》剧本有七万字,拍出来有五个小时,“给我一亿的资金,在长江边连续相遇20到30次,每一个码头都带有年代感,目睹时间在江边流淌产生的变化,既是一部心灵史,也是生活史。”
2012年1月3日,《长江图》正式开机。开拍时,李屏宾就认为剧本不可能全部拍完。
“宾哥拍过大商业片,也拍过侯孝贤的作品,对工艺的判断极为精准。我一开始死不承认,在上海的第一场戏就是迎头一棒。”杨超回忆道,“第一个镜头想从吴淞口拍摄,从东海到退回长江的航道,摇到灯火通明的外高桥码头,再慢慢移到一个孤独行驶的小黑船,看完剧本之后宾哥就笑了,但是他没有打击我,说我们试一试吧,最后发现这就是一场灾难,风浪超大,船摇晃个不停,我们连稳定都很难做到。”这场戏之后,杨超立刻醒过来,着手删减剧本,保住了心灵史的部分和交错的时空结构,放弃了生活史和风俗史的一面。
杨超的同学王彧是《长江图》的制片人,也是《三峡好人》的制片,和贾樟柯等第六代导演都有过合作。《长江图》是其中耗时最长,耗费最贵,也最难定义的一部作品。“从剧本角度来说,《长江图》很特别,第一版拍出来的时候感觉特别怪,这是一部从任何角度解读都会非常吃力的电影。” 王彧说,他被杨超的“轴”而打动:“十年去创造一部电影,四年去剪辑一部电影,要么是精神病,要么是没事干。他在用自己的生命完成这部作品。”
一条拍摄船,一条道具船,一条生活船,三条船沿江逆流而上,从上海出发,一直到长江源头楚玛尔河。逆流而上的一百多天,江面干燥,大部分时间静水深流,这和杨超预想中的不一样,超现实的长江需要极端天气:“万重浪,多重风雨的质感没有遇到,是特别可惜的事情。”但他也只能接受这个事实。三个月的航程中只遇到一场雪,这场雪只下了四小时:“我们什么事儿也不干,就拍雪中的长江。我不知道唐朝是不是会好一点。”
在长江逆流而上拍摄,对经验丰富的李屏宾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老天给你什么就是什么,长江水道的不可逆,我们不能总是重拍,只能一直向前。”
在李屏宾眼中,杨超是个很固执的人:“他很执着,去追求一件东西时,可能明知道很困难,但敢尝试。”他也曾坦率指出杨超的人文包袱太重,最初剪出来的两个半小时版本太长。
对于他的意见,杨超表示接受,“我的剪辑到了一个自己很难走出的程度,最后剪辑师大刀阔斧的改变了整个结构,才形成最后的版本。这个版本不完全是我的功劳。”
中国女性比中国男性更勇敢
《长江图》承载着关于生命的终极追问,罪恶与救赎,信仰、宗教和修行,记忆和遗忘,自然主义与现代文明,太过庞杂的符号和象征,超过多数人所能理解的边界。
不少观众看后一脸茫然,杨超也不着急,只是平静地说,“那你得再看三遍。”
他不介意观众把《长江图》当成旅游风情片来看,但对故事逻辑又有自己的坚持。有人质疑王宏伟饰演的角色必要性时,他回答道:“一百个人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这没问题,但是哈姆雷特基本的动作线应该是不变的。”参加访谈时,杨超穿着随意,简单的T恤,牛仔裤,长发束在脑后,和网上硬照的冷峻相比,现实中亲和多了,他的声音尤其温柔,讲起话来也慢条斯理。
导演、大学教师、超级影迷、知识分子,朋友给他冠以不同的名号,但杨超自称是个失意的文学中年:“高淳压根就是我自己的形象,他写不出顶级的诗歌,跟着父亲沿江流浪,在码头写诗,命名为长江图。他是拿诗歌抵抗平庸生活的男人。”
“两岸城市都已背信弃义,我不会上岸,加入他们的万家灯火”,“我厌恶生命的礼赞,悲伤高于快乐,纯净高于生活”。在《长江图》中,这样的短诗有十首,在高淳和安陆相遇的码头出现,每一首都像宣言。不久前上映的《路边野餐》也由诗歌串联,难免被人拿来比较孰优孰劣。杨超希望观众不要把他理解成一个诗人,而是理解成一个好的编剧:“我是个读诗的人,但成为一个出色的诗人要有驾驭汉语的能力,我没有这个能力。影片中的诗歌是我借高淳之笔写于80年代,是故事的组成部分。”
“要么丑陋,要么软弱,要么虚伪,没有神灵能让人信服,所以期待一个女性。”船行丰都鬼城的诗,暗示着杨超对男人和女人的看法。很多观众认为安陆是一个模糊的象征,是水鬼,是游魂,为此杨超不止一次地解释,她是真真切切存在过的活生生的人,“作者的缺陷就会让人物用极致的方式去完成,这个女人是用自己的全身心去实践诗歌,男人只能靠文字抵抗残酷现实,女人直接扑向生活,任由生活伤害她。”如果说高淳是和生活妥协的落魄诗人,那么安陆就是偏执而疯狂的修行者,理解了安陆这个人物,才能理解一正一倒两条相逆的时空线索。
“中国女性的勇敢者都比男性勇敢,中国男人比较难以摆脱对权力的崇拜,难以获得真正的自由。”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明显地产生在《长江图》中那个最令人窒息的场景:三峡大坝开闸。伴随着高频的金属摩擦声,十几条钢铁混合在一起痛苦呻吟,钢筋混凝土搭起的机械巨人宏伟、庞大、黑暗、压抑,那是地狱堡垒,又像是天堂圣殿。水面缓缓上升,大门沉重打开,自此进入另一片水域。三峡水库里,安陆消失了,他们也不再见面。
“我有点崇拜这个金属教堂,太恢弘了,人类制造的伟大事物改变了这个江河。但你又会非常惋惜被人类改变的这个江河,三峡改变了时间的河流的魔幻属性,让神奇的相遇再也不会发生。”杨超停顿了一下,叹了口气:“长江最好的状态是非常急速的流动,浑黄的江水,这才是长江本来的面貌。它理所应当是奔腾的,这才是它最震撼的状态。”
如需获得授权请联系第一财经版权部:banquan@yica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