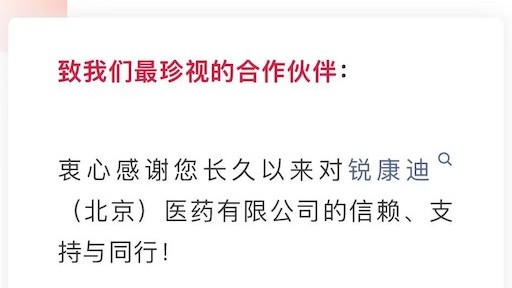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aisd}}
AI生成 免责声明
时隔六年,今年9月,中国又正式推出了新版CDS。现在的CDS修正了过去的主要缺陷,又正值中国金融体系信用风险酝酿发酵和刚兑的松动时期,自然增加了市场对CDS的各种期许。然而,提起CDS,人们不免想起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和有关CDS的种种负面报道。那么,何为CDS? 它在2008年的危机中扮演了什么角色?CDS在欧美市场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汲取?中国重新推出CDS会不会在缓释现有风险的同时引发新的风险?这大概是许多关注CDS市场前景的人想亟待了解的几个问题。
何谓CDS?
CDS属于信用衍生品,它最简单的形式是单一实体CDS。单一实体CDS是两个交易对手针对第三方实体信用风险的一种交易合约。在单一实体CDS交易中,买方(做空方)同意向卖方(做多方)在合约期内支付一定的定期票息,卖方则同意在第三方实体发生违约事件后向买方支付一次性等同于CDS合约名义额的代偿金。从某种意义上说,CDS就像汽车保险,只是它担保的不是驾驶事故造成的风险,而是经济实体的信用违约风险。交易CDS的目的,对买方来说,是要对冲第三方实体的信用风险(比如买方可能持有第三方实体发行的债券);对卖方来说,是要通过承担第三方信用风险而获得投资回报。本质上,CDS代表着一种金融技术,通过它,CDS把现金产品(如债券或贷款)中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分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CDS在美国出现之前,现金产品的风险和流动性是绑定在一起的;CDS出现以后,投资人可以仅就第三方实体的信用风险进行交易,甚至不需要持有第三方实体的任何债务,更不受该实体债务存量的限制。CDS具有重大的创新意义,它第一次为对冲信用风险提供了现实可行的金融工具。
信用衍生品的发展
CDS在欧美市场问世以后,先是经过了十几年的爆炸式增长,之后又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大洗牌,随后则是自2010年至今的艰难复苏。作为一种创新的金融工具,CDS在提高金融机构资本运用效率、释放银行资本金、对冲信用风险、实现套利机会等方面施展了特有的功用,受到投资者的青睐。过去的二十多年,信用衍生品从单一实体CDS发展到量身定制的组合产品(如合成CDO),之后又发展到指数产品,指数CDO以及指数期权产品等等。回顾以往,CDS的发展一直是在市场的呼唤和监管环境松紧之间寻求自身的生存和成长。今天,我国推出新一版CDS的时候,CDS在欧美市场正面临问世以来最寒冷的严冬。由于新监管框架对信用衍生品的资本要求大幅度提高以及自营业务在监管约束下的淡出,做市券商从事CDS已越发无利可图。为此,一些投行几年前就已经退出合成组合产品业务;如今,相当一部分投行又相继退出了单一实体CDS的业务。
始料不及的问题
CDS在发展的过程中的确暴露出一些始料不及的问题,为后来2008年的金融危机埋下了定时炸弹。首先,由于CDS的交易双方不必非持有合约针对的第三方实体发行的债务(所谓“空壳信用”现象),也不受第三方实体债务存量的限制,至少理论上,CDS可以“无限“地派生下去。结果是,其名义额可能远远超过第三方债务的存量总额。在现金产品下,债券发行人的违约风险不会波及到债权人之外;但在CDS之下,同样的违约事件,除了债权人之外,还会波及所有相关的CDS投资人。特别是当后者可能比前者大出数倍数十倍时,尽管就个体而言,CDS没有改变基础资产的风险特征,但在总量上,CDS却起到了传播和放大原有基础资产风险的作用。其次,无论是违约发生后CDS卖方的代偿,还是CDS盯市造成的资本利得(或利损)的交割,都需要交易对手承诺支付。如果交易对手因自身财务状况无法兑现支付责任,这就出现了所谓交易对手风险。交易对手风险在现金产品下是不存在的;但在CDS之下,交易对手风险却是导致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三,CDS属于信用衍生品,需要盯市。当市场CDS的名义额远远大于对应的实体债务存量时,风险溢价的剧烈波动会导致巨大的CDS市值波动;当这种波动通过损益表反映到CDS投资人的资本金状况时,在有大量利损发生的情况下,会导致CDS投资人净资本大幅减值甚至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最后,组合产品如CDO出现以后,为杠杆的使用提供了绝好的工具。合成CDO和现金CDO一道,在2008年的全球危机前,成为投资人大量运用杠杆的场所,为系统性风险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2008年危机的教训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CDS的上述种种风险不幸都得到了应验。2006年,全球CDS的名义总额达到62万亿美元,远远超过了同年全球8万亿美元左右公司债的存量。违约风险由于空壳信用现象被派生和反复复制,加大了信用风险的量级。在盯市的要求下,2008年风险溢价的巨幅波动直接导致许多金融机构资不抵债,如果不是后来政府的救市和美国FAS157会计制度的实施,除雷曼兄弟等大公司之外,将会有更多金融机构或许会相继倒下。此外,盯市直接把交易对手风险充分地暴露出来,导致了雷曼兄弟、AIG等大型金融机构的完结或濒临破产。
交易对手风险还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进一步推动系统风险的蔓延。必须提及的是,在信用衍生品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当中,组合产品杠杆的过度使用起到了引发、推动和致使危机恶化的最为核心的作用。CDO产品,包括现金和合成两类CDO,为大量使用杠杆提供了便利。据估计,由于杠杆的使用和叠加使用,大量以次级贷为基础资产的CDO遭到自股本块到超级优先块的全军覆没。在这场危机中,仅美国金融机构的损失就达1万亿美元左右。
回过头看2008年的全球危机,如果还有一个教训需要汲取的话,就是危机前欧美市场做多CDS的环境可能过于宽松了。过度的多头与有限的空头导致CDS的风险溢价过低,没能反映当时市场正在积聚的巨大风险。CDS的表外处理、过低的资本金要求、对交易对手风险的低估、过于宽松的保证金条件等是CDS做多环境过于宽松的主要原因。可以说, 2008年的危机不是因为CDS做空的存在,恰恰相反,是因为做多的环境太过于宽松、而做空力度不够所致。
一个富有争议的产品
包括CDS在内的信用衍生品或许是时下最富争议的金融产品了。一方面,它代表着过去四分之一世纪最有创新意义的产品之一;但另一方面,它又在2008年全球危机中负有难以推卸的重大责任。然而,CDS和组合产品CDO虽然同属信用衍生品,但就个别交易而言,前者更像是一面没有扭曲的镜子,是对基础资产风险的忠实反映;而后者则要求对基础资产的风险进行重组、调整和再分配。严格地说,2008年的危机既有CDS始料不及的诸多问题,更有组合产品CDO过度使用杠杆而造成的巨大危害。组合CDO的罪过,不是也不应该算在CDS身上;而组合产品也不应因为曾有过杠杆的过度使用而被否定它内在的独特优势。
对中国的借鉴
中国曾经推行过的CDS由于刚兑的存在和产品的缺失,加上监管的认可不足,推出不久便很快淡出了资本市场。在我国信用风险急剧积聚的当下,新的CDS能否有所作为还有待市场各方的协调努力。中国CDS市场除了要规避好空壳信用和交易对手的风险,还必须创造CDS市场发展所需的基本环境。在我国信用市场上,由于非商业因素的存在,违约事件的认定有着明显的不确定性。而二级市场的缺失,使回收的确定无法依赖二级市场的交易信息,而不得不依靠漫长的求偿过程。这些直接关系着CDS的公允定价。此外,监管对CDS对冲信用风险作用的认可,包括对银行资本金释放作用的认可,也影响着投资人对CDS的态度。最后,在中国CDS市场的发展还有赖于不同风险偏好的多样化投资主体的存在。所有这些将关系着CDS市场在中国的未来。(作者为中拉合作基金首席风险官中拉合作基金首席风险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