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aisd}}
AI生成 免责声明
针对高企的杠杆率,中国的监管机构已经采取了从宏观审慎到微观审慎的一系列措施。日前,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企业债务:宏观与行业风险分析”研讨会上,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指出,中国的监管标准已经相当高、监管力度也很大,接下来需要警惕过度监管带来的风险,不要在去杠杆过程中引发更快速的去杠杆。
“中国企业债务:宏观与行业风险分析”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该会议由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院和第一财经研究院联合主办。
中国企业的债务过高问题已经引起全球的关注。在上述研讨会上,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研究办公室(AMRO)近日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企业债务风险的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的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水平和发达经济体相当,但超过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企业债务是国际上的最高水平,越来越多的企业债务通过发行企业债券和影子银行借贷实现。尤其是工业类国有企业,其杠杆率极高,但盈利能力和债务偿还能力远低于非国有企业。
根据BIS数据,截至2016年底,中国的全部债务占GDP的比重为269%,高于235%的平均水平。其中,企业债务占全部债务的65%。
IMF近日发布2017年中国第四条款磋商报告(Article IV)也再次警示中国债务水平上升的风险。IMF估计,中国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债务将从去年的相当于GDP的242%,到2022年升至近300%。
AMRO经济学家许和易(Chaipat Poonpatpibul)在论坛上表示,不断攀升的企业债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中国企业债的攀升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所处阶段密切相关,例如中国以投资为驱动的增长模式、高储蓄率及相对滞后的股权融资等特点。
经过对各个行业企业的金融风险进行研究,AMRO报告中指出,基建、矿产、交通、建筑等行业的债务增长与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成正比,相反,一些新经济领域,例如服务业、互联网行业则用较少的债务创造了更大体量的经济增长。
许和易认为,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企业就会不断扩大投资,债务率居高不下;但若保持低增长和低利率,企业债问题仍无法被解决。
“我们认为中国需要一些改革,通过改革来提高资本的利用率,提高公司的盈利率,也可以增强公司本身的股权融资能力。”他说。
在前不久结束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中央提出要坚定“去杠杆”政策不动摇,尤其是对国企加强去杠杆。
曹远征认为,杠杆率高低不是问题的实质,关键问题是杠杆是否可持续,即企业有无复兴能力和盈利能力。
“单纯的杠杆升高和降低意义不大,若企业可盈利则企业可付息,杠杆即可稳住,否则杠杆垮掉则会有更大的问题出现。”在他看来,如何管理企业的债务问题,是下一步要考虑的核心问题。
“过去的经验是通过破产重组梳理资产负债表让企业可持续发展,但这个经验有些‘疼’,探索是否有更加温和的解决方法是接下来研究的重点。”曹远征指出。
对于业内普遍比较关心的基建行业和钢铁行业,曹远征认为,基建行业是不可持续的,原因并不在于其回报率高低的问题,而在于该行业最核心的问题——债务期限非常短,因此对于基建行业来说,债务期限的延长是最重要的;而关于钢铁行业,曹远征表示,要根据当时的市场情况来看。由于钢材价格的大幅上涨,所以钢铁行业自去年开始已大为改观,负债率大幅下降,目前钢铁企业的债务情况好转,对银行的还本付息能力大幅提高,情况并不像从前大家普遍认为的那样差了。
而关于目前中国的监管状况,曹远征表示,中国的监管标准已经相当高了,监管力度也很大,但带来的问题就是监管的风险。如何在实际监管的执行中将经济周期问题更好的考虑进去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最大的风险是若一个新周期并未到来但却加速退出了原来的周期,这会带来更大的金融风险,所以不要在去杠杆的中间导致更快速的去杠杆。”他说。
如需获得授权请联系第一财经版权部:banquan@yicai.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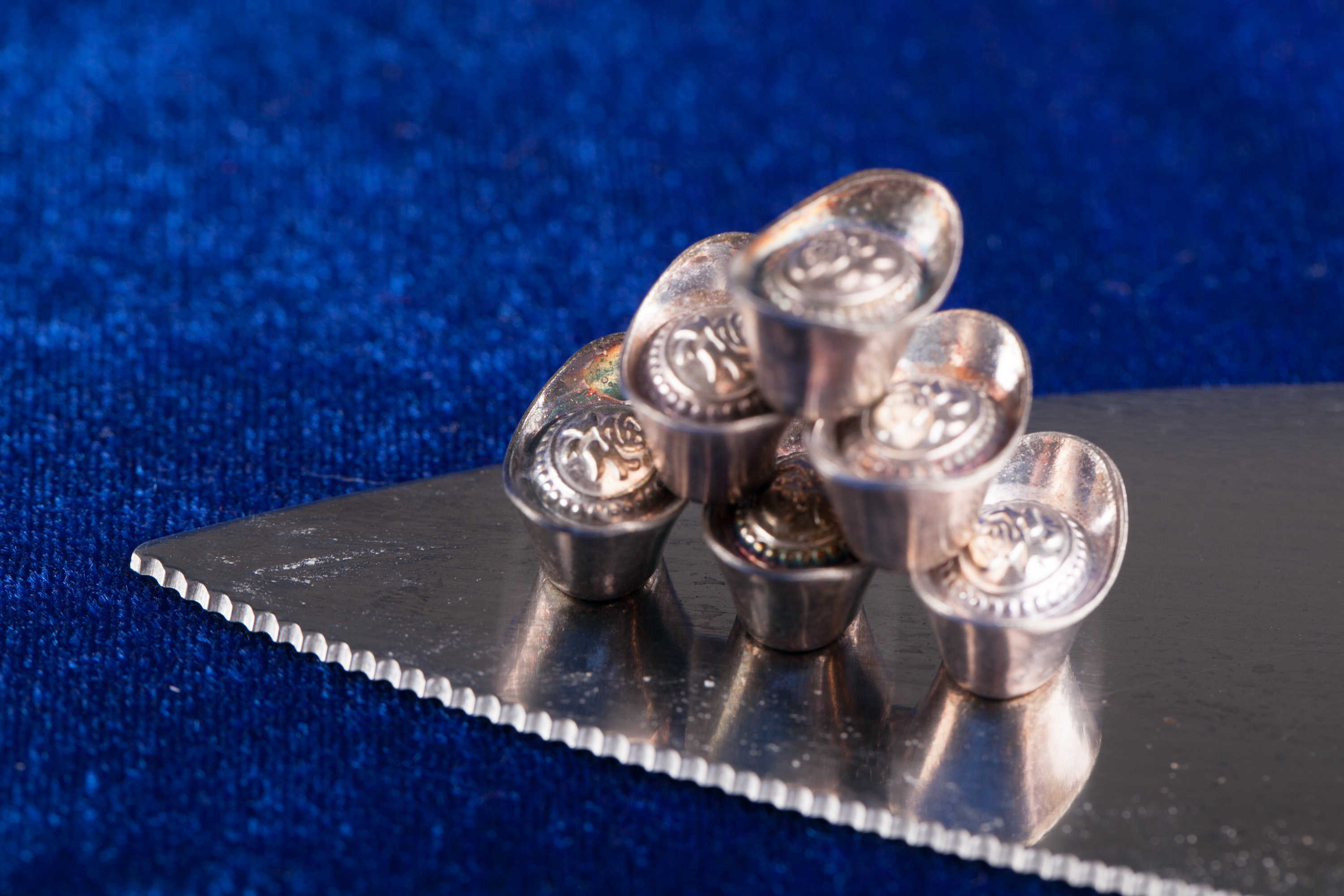
CME出手!白银狂飙后跳水,市场担忧高杠杆风险被引爆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于12日将白银保证金上调了10%后,又宣布将在当地时间12月29日收盘后再度上调履约保证金。

管涛:“灵活高效”的货币政策意味着什么
央行例会将“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替换成“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

6家银行被查,违规向房地产项目放贷210亿元
服务国家战略及实体经济数据不实问题整改资金3538亿。

曹远征:超大规模性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把钥匙
曹远征指出,超大规模性是中国经济集成创新的基础,也是其经济韧性的来源。

沈建光:“十五五”中小银行如何改革化险
中小银行的改革化险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兼并重组或资本补充的被动应对层面,还需要从根源上转变发展模式,重塑核心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