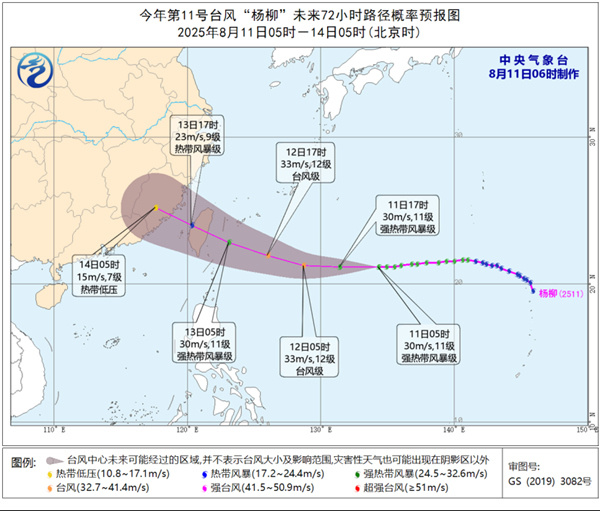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aisd}}
AI生成 免责声明
台湾艺术家陈界仁的影像作品多半沉闷、无声,他本人却是个话痨。
在公开场合,这位57岁的男子总会以台湾腔普通话,快速而清晰地吐出一串串机智妙语。他特别擅长以朴实的逻辑、简单的语言来论证很玄的问题,最终把大家问得捶胸顿足——对啊,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我之前没有想过?
“今天人们的漫想能力越来越被剥夺了,工作一天回家之后看娱乐片,被情节带着走仿佛很减压。没有恋爱的人就看看偶像剧,幻想着谈恋爱,愤怒的人就去看看《黑镜》,看他们怎么去整有权力的人。”他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说,悠闲、漫想的权力被剥夺,是遍及全社会的问题。艺术就是要重新唤起这种能力,把失去的权力慢慢夺回来,让人们重新建构一个情感寄托。
他戏称自己是“佛法左派”,称自己的艺术创作为“乡土科幻”——在现实世界,人人都经历过比电影大片更魔幻的体验,同时这一切又与传统意义上的高科技如此遥远,就在身边的亲友群体中,在最寻常的家庭仪式里。
这些看似戏言,却又从某个古怪的角度,解释了他那些“苦大仇深”的作品。
艺术重新建构情感寄托
日前在北京长征空间展出的两件新作,主要灵感都源自陈界仁的哥哥。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波及,他从一位体面的中产阶层设计师沦为失业者,并由于常年找不到工作而患上忧郁症,2008年病症恶化试图割腕自杀,所幸被友人相救。
哥哥出院后,独居在一个天花板有点漏水的家里。他原本就不常出门,从那之后更加深居简出。那个家逐渐被各种各样的资料、书本、文件夹堆积填塞,包括紫微斗数、《易经》,还有一个个写着“演”“诡”字样的文件袋。陈界仁管那些稀奇古怪、零散的信息叫做“异知识”。
看似没用的知识也许对哥哥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跟艺术家弟弟发来短信说要注意这个、留心那个,仿佛知晓了天机。“这也许就是他重新找回的存在感。”陈界仁说。
今年年初,陈界仁问哥哥,房间里为什么没有装灯,得到的回答是,“那是属于灰尘的世界。”
于是就有了装置作品“星辰图”。他拍下那个灰尘的房间,把摄影照片以卷轴方式呈现,机械动力慢慢转动照片,观众得以凝视哥哥的“异知识”。那滚动卷轴承载的则是艺术家小时候跟哥哥学习冲洗摄影负片的记忆。
“我以前不爱讲这些,好像在消费亲人的苦难。但是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而且其中可以反映出一些整体现象。不仅仅看到悲剧,还有背后的宏大原因。”他说。
失业的哥哥只是台湾地区社会大势之中的一个案例。十几年前的第一波失业潮影响的是工人,第二波就是城市中产。随着全球化不断发展,全世界都在以不同的速度走向社会两极化。
另一件作品“中空之地”是长达61分钟的影像作品,色调暗沉、节奏极其缓慢,分别拍了五组出殡的队伍。陈界仁排演了一场并不真实存在的送葬仪式,看似没有亡者,但仿佛是在给所有在失业潮中被损耗、被牺牲的人们送葬。
作品过半,出现了几十名中年妇女,她们是著名的“华隆女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华隆纺织爆出各种丑闻,随之开始恶性裁员关厂、强迫退休,2012年,50名华隆工人从新竹徒步至台北凯达格兰大道抗议游行。
陈界仁找到她们进行拍摄,在镜头前面只需要一起往前走,同时要喊一句话,这句话请她们自己商议,尽量避免太教条、太抗议的激烈词语。大家不知不觉就出来一句:怎么办,名字没了,怎么办。
“这就是诗学的发生。”陈界仁说。
在影像中,女工的这句话反反复复持续了12分钟。开始时,她们用客家话边走边说,仿佛喃喃自语,观众需要通过字幕才能了解这句话的内容。这句话不断重复,画面切换到每个女工的特写,恍恍惚惚有催眠效果。到后面开始下大雨,她们淋着冷水越说越急,那句没头没尾的话最后几乎变成了怒吼。
观众从开头听不懂客家话,到意识到语言的力量,再到在脑海中留下残响,构成了充满银幕内外的氛围。“这就是从很现实的生命经验出发,走到了艺术发生的时刻。”他说。
哥哥和华隆女工所面临的,其实已经不只是失业的问题,还有一点点丢失的个人存在感。怎样寻找力量重新组织起来,找到新的发展途径?陈界仁认为,艺术是个很重要的解决办法。
“除了要为弱势群体抗争之外,我还想争取更多的空间。当人们有了这些空间就可以冷静下来,可以思考,甚至写出那句诗。”他说,艺术就是要重新唤起这种能力,让人们重新建构一个情感寄托。
“当代艺术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它很难,导致大家看不懂。”他说,“本来也不是懂不懂的问题,而是种漫游、遐想,在既有的知识框架、行为、生活方式、思考方式之外。到画廊,看到什么、记不记得都无所谓,能激发一些想法,甚至只是在这个空间里晃着,就已经很重要。”
陈界仁过去的影片大多基于这种理念而创作,刻意摒弃了叙事、悬疑、趣味,像是制造一幅关于社会问题的风景画。里面的断裂和空隙,恰恰是艺术家最珍惜的。
我跟他坦白,自己在看的过程中睡着了一会儿,他觉得很正常。身边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连续的,走在街头看到的商店、游客都是碎片,各自有各自的小宇宙、小烦恼,这些碎片既独立存在又互相关联。“60分钟也没有很长啊,就是须臾或刹那而已,只是我们总想要更多快感。可所谓诗学和漫游就是这样的,睡醒之后再继续,可以重新看待生活。”他说。
正视历史社会问题
1988年,台湾地区正式解除戒严体制后不久,陈界仁开始了一次长达八年的漫想。
开始,他只是主动停下创作,想要厘清自己与当代艺术的关系,结果一两年过去,他依然沉沦着。他并没有得抑郁症之类的疾病,也没有工作,生活依靠弟弟供养,整日浑浑噩噩,到处游荡。时间过得好像很快,抽抽烟一天就过去了。
陈界仁出生在台北眷村的一个普通家庭,从小喜欢画画和胡思乱想,长大去职业高中念了美工科。可是学校里死板的美术教育又叫他心生厌恶,为什么要画石膏像、菠萝静物,为什么要临摹《芥子园画谱》里树叶的各种皴法?“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它与我的生活是断裂的。本来我画画很开心,突然开始有了分类判断标准,青春期胡思乱想的自由被剥夺了。”他说。
他成长的年代与台湾这个小岛所背负的重重苦难难逃关联:先是日本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然后是国民党近40年的戒严,同时美国官方透过大众媒体对岛民进行全面的冷战文化宣传。这些共同制造了民众的集体失声,每个人都被迫要忘记自己的身份。
在那个特殊时代,陈界仁从学校、图书馆、艺术期刊了解大量关于西方艺术史的知识。从认知上他完全理解诸如“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先锋流派的艺术形式,也很容易模仿,可在情感上,始终都是断裂的。
“其实我们日常很多经验比超现实主义更超现实,但为什么你们成立,我们不能成立?”他说,“现实世界和书本里的艺术为什么如此割裂?那些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这样的人占据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但在艺术史里却好像变得不存在。为什么不可以理直气壮地做艺术?我没有想通。太矛盾了。”
很多事情想通之后就会豁然开朗。在一篇关于陈界仁的评论中,作者认为他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找到了那个盲点。“一个被跨地域殖民机制与国家机器以民主化、自由化、现代化、民族主义等合理化论述所蒙蔽的巨大盲点;这是一个失声的所在,从属于‘内在殖民’的结构。”
简单来说,就是他勇敢地正视了长久以来大家不敢面对的历史社会问题。
1996年,帮他走出八年沉沦的,恰恰是整日闲晃的生活环境。那个小区旁边有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有台湾地区作为世界工厂时期建造的工厂,有支援过美国参加越战的兵工厂,还有被俘志愿军的关押地。大片违章建筑群里住着外来打工的少数民族,突然有一天,陈界仁发现,从小熟悉的地方原来就书写着活生生的世界史,所有问题的根源和解决方案都在这里。
他开始使用摄影与影像的方式再现这些历史的边缘地带,于是就有了1996年摄人心魄的《魂魄暴乱1900─1999》,2002年三频道录像作品《凌迟考:一张历史照片的回音》,探讨历史摄影当中被忽略的问题;2003年单频道录像作品《加工厂》、2005年《八德》、2006年《路径图》关注劳工问题,2008年《军法局》涉及当代监狱议题。而2009年《帝国边界I》、2010年《帝国边界II─西方公司》则反思了美国对台湾社会长期控制的历史。影片当中所强调的“人民书写”、“人民记忆”,尤为需要依靠艺术的形式来作答。
“陈界仁:中空之地”在北京长征空间将展出至2018年2月4日。(本文图片由长征空间提供)
如需获得授权请联系第一财经版权部:banquan@yica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