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原标题:《中国全面超越美国之辩(之二)》
我在《中国全面超越美国之辩(之一)》 中认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在十年内应能超过美国,但是质量指标——公司效益、品牌价值、劳动生产率——和美国差距很大,同时中国为实现增长付出的代价很大,比如环境代价和资本投入的代价,这种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速持续下行,民间投资意愿低迷,低效产能难以出清,实体经济的创新转型困难重重,甚至出现靠“资产性繁荣”饮鸩止渴的现象,都说明,成就虽然巨大,包袱同样不轻。
在和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钱军教授的辩论中,我提出,支撑经济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法治,这方面中国还有相当的不足,在国际的排名也不高,必须加快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
营商环境:美国第7,中国第84
我举了四个方面的例证。
一是世界银行从2003年起每年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它对189个经济体以及所选城市的营商法规及其执行情况进行评估,主要针对内资中小企业,目前包括11项指标,即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证、获得电力、登记财产、获得信贷、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执行合同、办理破产。
去年10月公布的《2016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排名前十的经济体分别为新加坡、新西兰、丹麦、韩国、香港特区、英国、美国、瑞典、挪威、芬兰。美国第7,中国内地排名第84位。
以上海和纽约为例,来做一些具体的比较。
开办企业:上海需要11个程序,30天,成本为人均国民收入的0.6%;纽约需要6个程序,4天,成本为人均国民收入的1.3%。
办理施工许可证:上海需要22个程序,274天,成本为人均收入的7.2%;纽约需要15个程序,89天,成本为人均收入的0.3%。
纳税:上海的频次为9次,时间为261小时,应税总额占毛利的67.2%;纽约的频次为11次,175小时,应税总额占毛利的45.9%。(注:时间是指每年编制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社保缴费计报表、将其归档以及缴纳税费所需时间)
执行合同:上海为406天,成本为标的额的15.1%,司法程序质量指数为14.5;纽约为370天,成本为标的额的22.9%,司法程序质量指数为15。(注:时间是指从原告提起诉讼到实际付款期间的时间,成本是指法院费用和辩护律师费占债务总值的百分比,司法程序治理指数衡量法院结构和诉讼程序、案件管理、法院自动化和替代性纠纷解决这四个方面的实践,满分为18分。)
办理破产:上海的回收率为36.2%,破产框架力度指数为11.5;纽约的回收率为81.5%,破产框架力度指数为15。(注:回收率计算的是债权人、税务部门和雇员等申请人从破产企业收回的款项占其投入的比重,破产框架力度指数包括启动程序指数、管理债务人资产指数、重整程序指数和债权人参与指数,满分为16。)
上海是中国最为国际化、经济法治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但和纽约还存在一定差距。至于整个中国和美国的差距,比上海和纽约的差距要大很多。
经济自由、清廉与法治排名
第二方面的例证是经济自由度。全球主要的评价排名有两个。一是美国传统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1995年开始编制,目前的10项评估因素是:营商自由、贸易自由、财政自由、政府开支、货币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产权保障、廉洁程度、劳工自由。2016年度全球经济自由度排名,在186个经济体中,香港特区连续第22年名列榜首,之后是新加坡、新西兰、瑞士和澳大利亚。美国排第11,中国台湾排第14,中国内地排第144。
另一项经济自由度排名由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所做,它的5个主要评估范畴是政府规模(支出、转移支付和补贴、国企和投资、最高边际税率)、法治和产权(司法独立、法庭公正、产权保护、军队不干预法律和政治、依法执行合同、警察的可信赖等等)、稳健货币、国际贸易自由、监管(信贷市场、劳动力市场、商业)。在2016年对178个经济体的排名中,香港特区第一,美国第16,中国台湾并列第23,中国内地第113。
第三个方面的例证是总部在柏林的“透明国际”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CPI,0到100分,得分越高越清廉)。2016年1月发布的2015年全球168个国家和地区排名,平均分为43,2/3的国家和地区得分低于50。丹麦得分全球最高(91分),新加坡得分亚洲第一(85分)。美国排名第16(76分),香港特区第18(75分),中国台湾第30(62分),中国内地第83(37分)。中国内地此次得分比上年多1分,排位比上年向前提升了17名。
第四个方面的例证是“世界正义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发布的法治指数,从0到1,1代表最遵守法治。该工程最初是美国律师协会2006年发起的一项计划,2009年转变为非营利组织,2011年开始评估中国法治状况。在2015年发布的报告中,全球102个国家和地区的法治指数平均值为0.568,排名前三位的国家为丹麦(0.87)、挪威(0.87)和瑞典(0.85),香港特区排第17,美国排第19,中国内地(0.48)排第71。(注:2016年数据将于10月20日发布)
“世界正义工程”的数据来自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三个城市中1000名居民和法律工作者的回答,中国的数据来自北京、上海和广州。报告对“法治”的定义基于四条原则:可根据法律对政府及其官员和部门、私人和私营机构问责;法律清晰、公开、稳定且公平,平等应用,保护基本权利,包括人身和财产安全;法律的制定、管理和执行过程可了解、公平且高效;正义由有能力、有操守、独立的代表和中立者及时实现,这些代表和中立者人数充分,有足够资源,且反映了他们所服务的群体人员构成。这四项原则通过八个方面来进行衡量: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无腐败、政府公开、基本权利、秩序与安全、监管执行、民事司法、刑事司法。
根据该报告,中国内地在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政府公开性和基本权利方面的得分处于低段,排名分别为87、87和99,其余五个指标处于中间段。
由以上例证可以看出,在体现经济法治化程度的各项国际评价中,中国的排名都不高,总体处于中偏下的水平。这种地位近似于中国人均GDP的国际排名,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世界人均GDP排名,中国排世界第76位。
法治对经济增长的意义何在?
按上述排名,中国的营商环境、经济自由度、清廉和法治化程度在国际上都表现平平,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增长速度还能一直领先全球?是不是法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那么大?中国是一个“普遍原则之外的例外”?
按一般共识,“一个国家如果具有稳定的政府、可预知的法律变动方式、有保障的产权以及强有力的司法体系,就会比缺乏这些制度的国家取得更大的投资和增长。”(世界银行,1997)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教授裴文睿(Randy Peerenboom)在这方面有一篇著名论文《中国的法治与经济发展》。他的问题是:中国如何在明显缺乏法治和似乎也没有可执行的产权制度的情况下,却吸引了如此多的外国投资和实现了如此高的增长率?论文的假设是:
1.也许中国在法治和可执行的产权方面存在的问题比一般认为的要少;
2.也许因为存在能为投资者提供所需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的其他可替代机制或选择,因而法治就不是那样重要了。尽管存在法治风险,但中国巨大的市场本身就使投资决策具有合理性。或许,极其高比例的海外华人投资抵消了法治和可执行的产权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3.尽管增长率不低,但缺乏法治实际上影响了可能达到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也许可能更高。
围绕第一个假设,裴文睿援引了一些实证数据,证明中国的法治并不是那么糟糕。西方媒体经常报道说,中国法庭的判决和仲裁裁决根本无法得到执行,但一项调查显示,在所调查的案例中,有40%的要求法院强制执行的仲裁裁决的申请人获得了至少其裁决值的一半的赔偿(裴文睿, 2001a)。这比媒体流行的极为悲观的预测要好很多。
围绕第二个假设,裴文睿提到了三种“法治替代物”,分别是庇护主义、社团主义和“中国式资本主义”。所谓庇护主义,是指依靠个人和社会网络关系,比如依靠现在当官的老同学,比如地方企业依靠地方政府(“主仆式关系”);所谓社团主义,既不是“弱势政府+强势自利集团”的自由主义,也不是“国家集权+弱势自利集团+几乎不存在的草根阶层”的国家主义,而是将强势国家和享有一定自主性的利益集团结合在一起;所谓“中国式资本主义”,其特征是偏好家族企业,倾向于以非正式机制而不是法庭来解决纠纷,遵从儒家价值观,注重人际关系。一些学者认为,法治以中央颁布的普遍适用的法律为特征,但自上而下、中央集权的法治方式并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各地区存有重大差异,相反,社团主义安排会促进社会关系网的发展,把特定环境下所有经济主体联合起来,开展局部地区的试验,传递出不为中央政府所知的关键信息,从而形成更符合具体情况和可能更好的规则。
围绕第三个假设,裴文睿援引了很多学者的研究,说明在以市场不完美和法律体系存在严重缺陷为特征的转型时期,庇护主义、社团主义和不明确的产权是非常有用的,但并不是理想的。随着市场和法律改革的进行,它们将变得不那么有用。如果企业寻求与政府的密切关系,依靠关系获取批文;如果地方政府越过税务部门擅自给企业减免税收,或通过预算外“小金库”的各类收费降低企业的盈利率;如果地方政府通过设置贸易壁垒保护本地企业,让外部诉讼方在与有势力的当地企业打官司时很难取胜,即使赢了当地法院也不执行;如果行政部门利用许可权制造行政性垄断,或从申请人那里盘剥租金;如果政府官员与他人合谋为资产价值定价,以此换取回扣……所有这些,都会损害那些经济上更有效率但缺乏必要关系的企业,同时也降低法院、法律职业和其他实现法治所必须的职业阶层的地位。
这篇论文最后的结论是:
第一,法治并不是导致持续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但如果中国要保持长期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一种符合基本法治要求的法律体系是绝对有必要的;
第二,中国几乎不可能例外于法治,这是长期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要素的一般性原则。关系、庇护主义、社团主义和纠纷解决、融资以及合同保障的非正式机制,至多不过是一些不完备的替代机制,当法治建立起来后,这种作用必然会发生变化;
第三,法治是需求的函数。经济改革和发展加强了对法治的需求,而法律改革和法治有助于经济发展;
第四,法治对不同的集团的影响是有区别的。如果实施法治,有些集团、企业和个人——特别是那些依靠政府关系的――将会处境变坏。但是,就制度、规则、惯例和更多的方面而言,法治的建立具有溢出效应,会使国内的企业、私人企业家和公民个人等社会大多数受益;
第五,法治并不总是有效的解决方案。有些情况下,依靠市场或政治渠道,而不是依靠正式的法律,可能会是约束当事方或解决纠纷的更有效的方法。而且,只有在与文化价值、非正式惯例和制度及经济发展的一般水平相适应的情况下,法律才是有效的。在没有其他制度、经济政策和文化习俗相应变革的情况下,单枪匹马地进行法律体制改革,会使改革的效力受到限制。
中国的“办法”与美国的“法办”
和美国通过两百多年努力所形成的,以宪法为基石、以司法审查为核心机制、以基本权利保障为实质内容的司法中心主义的法治模式不同,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法治建设,比较快地建立了完整的法律体系,同时也有着明显的行政主导、行政立法色彩。其利,是效率优先,有利于通过国家、社会方方面面集中资源,高效实施,完成中心任务;其弊,则是司法权屈从于行政权,形成对行政权力的过度依赖,行政主导、部门立法也助长了权力的任性与滥用。
如果通俗些说,中国更多讲“办法”,法是一种“办事”的工具,美国更多讲“法办”,法律重在“律”,也就是约束权力。
在中国,为达成一个执政目标,程序可以改变、变通,灵活施政,因应变化,所谓“办法总比困难多”。比如为了提高效率,行政部门创造出“领导批示督办”、“一个窗口一站式服务”、“现场办公”、“联席会议”等办法。中国有些大政方针,急着出台,酝酿时间很短,也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比如分税制和房地产、资本市场的调控。
如果方向正确,合力大、阻力小的中国式道路会走得更快。中国经济之所以持续高增长,是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焦于此想办法,无论是立新法,修旧法,制定行政性条例,实施优惠刺激政策,都紧紧围绕促增长展开。只要有用、有效,不管黑猫白猫,拿来就用。
但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也在于此。
一方面,凡是容易出政绩、有近功速效、有比较多资源可以调度、对个人有更多利益关联(升迁、寻租等)的领域,成效就明显,比如城市建设、形象工程、招商引资、房地产。凡是不太容易见效、更需要久久为功的领域,发展就慢,就失衡,比如科教文卫。凡是容易出成绩的地方,就争权夺利,凡是不容易出成绩的地方,就诿责推脱。更有甚者,为了达标不择手段,给未来埋下定时炸弹。
在另一方面,由于权力集中和缺乏监督,事实上还是人治大于法治,公权私用,因权施威。部门立法,选择性执法,执法不透明不文明,甚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凡此种种,历久不衰。“图章经济”下的“寻租”可能带来增长,对污染视而不见可能带来增长,但也容易失去人心,很多富裕起来的人挣到钱后还要忙着移民。
行政权力主导还有一个弊端,就是在全社会形成“权大于法”的示范和潜意识,托关系、找门子、求干预,普通人有冤屈首先想的也是找领导,不找领导解决不了。2008年五四青年节,温家宝在中国政法大学和学生座谈时说,我今天一出门就有个感触,我的汽车刚拐弯,就被两个上访的群众拦住了,我统计了一下,在我住的周边经常来上访的47%都和司法有关,而且很多都是为自己亲属或者本人判决是否公正上访的,好多是多年上访。“什么时候我们的法律,从立法的完备到执法的公正,到诉讼法的健全,使人们不必跑这么远,能够就地解决这些问题,那时我们的社会就更进步了。因为所谓上访,它所体现的不是法律的程序,还是寄托在人,寄托在领导人的批示,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还带有人治的封建色彩。”
“法办”可能是更好的“办法”
最后谈一下美国,法律的核心是“律”,是对权力的制约。20世纪前30年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霍尔姆斯说:“罪犯逃脱法网与政府的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所以美国法治的突出特点就是制衡,让权力不可任性。也因为如此,美国的经济和社会总体上十分稳定,政府很少进行微观干预,企业因受政策影响而大起大落的情况比较少,主要是靠内生能力在市场上打天下。
但世上没有完美的制度。当年托克维尔在赞美美国民主的同时就曾指出,美国政坛上常常出现能力平庸、无所作为的人,而真正有能力的人却游离于政坛之外。人们习惯了频频立法,这种对法律的便利的修改似乎成为了“多数”的一种集体爱好,这要求国家将立法工作提到十分重要的位置,因此无暇顾及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领导人有时为了讨好人民或为了转移自己工作失职而可能受到的谴责而将工作重点转向立法,参与到永无休止的立法争论中。立法的不断进行,一方面会使人们因对多变的法律缺乏了解而无所适从,另一方面也会造成一些法律间的相互抵触和冲突。
不少人说,只要有好的法律体系,领导人素质不是那么重要。太平盛世可能如此,沧海横流的危机与挑战面前,领导人的作用还是异乎寻常的。今天,当我们看到美国的公共产品供给(如基础建设和医疗保障)不断陷入争议、难以推动,看到整个社会的法律事务支出越来越高,看到像特朗普这样的总统候选人所掀起的一轮又一轮风波,不能不感叹托克维尔的先见之明。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曾言:“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就是“诺思悖论”。一个经济体的长期健康发展,本质上还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此而言,法治仍是关键。法治既是制约政府权力的力量,也是政府进行有效监管的依据,更是保障企业权利的基石。
美国可能要借鉴中国的一些办法,而中国要超越美国,未来必须把“依法办事”,把“法办”作为真正的行之久远的好办法。法治程度是支持创新与发展的最重要指标。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同卢梭所说的,“规章只不过是穹窿顶上的拱梁,唯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窿顶上不可动摇的拱心石。”但不从眼下的点滴做起,人治就仍然是中国的宿命,并给我们的未来埋下巨大的不确定性。
TikTok称将对美国限期剥离法案发起诉讼

中国代表驳斥美国就外空安全对中国的无端指责
国际社会应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理念,在平等互利、开放包容的基础上开展外空国际合作,确保各国和平探索利用外空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推动在外空领域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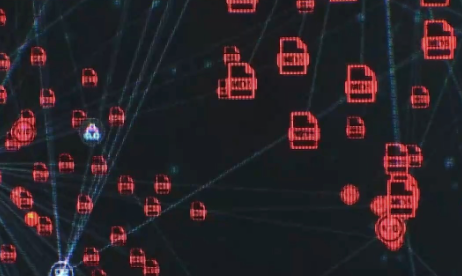
揭秘!美炒作“中国网络攻击威胁”实为栽赃陷害
近年来,中国公安机关侦破西北工业大学、武汉地震监测中心等多个机构被美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网络攻击案件中表明,美国才是真正的"黑客帝国″、″窃密帝国″。

最大出口国美国暂停液化天然气出口项目审批,今年全球会缺气吗
业内人士认为,此一政策是在美国大选之年仓促作出的政治决定,对中国的影响总体可控

美国胃迎应中国味,耶伦访华强调“不脱钩”
“鸽派”耶伦,传递何种讯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