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作为美国最重要的政治学家,以及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三任美国总统的资深顾问,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是一个标准的美式精英。他身材高大,面色红润,精力旺盛。每到公开场合,他都会穿上质地精良的黑西装,一派名教授风度。在北京的公开演讲中,现场两位翻译同时上阵,都跟不上他的节奏。这位77岁的美国政治学会前主席,每说起自己的研究,都是滔滔不绝,条理分明。

一如其笔尖洋溢的亲和力与开放性,帕特南是一个充满活力、善于社交的人。握手送别了几拨采访者,他依然精神饱满,还很仔细地为记者在书上签名。年近八旬的他,玩起来也是毫不含糊。在北京,他背着沉重的相机,一口气逛了颐和园、什刹海、潘家园和798艺术区。在胡同里穿行时,他尤其喜欢观察普通市民的生活,还拒绝了朋友请他坐三轮车的建议。在798,他也有所斩获,买下了一幅描绘江南水乡、看上去水汽氤氲的油画。
帕特南出生于俄亥俄州的小镇克林顿港,家境平平。他的少年时代,正赶上上世纪60年代的经济大繁荣。美国民权运动高涨,许多人上街游行、演说,抵制种族隔离和性别歧视,帕特南也是其中一分子。
60年过去,呼唤社会平等的热情依然如野火般在他身上蔓延,只是以另一种方式被表达。“当年,有几十万人和我一样上街游行。我并不觉得当时的自己是激进分子,如今坐在书斋里的我才是。”
1950年代与2010年代的美国
在相当长时间里,这位出生于平民家庭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讲席教授,是“美国梦”的坚定信奉者。他曾认为,“能有今天的成功是来自我的个人奋斗”。但在着手一项从自己家乡出发的调研之后,这个看法被扭转了。
他把这一研究写成了新作《我们的孩子》,并于去年出了简体中文版。书里收录了美国各地100多位年轻人的成长史,时间跨度从1950年代直至21世纪。帕特南和他的团队追踪了这些人的命运走向,细致记录了这些来自不同阶层的孩子,是如何铺展人生的。
阶层分化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相关研究也有很多。这本书的特点在于,提供了许多普通人的故事,并从宏观到微观各个层次,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通过这些,一个宏大的社会问题变得易于触摸。它让人们清楚地看到,父辈的地位差距是如何一点一滴地渗透到孩子们的生活中,最终将穷孩子和富孩子牢牢分隔在两个世界。
分隔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逐步加剧的。那些1950年代生活在克林顿港的工人阶层的孩子们,包括帕特南自己,还有很大机会通过个人奋斗实现“美国梦”。可到了21世纪,成功对穷孩子来说已经遥不可及。
在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帕特南的同学,那位出身工人家庭的唐,家境贫寒。父辈虽然没什么文化,但也时刻敦促儿子上大学。为唐提供人生道路指引的,还有社区的教会。一位牧师时常指点唐,还推荐他上了大学。后来,唐也成了一名职业牧师。
他的另一位同学弗兰克,出生在大富之家,从小就被严格教育“不可炫富,要与同学们打成一片”。弗兰克没有因为家庭享受什么特权,且资质平平,在父母的资助下,上了本州的一所小学院。毕业后,他参加了海军,退役后做了25年编辑。家族财富让他不至于伤痕累累,但也没有让他一飞冲天。
对一个美国平民家庭的白人男孩来说,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或许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帕特南高中班级里,将近3/4的同学受教育程度要高于父母。而且,出身平平的孩子反而比家境优渥、父母受过高等教育的孩子取得了更高的社会经济成就。
可50年后,一切都不同了:因为许多工人父母的境况恶化,穷孩子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条件都开始快速衰退。不少孩子早早辍学,打架吸毒、性格暴戾,前途一片黯淡。但很明显,错并不在孩子们自己。在他们的故事里,总是充斥着贫穷、匮乏的教育资源、家庭暴力、冷漠的社区、坐牢或是频繁结婚的父母。而另一边,被高高的围墙围起来的中产和富人社区里,诞生了千千万万个“虎妈”,正挤破头要把孩子往好学校里送。
美国孩子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孤立的,在剧烈社会变迁中生活的人们多少都能感同身受。书中两个世代、各个阶层孩子的成长轨迹,应该也会让中国读者产生共鸣,伴着庆幸或遗憾的情绪。
从“我们的孩子”到“我的孩子”
与许多欧洲同行不同,帕特南并不以构筑一个深刻或完整的理论见长,而是以贴近现实的关切、详实的调查和精到的论述打动人心。或许也正因如此,这位政治学家的著作总是能够深入普通人,还直接激发了美国草根运动的勃兴。
“我这些年的学术著作,其实都是在呼吁美国人能够重拾一种集体感。”在北京的一次讲座中,他如此总结。
帕特南不止一次回忆起这样的细节。小时候,妈妈常把“我们的孩子”挂在嘴边。“我们的孩子”并不单指帕特南和他的姐妹,而是指镇上所有的孩子。但是后来,他再也听不到“我们的孩子”了,人人都只说“我的孩子”,“整个美国都从‘我们的社会’变成一个只有‘我’的社会”。
在《我们的孩子》末尾,他呼吁美国人重归社群主义传统,担负起照顾别人家孩子的责任。他还提到,即便是站在自利的角度,这也是必须承认的义务,“因为我们和穷孩子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帕特南的成名作《独自打保龄》今年8月又出了一个中文版,这本书更是直接讨论美国社会的公共参与。保龄球是一项常见的运动,打保龄球的美国人甚至比参加大选投票的人还多。人们对保龄球的热爱从未消散,但打球的方式变了。过去大家总是成群结队去打球,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喝很多啤酒,吃很多零食,这对产业发展有好处。更重要的是,人不那么容易孤独,社会参与感也强了。可进入197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独自打保龄球。
独自打保龄,成了整个社会的缩影。通过广泛的调查和数据分析,帕特南发现,美国人宁可独自运动、上网,也不愿意走到人群中,参与集体活动的热情逐渐冷却。这不仅发生在休闲活动中,也发生在教会、工会、社区互助组织甚至工作单位里。社会资本的流失,不只让社区的温暖和可爱褪色了,也给经济、民主甚至健康带去了不好的影响。
就如很多人对中国人“搞关系”那一套多有诟病,被理解为人脉资源的“社会资本”也可能带来不公平,这引起学者们的疑虑。但帕特南的数据统计表明,对重建“社会资本”的疑虑完全没必要,因为“在几乎整个20世纪里,社会资本和经济平等都是共进退的”。

专访帕特南:我们可以同时赢得经济繁荣与社会平等
第一财经:很多时候,你把1950年代视为一把标尺,来比照之后的社会情况。对半个世纪前的岁月,你是否总怀着好感?
帕特南:不是。1950年代也有很多很不好的事情。那时有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这些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公平。我们也没有苹果手机,要知道,我可是很喜欢苹果手机的。当然,当年我们也有很多好东西,都是现在已经遗失的,也是大部分美国人早已忘却的。其中最重要的是,那时我们拥有一个阶层平等、相互融合的团结社会。我们不像现在那么以自我为中心。我想探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重新回到当时的状态,让人们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党派之间可以妥协和谈判。
第一财经:今年正好是法国“五月风暴”50周年。1968年的你处于怎样的状态?
帕特南:1968年,我已经毕业了,成了一名大学助教。我已经结婚了,我的妻子现在依然是我的妻子(笑)。我也已经有了两个孩子。
对于“五月风暴”,我关注过,但我当时已经正式进入学术圈,不再是一个学生了。当然,此前,我积极参与了美国的民权运动。
除了这两本书以外,我还在写一本新书,是关于20世纪历史的。在那本书里,其中有一章就是关于1960年代的事情。现在你还没有拿到那本书,如果让我来说服你同意我的观点,是不公平的。但我还是试着来概括几个观点:在很多西方国家,1960年代到1990年代之间,社会总体来说变得更加公平,政治上更加合作,文化上也更加融合。1960年代,是20世纪充满奇迹的10年,也是变化最大的时期。从那以后,美国经历了一个转折,美国人变得越来越自恋。美国成了一个“我”的社会。
第一财经:这种巨大的转变,是否也和1960年代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有关系?
帕特南:这个时间点是很多国家都经历的,但是对每一个国家,它的意义却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历史,与美国也完全不同。台风会带来暴雨和潮汛,但我想要描述的是河流底下的深层基础。我想要解析的是美国变化背后的深层逻辑。
第一财经:民权运动时期的美国社会波澜起伏,很不安定,但就如你所说,当时广泛的社会参与让社会凝聚力加强了。在社会稳定和凝聚力之间,你认为应该如何权衡?
帕特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我需要用一本书来写出这些内容。我正在写的一本新书中,关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事就是其中的章节,会涉及这些内容。
第一财经:在《我们的孩子》结尾,你号召富人和中产阶级多多关心穷人家的孩子。对你来说,阶层鸿沟真的是缘于人们的冷漠和为富不仁吗?这是文化所导致的后果,还是制度因素占主导?
帕特南:我认为它们共同起作用。先谈制度,制度对学校教育和社会资源的分配都会起作用。在学校里,穷孩子和富孩子不得不分开上学。居住区域的分隔也是一个原因。现在,国家为富人减税,也拉大了贫富差距。
但当我们再追问下去,制度为什么会变化?我觉得还是文化上的原因。并不是说文化上的问题直接造成了这样悬殊的不平等,而是文化通过制度起了作用。我来举一个例子。美国人选择远离贫民区,要往富人区居住,这是制度吗? 不是,这是一个文化问题。1960年代,我父母总说“我们的孩子”,现在没有人这么说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变了,这是所有变化的背景。
第一财经:你觉得经济繁荣和社会分化有没有相关性?经济繁荣是否必然会付出社会不平等的代价?
帕特南:不是这样的。在1900年代、1950年代和1960年代,我们的社会都处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但同时也拥有公平。现在,我们的经济增长放慢,不平等却很严重。所以,这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相关性,两者的正向效果是可以同时出现的。
第一财经:你并不是“社会资本”的提出者,却让这个学术概念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在我看来,能够唤起公众关注,是你学术写作的突出特点。你是如何让自己的学术写作深入民众的?
帕特南:很对,我当然不是这个概念的提出者。许多学者都在研究“社会资本”,但我和他们对这个概念的定义是不同的。布尔迪厄(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关心的是富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是一个内向的社会网络如何有利于网络内的人。我关注的是更大范围内的社会资本,是一个外向的社会网络如何作用于社会整体。
在我写《独自打保龄》时,别人都不知道“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但是我写了以后,很多人都知道了,甚至克林顿都邀请我去演讲。我要说的是,我的成名并不是因为我突然变聪明了,或者特别有创造力,我只是写出了很多美国人都有的感受。在我写出这本书之前,很多人都以为这种孤独只是自己才有的感觉,但这本书让大家知道,这是一种弥漫于整个美国社会的气氛。只是,我用一种学术的方式把大家的苦恼写出来了。如果你们做记者的也能够发现大家面临的问题,然后好好写出来,相信也一样可以成名。
罗伯特•帕特南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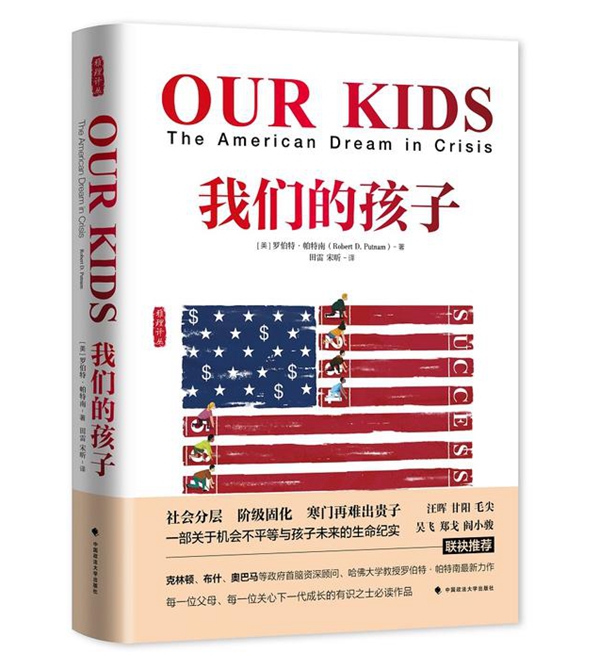
《我们的孩子》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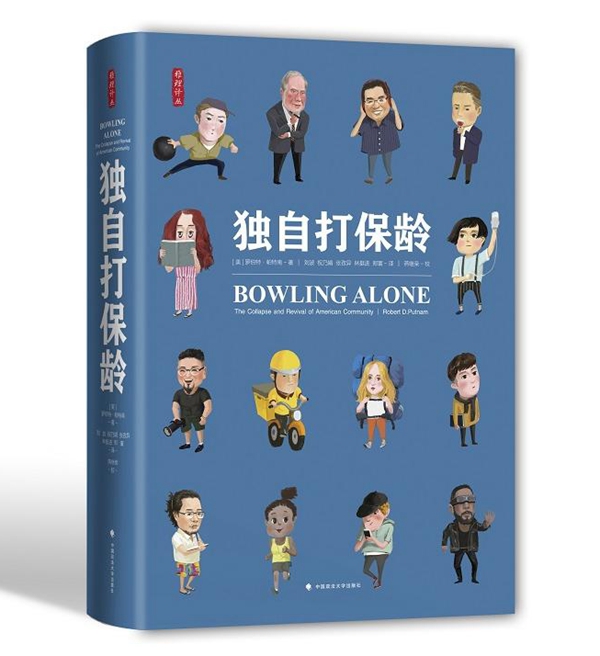
《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9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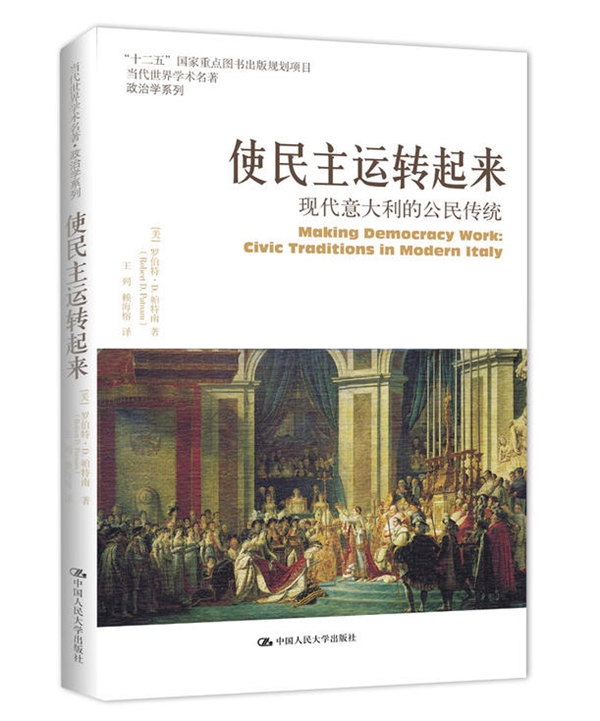
《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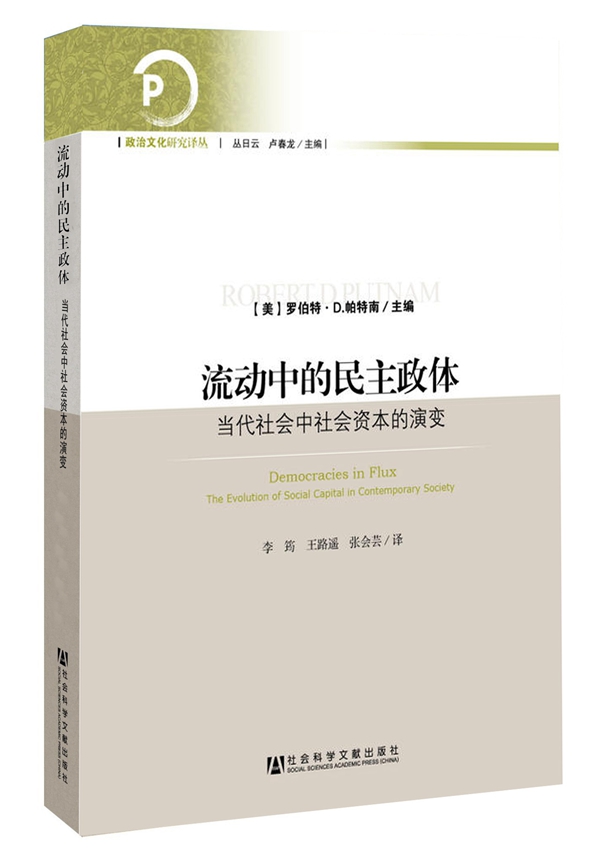
《流动中的民主政体:当代社会中社会资本的演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6月版
如需获得授权请联系第一财经版权部:banquan@yicai.com
文章作者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两国元首同意双方团队继续落实好日内瓦共识,尽快举行新一轮会谈。

中国车企告别“多生孩子好打架”时代
头部汽车集团的纷纷整合,是中国汽车行业竞争白热化、淘汰赛下的车企战略选择。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取消哈佛大学免税资格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取消哈佛大学的免税资格,称“这是他们应得的”。

孩子需要怎样的戏剧?上海这个儿童剧厂牌探索了7年
2018年,陈丹丹和凌伶创办小顽家儿童戏剧,希望通过剧目的引进和创制,为中国市场带来更先进的儿童戏剧理念。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泽连斯基3月19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前乌美双方团队顺利举行会晤。在19日同特朗普的通话中,希望获取有关美俄总统通话的详细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