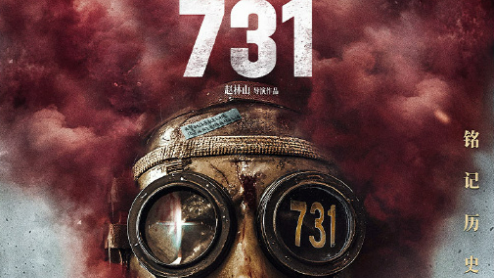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今年是伯格曼诞辰100周年,前几个月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安排了他的专题,放了十几部片子。十年前,2008年,是伯格曼诞辰90周年兼逝世一周年,电影节也做了专题,那回因为是第一次有机会在大银幕上看贡纳•费舍尔和斯文•尼克维斯特风格迥异但都张力十足的画面,所以除了《假面》,东奔西走看完了每一部,加上此前为了写介绍文章在电脑上拉片看的十几部,算是集中把伯格曼粗粗捋了一遍。十年过去,再次在大银幕上看那些几十年前的旧作依然震撼,但当年的崇拜之情却少了。

塔可夫斯基在他的太空科幻片《索拉里斯》里,引用了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名作《古老的恐惧》中的一句话:“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宇宙感。”
的确,这十年,我逐渐意识到某种“泛宇宙感”在构建一部真正伟大的艺术作品时的重要性——你得需要一种超出对现实的描摹,也超出自我探究和社会批判的更宏大也更根源的目光,就如尼采在锡尔斯玛利亚、在阿尔卑斯群山间所感悟到的:“高出海平面6000英尺但更高地在一切人类事物之上!”
伯格曼身上有这个东西,但不够。他过多地纠缠于自我反思、家庭阴影和宗教批判,因此过于刻薄甚至刻毒了。本质上他是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拒绝简单地投向无神论,却无法拥有任何虔诚的信仰,并意识到即便上帝真的来到面前,也完全不能信靠。在他看来,有神论迷信到无脑或十足虚伪,无神论虚无到歇斯底里然后自毁,总之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桩事情是对的。他不相信上帝,更不相信亲情、爱、自我、群体、社会。人类在历史上曾经为自己开出的种种药方,他一概质疑。
他对塔可夫斯基佩服得五体投地,并不仅仅是我们通常以为的,因为后者比他更自由地穿梭于现实与梦幻之间。这话是伯格曼自己说的,但背后的潜台词,其实是塔可夫斯基拥有一种宏大而深沉的俄罗斯式泛神论信仰,在这种信仰的围护下,所谓的现实和梦幻本来就是相通、相互转化的。塔可夫斯基的游刃有余、浑然天成与伯格曼对梦境不时用力过度的刻意表现,的确如他自己意识到的,在境界上有距离。塔可夫斯基自己也对此看得很清楚,在评价费里尼的《八部半》和伯格曼的《野草莓》时,他指出其“失败”是因为影片依然是“基于情节的叙述”,换句话说,梦幻是被刻意插入以便搅乱情节主线的;而他自己的《镜子》则从一开始就拒绝了情节的控制,完全成为一种对意识(记忆、想象、思考、感受、知觉等等浑然未分、纵横交叠的意识)状态的现象学描述。
根本来说,这其中的距离,源于基督教发展到20世纪已活力尽失,而与之相颉颃的宗教批判则日益虚无化。因此在意识清明的时候伯格曼总是充满绝望,咬牙切齿地诅咒着什么,只是在某些边边角角的地方,某些放纵自我迷醉的时刻,内在的温情的余烬,才透出一些希望的火苗。
在电影领域,伯格曼是现代病最全面的、毫不留情的揭示者和呈现者,这是他的伟大也是他的局限所在。相比之下塔可夫斯基几乎前现代的泛神论底色(他在这底色之上来信手撷取现代性的可恶碎片),使他总是自成一体地拥有一种随时在线的家园感(哪怕主题是“乡愁”),因此无法像伯格曼那样将现代虚无主义的种种征象如此形象如此淋漓尽致地一一摆置于我们眼前。我想,很大程度上(撇开政治体制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塔可夫斯基一辈子只拍了七部半,而伯格曼的产量是他的近七倍!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电影的元素》
【美】罗伯特•伯德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版

《伯格曼的电影》
【美】杰西•卡林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