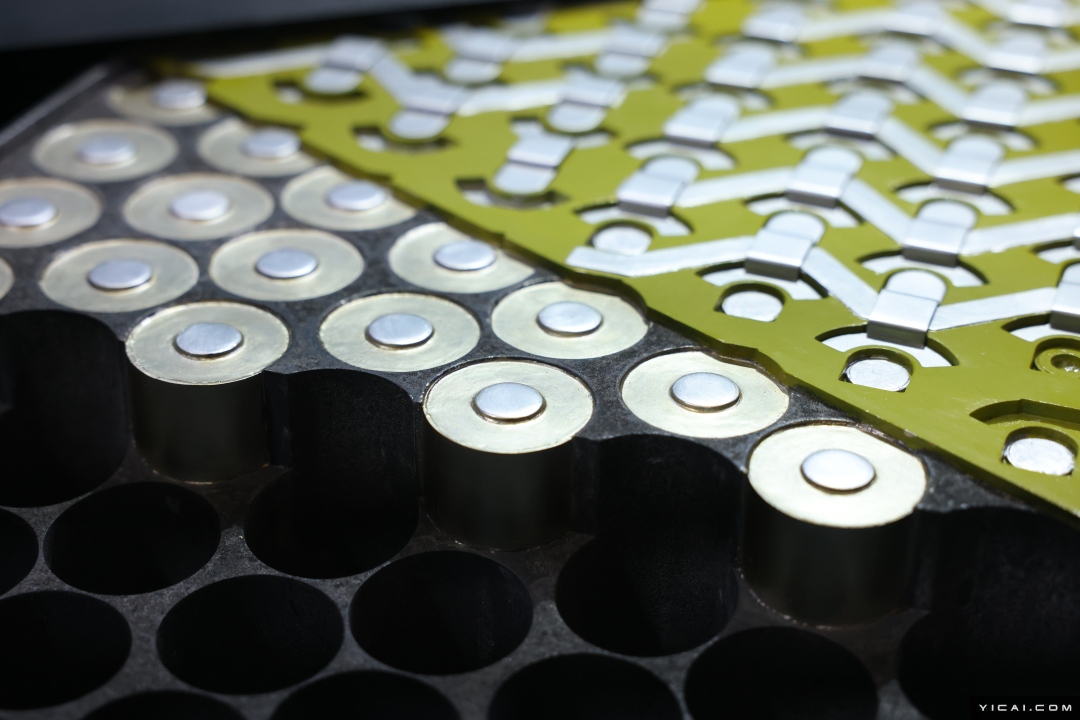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前些年,当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陆续回国时,在国人中又激起了对近代国耻的记忆,那不仅是英法联军在皇家园林中的劫掠,还被视为一段尚未抚平的创伤的象征。对中国人而言,这是特殊而难忘的经历,不过在西方历史上,这样的事却历来多有,从特洛伊战争以降的三千年里,可谓史不绝书,被运到罗马帝国各地城市广场上的方尖碑竟有十三座之多。对近代帝国主义列强来说,用劫掠来的珍宝文物自我装点,也事属平常,但将这一暴行发挥到登峰造极地步的,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纳粹德国。
这正是《劫掠欧罗巴:西方艺术珍品在二战中的命运》一书着重叙述的,书名中的“劫掠欧罗巴”(The Rape of Europa)一语隐含着古希腊神话中的典故:大神宙斯爱慕腓尼基公主欧罗巴,变身为公牛将她诱拐到大海彼岸,那块大陆自此因她之名而被称作“欧洲”(Europe)。在此,作者似乎暗示了这种做法在欧洲的长久历史,又语带双关地指明纳粹德国对艺术品的摧残给整个欧洲文明带来的创伤。在二战以前的欧洲史上,这方面遥遥领先的是拿破仑(他在攻下罗马后洗劫的文物珍宝曾装满了500辆马车),但纳粹在整个欧洲的破坏强度不仅空前,也很可能是绝后的。
在此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纳粹德国当时劫掠艺术珍品的出发点和行事逻辑,与此前那种战利品式的抢夺方式并不完全相同。事实上,纳粹对文物的破坏首先始于本国。1939年,他们将一大批所谓“堕落艺术品”从德国清除出去,在瑞士进行拍卖。在纳粹的意识形态中,对艺术品的劫掠与清除,本质上和他们在集中营里屠杀犹太人一样,都是为了达到“净化”,即完全符合他们要求的秩序,而将剩余的部分都予以驱逐、破坏或粉碎。“文化”要剥离其精英主义意味,而代之以种族、民粹的含义,当时盛行一句挖苦的话:“当我听到文化这个词的时候我就要伸手拿枪。”正因此,他们并不全是因为某一艺术珍品值钱而劫掠它,还混杂着更具破坏性的动机,那更像是一场宗教战争,凡是异教一方的都要毫不留情地予以毁灭。
某种程度上,这是铁血宰相俾斯麦在1870年代发起的“文化斗争”(Kultur kampf)的延续,只是推向了不留余地的极端。作为一个曾在维也纳街头混饭吃的二流画家,希特勒坚称艺术中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是时代病症的征兆,他在1937年的“德意志艺术节”上咆哮:“从现在起,为了反抗压迫我们的艺术的最后因素,我们要领导一场不屈不挠的净化之战、一场不屈不挠的灭绝之战。”他这么说不是闹着玩的。事实上,1933年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仅九周,纳粹党下属的“德国文化战斗联盟”就宣称“革命首先是文化层面的”,要“根除、粉碎那些破坏我们命脉的东西”——特别是不符合其审美的现代派艺术品;与此同时,连党卫军都特设有一个艺术分支机构“遗产研究所”,赞助那些能证明日耳曼种族文化优越性的古怪研究。
因此,与其说纳粹德国是在劫掠欧洲的艺术珍品,倒不如说是他们在侵入邻国之后,将国内那一套“文化净化”的做法推广到了占领区。当然,他们对波兰等国的博物馆、图书馆和宫殿都任意搜刮,但他们在搜刮时所遵循的标准仍然是自己那一套:那些“庸俗文化”的犹太、波兰艺术品被封存后毫不可惜地加以处置,一些毕加索、达利的作品甚至被放在空地上烧毁;但丢勒的27幅画作则被视为“日耳曼遗产”,希特勒下令特别留意运回国内。正如纳粹秩序下的许多侧面一样,在艺术品的收缴与买卖中也有虚伪的一面:巴黎的占领军高层在蔑视法国“堕落艺术”的同时,却又在拼命搜刮,享受着巴黎的安逸生活。这催生了当时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因为在资金无法自由流动、货币随时贬值的战争时期,艺术品是最能保值的。
在当时的德国高层中,也不是没有“好人”。驻法德军军政府艺术珍品保护协会会长弗朗茨·沃尔夫-梅特涅伯爵是中世纪建筑专家,自认是艺术守卫者,他向巴黎军政府坚称:巴黎占领行动必须严格遵守1907年的《海牙公约》,而公约中的条款禁止以军事威胁掠夺艺术品,也不得侵犯私人财产。1944年,面对逼近的盟军,防守巴黎的德军指挥官冯·肖尔铁茨将军拒绝了上级再三重申的命令,因为他觉得巷战和地毯式轰炸将会使这座遍地珍贵建筑的城市变成一片废墟,他宁可投降也不做这样的罪人。更令人惊讶的是,甚至连希特勒有时都持有类似观点,他虽然认为佛罗伦萨是“阿尔诺防线”的关键,但同意它应该“被保护”,因为这座城市“太美丽了,不能毁掉”,还颁布了一项特殊命令,要求选出意大利的一些艺术品“送回不设防城市佛罗伦萨和罗马,它们在那里可免遭恐怖的轰炸,从而为了欧洲被妥善地保存下来”。
不可否认,当时的盟军也轰炸历史建筑,甚至不乏有人顺手抢点珍宝,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官兵并不清楚哪些文物更值得保护——1943年的意大利城市几乎遍地都是老房子;但盟国在1943年1月就联合发表一份声明,宣告所有“在敌占区的被迫财产转移”都是无效的,这使艺术品的劫掠成为非法之举。不仅如此,盟军内部特别成立了一个“战区艺术和历史古迹保护和抢救委员会”,一些军官兼有学者的学识和军官的职能,号称“维纳斯修理工”(the Venus fixers),奔走各地,竭力使不可复现的文物幸免于炮火。这是历史上首次出现这样的景象:一边要消灭敌人,一边要保护并修复敌方的文化遗产。
说实话,这些做法在当时很难得到军方的理解。盟军意大利战区统帅、英国的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虽然说这一战役的“背景让人不断想起意大利的辉煌过往”,但在1944年初的战役中,他仍不顾美军的反对,将不可复制的卡西诺山修道院夷为平地,因为在他看来,“当士兵为正义大业而奋战,且准备为此牺牲生命、断手断脚时,再怎么尊贵的砖块和灰浆,都不能看成比人命还重要”。而美军的克拉克将军则将之称为“悲惨的错误”,因为它不但摧毁了这一珍贵的遗产,而且并未达到军事效果:在它被炸毁后,德军仍固守废墟达三个月之久,残垣断壁反倒更适宜作为狙击手的藏身之所。但尊重当地文化遗产也有另一个现实的原因——减少当地人的敌意,正如艾柯所言:“可以确定,战后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基本上发展得不错(历史证明了这点)应和京都没有遭受毁灭有关。”
令人讽刺的是,当时的纳粹宣传中将英美盟军称作是“野蛮人”,说他们“正像鬣狗一样扑向德国的艺术品,并开始了一场有组织的掠夺行动”。不必讳言的现实是:战争中,双方的道德边界都是模糊的,但至少都不敢公然背负破坏文化遗产的罪名。平心而论,双方都曾有大量普通官兵损毁、亵渎或破坏文物的举动,这也是为何英军轰炸卡西诺山修道院后,德国报纸立刻大肆报道,将之视为“破坏文明、伤天害理的罪行”——尽管在盟军方面看来这不过是“不小心炸毁这么或那么一丁点古建筑”。从盟军的角度来看,德国艺术品保护局在撤退时“抢救艺术品”更像是“偷窃艺术品”的掩护机构,但这也是事实:德军在从佛罗伦萨撤离时,即便没有交通工具和燃料供部队使用,却仍腾出车辆运走该城1/4的艺术品;德国军官还请求博洛尼亚大主教保管运来的大批艺术品,一名德国文物修复员及党卫军指挥官还冷静地保住了600多件意大利艺术精品。
这么说并不是要为德军翻案,德军在二战时摧毁“劣等文明”的文化遗产时从不手软,如华沙几乎全城都被夷为平地;但在意大利,德军和盟军这交战双方却都默契地放过了罗马。耐人寻味之处正在于此:为何英美盟军与德军都认为战火损毁意大利古迹是一种无法承受的罪孽?为何都认为破坏其遗产是“野蛮”而“不文明”的举止?答案或许正在艾森豪威尔1943年底签发命令时所说的一段话中:“如今,我们正在一个国家内打仗,这个国家曾对我们的文化遗产有很大贡献,这个国家所创造的丰富古迹,曾协助催生我们所属的文明……我们必须尽可能尊敬这个古迹。”
概言之,“我们”保护这些古迹,是因为它们是“我们的古迹”,与“我们现有的文明”紧密相连,摧毁它因而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在那些与自身的文明较为疏远且似乎不那么值得尊重的国家作战时,美军的行动就未必那么谨慎了。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当地许多古建筑和博物馆遭美军大肆破坏或因疏于保护而损毁——二战时盟军在意大利派警卫看守王宫文物,使其免遭劫掠;但在六十年后的伊拉克战争中,博物馆却未能享受与石油部同等的保护优先级,以至于美国一名文物专家为抗议中央司令部命令而辞职,称之为“不可饶恕”的错误。在考古学家们抨击这是伊拉克文物所遭受的“500年里最严重的文化浩劫”时,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却轻描淡写,称这不过是“足球赛后的疯狂”,耸耸肩不以为然地说“这种事情不可避免”,然后开玩笑说,他倒是没想到伊拉克还有那么多古董花瓶。
为何如此?是美国变得更傲慢了吗?还是因为那些不是“我们的遗产”?无论如何,我们理应记住:艺术珍宝最大的劫难历来是在战争期间,而造成最大破坏的,既不是劫掠本身,甚至也未必是疏于保护,而是人为的区分——如果将一部分艺术品划为“堕落的”或“异族的”,那么毁掉似乎也就毫不可惜了。正如西蒙·沙玛在BBC的九集纪录片《文明》开篇就说到的:也许我们平日不知道何谓文明,但当我们失去它的时候会知道。从这一点来说,在战争中损毁的艺术珍品不仅是“西方的”或“伊拉克的”,它们全部都是“我们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将之毁弃,也只有树立这样的意识,才能让悲剧免于重演。

《劫掠欧罗巴:西方艺术珍品在二战中的命运》
[美]林恩·H.尼古拉斯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后浪 2018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