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随着全球新冠病毒的感染者已超200万人,各界将终结疫情与预防疫情反扑的希望寄托于疫苗的研发。但事实上,这远不止是一个如何在实验室“从无到有”的挑战。
一种成功面世的疫苗需要经历实验室研发、临床试验、监管审批、生产交付等复杂而漫长的环节,涉及全球协作、供应与部署。为加强跨国与跨部门的广泛合作,20国集团领导人在3月底特别峰会上承诺,在自愿基础上立即向世卫组织新冠肺炎团结应对基金、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提供资源。
CEPI和Gavi均是疫苗研发与交付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致力于将有效的疫苗部署到往往无力承担采购成本的中低收入国家。前者专注于研发针对传染性疾病的新型疫苗,其疫苗的研发速度目标是平均40周;后者则发挥其专长,基于有效性和量产能力来发掘应对传染病的最佳候选疫苗,并通过其资源加速疫苗的后续研发、生产环节。
在盖茨基金会于15日主办的线上研讨会上,第一财经记者采访到CEPI首席执行官哈切特博士(Richard Hatchett)以及Gavi首席执行官伯克利博士(Dr. Seth Berkley) 。他们一致同意,必须从全球角度统筹疫苗的生产力,以防疫苗生产资源的挤兑。
“我们现在正努力了解全球的情况,以便得知我们是否有充足的生产能力。在制造方面也出现了创新成果,比如有些疫苗可以模块化、可拆卸式生产(disposable units),我们也需要关注这些。” 伯克利对一财说,“因此,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以全球视野来思考我们的能力,如果我们依赖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可能最终会陷入两难的境地,比如为了救命的疫苗而停止其他疫苗的生产,这不是好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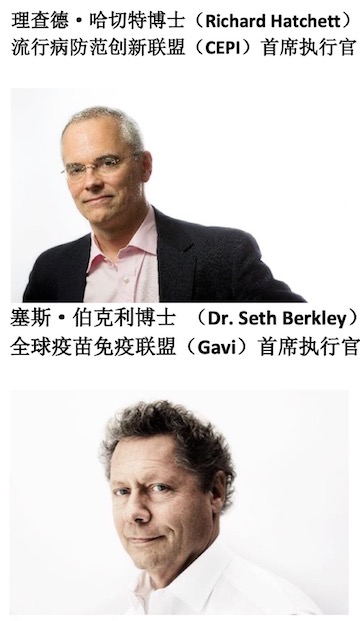
全球合作对缩短研发周期至关重要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仅三个月后,截至4月8日,全球有115支新冠疫苗处于开发过程中,其中78个已确认为活跃状态,有五个候选疫苗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尽管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等权威机构和专家预测,疫苗最快也需要花费12-18个月的时间才能问世,但这相比埃博拉疫苗的研发时间已经快了10多倍。
事实上,开发新冠疫苗的进程堪称史无前例。在人类历史上,麻疹疫苗的研发用了9年,埃博拉疫苗用了16年,脑膜炎疫苗用了41年。但这一次,在中国共享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的仅仅63天后,在美国西雅图就开展了首次临床试验。
而现今各界急切想得知的是,疫苗开发所需的18个月能被缩短吗?
哈切特指出,我们现在仍面临着资金和生产方面的挑战。他称,CEPI在疫苗研发中需要投入的20亿美元(现在仅获得8亿美元的支持)与总开支相比是很低的,采购、制造和分发疫苗所需的费用相较之下将会更大。
“我们已经开始进行全球层面的评估,可能需要80亿到280亿美元,具体取决于侯选疫苗是什么、需要多少剂量、以及多少制造商,所有的因素都可能使整个程序更加复杂以及成本翻倍。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让候选疫苗得以生产的早期资金,但随后我们将需要扩大规模,为全球采购10亿剂量,这将需要更多的资金。” 伯克利说。
而在全球生产方面,伯克利表示:“全球各地都出现停产现象,有21个国家已经面临疫苗的短缺问题,我们希望能够利用全球的运输系统来处理这一问题,在航班被取消或国家正在封锁的情况下,确保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及时地获取药物。”
伯克利认为,在缩短研发周期方面,全球合作至关重要,因为如果要确保安全有效的疫苗,有很多问题都必须各国共同谨慎思考。另外,世卫组织在动员全球科学界团结上功不可没。协调各国努力、利用共享信息、将其有效地提炼成可用于加速疫苗开发的战略,并确保疫苗开发商拥有所需的工具、材料、资源和试验品也十分必要。
对抗快速量产的生产力限制
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称,即使存在针对性的疫苗,在疫苗的可及性上也有很大的挑战。“我们可能需要有10亿支以上的储备才能够有足够的覆盖,人类历史上超过10亿支的单个疫苗只有一个,就是小儿麻痹症疫苗。” 李一诺介绍,“中国的疫苗产量是世界上的大头,10亿支疫苗是有潜力达到的,但(现在生产的)这都是有需求的疫苗,所以在提供新疫苗的产量上,仍需做相应准备。”
换言之,如果几十亿民众都亟需同一种新冠病毒疫苗,而各大企业又要继续生产流感以及麻疹、腮腺炎、风疹等疾病的疫苗,产能就会出现较大缺口。
伯克利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CEPI、Gavi联合世界银行的制造业工作组正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动员制造业能力的原因之一,就是避免挖东墙补西墙,确保常规疫苗的继续生产和注射。现在,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被委任的工厂开始投入使用,还有新工厂正在建设之中,此外一些有生产设施的合同制造商也可以发挥作用。
伯克利称,这不仅仅和疫苗生产有关,还有疫苗的制剂(fill and finish)。“而且我们谈论的数量是巨大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有大量人口的国家需要有能大幅度地扩大生产规模的系统,这包括中国、印度与世界上其他大国。这种制剂的能力对于未来发展也至关重要。” 伯克利介绍,“我们也需要大量的注射器、冷链运输工具等必要的物品。再一次地,这又将我们引回需要国际合作的讨论。”
哈切特则对一财表示:“这已经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目前正在开发的疫苗很可能需要与制剂流感疫苗同等的生产力。所以我们应谨慎地考虑全球对疫苗生产、疫苗制剂的需求,来搞清怎样更有效、更高效、更少干扰地生产新冠疫苗,同时不耽误其他疾病的疫苗生产。我们不希望为了解决新冠肺炎导致其他疾病再度重来。”
哈切特介绍,CEPI目前支持的一个项目就是使用某种疫苗作为基础架构,研发能产生双重疗效的疫苗,比如既能针对麻疹,又能针对新冠病毒。
此外,能否迅速扩大生产能力也与目标疫苗的类型息息相关。普华永道卫生产业主管奥马·尚(Omar Chane)称,如果生产的是mRNA疫苗,那么量产所需的投资将少于细胞基等传统方法,后者需要3-5年的时间、5-6亿美元资金才能建成生产线。
避免重蹈SARS复辙
2003 年,SARS 疫苗的研发投资因疫情结束而中断。但哈切特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在非典时期,疫苗资金链枯竭,导致研发没有继续,但这次不会重蹈覆辙。
“现在大多数的流行病学专家都认为,新冠肺炎恐怕会与我们长期共存,新冠病毒可能会无限期地存在于人群之中,所以未来对新冠疫苗的需求很大概率会是持续的。” 哈切特称,“毫无疑问的是,我们会将新冠疫苗的研发完成。但我认为,如果我们要通过在全球分发疫苗控制住疫情,我们不能将新冠病毒视为已被我们抛在身后,而是要将其看成是能造成全球风险的传染性疾病的一个典型例证。”
哈切特对第一财经表示,我们需要反思从这场大流行病中学到的教训,并思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机制、结构与投资,在未来从全球层面推动预防行动。“未来也还会有大流行病的。这已经是21世纪的第二场大流行病了。” 他说。
哈切特此前曾表示,成功的疫苗开发不仅取决于科学上的突破,还依赖于持久的需求和资助。疫苗开发是一件长期、高风险、高投入的事情,疫苗通常需要几年的时间去检测安全性和有效性。当前疫苗的开发难点不在于技术,而在立法和资源的调配。
哈切特说,商界和政府都对潜在的疫情缺乏防控动力,只有在疫情暴发之后才一哄而上,因此需要国家层面的调节,例如将如何让大机构的信息分享给小公司、什么样的政策可以帮助推进疫苗开发的进程、如果疫情消失研发如何继续发展。同时,国家也需要确保有投资者利益的政策, 比如提供提前储备医疗物资的公共资金。
如需获得授权请联系第一财经版权部:banquan@yicai.com
文章作者

为何它已成全球健康领域的主要威胁?达沃斯论坛上的专家开出了“药方”
新发传染病和抗微生物药物耐药(AMR),已成为全球健康领域的主要威胁,二者均与人畜共患病密不可分,而要有效防控这类疾病需克服两个挑战,即跨部门协作不足和创新成果推广难。

走过剧烈变化的5年,中国吸引外资正发生质变|“十四五”规划收官
在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外资将中国从原本的全球制造基地,转变为如今产研一体化的创新热土。

赛诺菲四价流感疫苗恢复在华销售
赛诺菲四价流感疫苗恢复在华销售

震惊愤怒!CDC专家被“一锅端”后,美国医学界要求特朗普政府撤销决定
卢里表示,小罗伯特·肯尼迪用来证明委员会存在利益冲突的数据“已过时”。

美国CDC疫苗顾问组被“一锅端”
美国疾控中心的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负责审查疫苗数据并提出建议,以确定哪些人有资格接种疫苗,以及保险公司是否应该承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