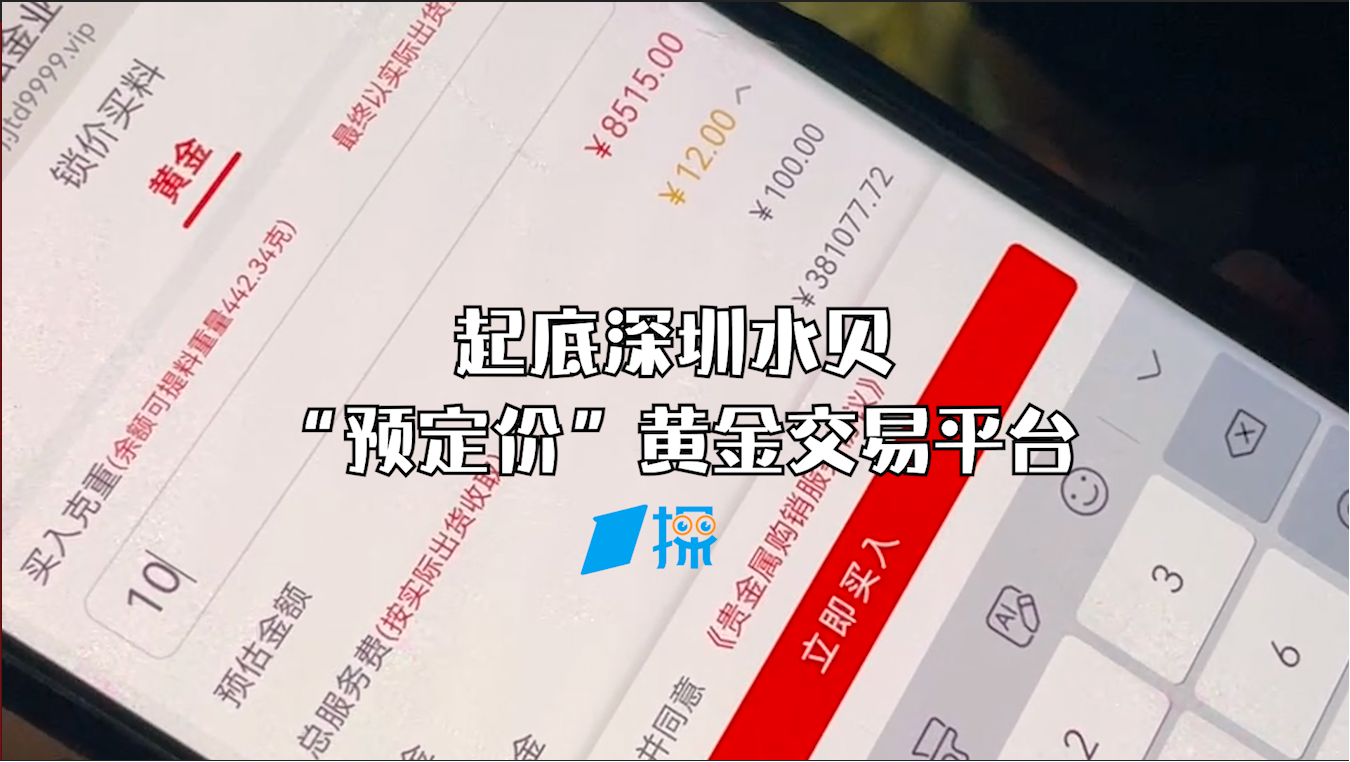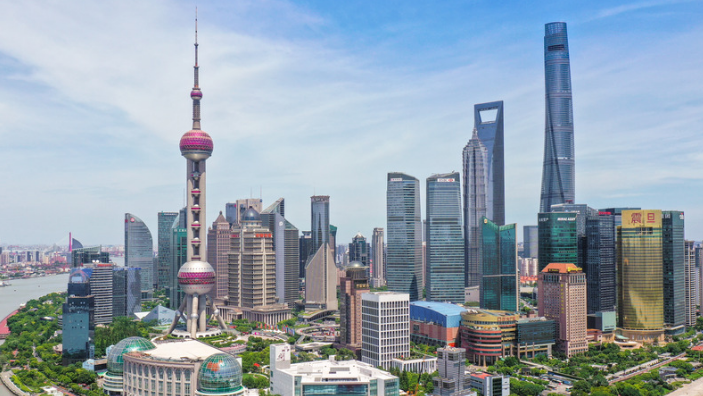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aisd}}
AI生成 免责声明
20世纪后半叶出现过一些今天看来很奇怪的跨学科潮流,比如试图用哲学和文学来分析政治经济问题,或把弗洛伊德派的心理学用来研究物种进化。社会科学作为一大门类朝着数据化、模型化大转向之后,此类方法论日渐式微,如今在社会科学界,恐怕很少有人会认真对待如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作为一名所谓“社会科学哲学家”的根本立论——不存在什么“集体性”或者“组织性”的行为,所有社会趋势变化都起源于单一个人行为。
埃尔斯特出生于挪威,在法国获得博士学位,曾是让-保罗·萨特著名的对家雷蒙·阿隆的学生。阿隆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似乎对埃尔斯特影响深远,他最著名的作品无疑是《理解马克思》(Making Sense of Marx)一书。埃尔斯特学术生涯的绝大多数时间在美国度过,也是在那里开启了英美分析哲学和经济学的思路,他也因此成为一种存在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独特学术范式——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尤利西斯与海妖:理性与非理性研究》
[美] 乔恩·埃尔斯特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21年7月版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尤利西斯与海妖——理性与非理性研究》(Ulysses and the Sirens,Studies in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是埃尔斯特的早期著作,写1979年。埃尔斯特的写法实在非常有意思,很少在同一本书里,你能看到笛卡尔、萨特、司汤达、普鲁斯特与丹尼尔·卡尼曼、乔治·安斯里、加里·派克毫无违和感地穿插演出。从这种意义上说,此书可谓引人入胜,甚至读完此书我竟无法分辨埃尔斯特本人的意识形态究竟偏左还是偏右。哲学和文学作为实证分析工具,用在诸如管理学院里常见的博弈论、理性选择理论或后来被“龙虾哥”乔丹·皮特森普及的进化心理学里,效果也确实匪夷所思。埃尔斯特在此书序言里已经开诚布公地自嘲了一番:“很多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他们生命中的某个时期很想写小说或诗歌,不料却发现自己并没有这个能力。还有人之所以选择哲学或社会科学,只是当他们发现自己的第一选择搞数学确实超出了他们的能力,才把它作为第二选择。眼下这部作品处在这两种失败的交会点上。”
就理性选择理论而言,埃尔斯特的一整套分析几乎是个死循环。《尤利西斯与海妖》一书第一章,埃尔斯特试图解决“完全理性”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众所周知,经济学里的理性基本是指市场决策意义上的理性,也就是效益最大化。埃尔斯特作为雷蒙·阿隆的学生和貌似萨特哲学的爱好者(本身就是个悖论),显然不能接受这种无聊的定义。比如他批评所谓“适者生存论”——“偶尔有人说,自然选择理论是同义反复;适者生存就是生者生存。如果我们所说的适应性指的是遗传适应的话,这个说法足够正确。然而,如果我们把适应性理解为生态适应,例如按照有机体的生命跨度来衡量的话,适者生存就变成了一个经验主义的命题,存在很多重要的反例。”埃尔斯特举了一个经典反例,也就是父母为子女做所谓“最优化选择”——人自身要“适应生存”,其最优的选择肯定是不繁殖;但为了所谓“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适应生存”,那么最优选择是生很多的孩子。在这一命题中,局部效益最大化和整体效益最大化是矛盾的。就像埃尔斯特说的,“大自然经常被看成一个经济学家,最优预算、线性规划、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如今也成为进化论的组成部分”。而实际情况是,大自然恐怕没学过经济学。
你可以认为——埃尔斯特也指出——进化论证明人和动物的区别正是能够放弃局部利益,选择整体效益最大化。那埃尔斯特又进一步否定了这种简单思维,就此他针对一些博弈论里常用的例子,如囚徒困境、保证博弈、胆小鬼博弈等,展开了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分析。例如,他认为在囚徒困境里,所谓的最优选项(合作、合作)对个体来说既达不到,也不稳定,因为它能稳定达到的前提是信息必须完整。所谓选择“整体最大利益”超过“局部利益”,你不得不保证你有足够多有关“整体”的信息,这正是囚徒最缺乏的。而“信息完整”是一个极荒诞的概念。好比一家大型公司在进行了所谓“充分调查”以后选择放弃投资某个行业,似乎这个结论是从“信息完整”得来的,但经验告诉我们,这所谓的“信息完整”几乎不可能做到。
埃尔斯特更是在讨论尤利西斯与海妖问题的时候,指出“只有人拥有这样的能力:以牺牲局部最大化为代价寻求全局最大化,但有一点同样是真的:只有人容易受到自控能力缺失(akrasia)的影响”。尤利西斯堵住自己和海员的耳朵,这可能是最优决策,但与此同时又是对自控力挑战最大,也因此最困难的决策。对这些“上坡任务”来说,一些“迂回决策”就事实成功而言反而是效益最大化的决策。更复杂的是,人对自己的意志力并没有信息充分的认识。人在面对“上坡任务”的时候,既有可能误判自己的意志力,也有可能在中途深思熟虑过后,放弃这项任务。这两种决策都不能说是非理性的。埃尔斯特在分析此类理性时,还强加了最后一个条件:“自我约束的行为必须是有为之为,而不是无为之为。”如一个人从小被灌输某种信仰,他既不否定也不肯定,去教堂却不听讲,这只能算无为之为,并非多么理性。被动理性,比如尤利西斯强迫他的海员把耳朵塞住,从并不一定有什么政治抱负的海员角度来看,是不是最优选择呢?埃尔斯特认为笛卡尔当然是对的,人只要有足够强烈的意愿,什么都能做到。如果这是理性,那么大部分人毫无疑问都是非理性的,他们缺乏自制力,没有预判的准确度,也不能充分理解自己意愿的强烈程度。
到头来真正的问题当然是另一个:究竟什么是理性?美国经济学之所以能把博弈论当作一种真正的科学来对待,可能因为对理性的定义比较狭窄。用埃尔斯特的例子,一个人困在森林里,最“理性”的决策很有可能是按照一条直线走。运用到美式经济学里,咨询公司可以告诉一家大公司坚持自己的老本行,因为调整策略或者寻求“最优策略”所消耗的成本可能会让这家公司破产,哪怕这家公司有转行或更新换代的意愿与追求。埃尔斯特认为“法国人过度的理性成为了经济理性的一个障碍”,也就是说,哲学理性与经济理性可能根本不是同一种理性。这不是简单的维度问题。比如在意识形态上,埃尔斯特刚援引完笛卡尔,就援引了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的说法——保持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省信息成本的方法,并因此一般意义上是一个理性的回应”。在某些领域不动脑子,对另一些领域是理性。想太多哲学问题,就很有可能挣不到钱。
再进一步,人选择或追求理性本身未必理性。《尤利西斯与海妖》的最后部分谈到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就尝试从哲学上解决的问题。爱、恨、情、仇等人的情感的各大组成部分,仿佛都跟理性有一定距离。这种错位非常复杂,无论是弗洛伊德所谓“本我”“自我”“超我”的区别(每一种都有其理性),还是萨特的“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两种几乎相悖的理性,就像埃尔斯特所说,“萨特的哲学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人念念不忘的是渴望听到自己葬礼上的悼词,好让他最终能够知道自己是什么”),或者经济学家眼里的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都存在极大的矛盾。埃尔斯特提到让·兰辛的小说《安德洛玛刻》(Andromaque),其主人公说“我爱你并不专一,我如何才能做到忠诚?”这几乎是此类理性错位的绝佳注解。一个上战场的士兵用反复说“我不怕”来掩饰自己的恐惧,它是自我欺骗的非理性还是为了被动履行某种社会合约的迂回策略?
在《尤利西斯与海妖》里,我们看到一个受了欧洲大陆哲学教育的人,在想方设法套用分析哲学和大众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这两种思想传统,对哲学(或者广义上的学术)的目标始终不太一致。分歧一直持续到今天,在数据分析盛行的社会科学框架下,个人意志就好像矩阵上的一个小点,几乎被默认不重要。一旦脱离集体理性,便成为数据异端。而事实上,埃尔斯特自己在学术生涯后期,对《尤利西斯与海妖》里这套理性选择理论已经不太感冒,认为正常人是根本不可能按照经济学学术刊物里的数学模型来做决定的。“没有任何非意向性的总体机制可以模仿理性。”

乔恩·埃尔斯特著作中译本:
《解释社会行为:社会科学的机制视角》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9年1月版
《理解马克思》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10月版
《逻辑与社会:矛盾与可能世界》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4月版
《政治心理学》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年4月版
《心灵的炼金术:理性与情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12月版
《社会黏合剂:社会秩序的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