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把社会责任内化为企业的追求,要求企业家“使真正有利于公众的事成为企业的自身利益”。
这个境界倘若实现,那便像孔子所言——“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矩内化在欲中,欲不再对抗矩,矩不再压抑欲。
能否既解决“富裕”问题又能解决“共同”问题,是时代性的命题,也是历史性的命题
三次分配进入基础性制度安排的时代意义
目前第三次分配的呼声很高,但从“8.17会议”的精神上可以看到,第三次分配有一个目标和前提——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我们要在这个前提下来看第一、第二与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我们要在共同富裕的前提下来看第三次分配,而不能局限于从第三次分配的角度来看共同富裕。
第三次分配已经说了几十年了,公益慈善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第三次分配和第一次、第二次分配要作为基础性制度统筹安排是第一次提出。
从根本上来讲,共同富裕具有历史性与时代性意义。
自现代社会以来,资本主义制度安排下的市场经济,创造了“富裕”,但没有实现“共同”。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现了“共同”,但是没有创造“富裕”。二十世纪,在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有觉悟的人对这些问题都有反思和认识。
美国在20世纪中叶,出现《正义论》为代表的政治哲学思潮,欧洲建构以福利制度来平衡社会的方式,这些都是对社会制度的矫正。我们中国也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开始着手改革,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既解决“富裕”问题,又解决“共同”问题呢?
这是一个时代性的命题,也是一个历史性的命题;这是一个中国命题,也是一个人类命题。我们能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既解决财富创造的问题,又创造性地解决共同享有的问题,实现一个共有、共享、共治的社会?现代化在西方世界首先实现,但是西方世界实现了大多数人的现代化吗?实现了所有人的现代化吗?
面对两个挑战:一个是国家内部的阶层、阶级、种族问题;一个是不同国家怎么均衡地享有人类创造的财富和现代化?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要面对的问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理解“8.17会议”,要看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共同富裕的目标,肩负着一个时代和历史的使命。
“8.17会议”强调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这不只是在强化公益慈善这个第三次分配的地位问题,而是从综合统一的角度看待三次分配。这里所言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不仅意味着第三次分配中有制度安排的问题,第一次分配中也存在制度安排的问题。
比如第一次分配中工农业产品交换中的“剪刀差”问题,农产品精加工后的部分利润返还原料提供者的问题,这是第一次分配中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对城乡收入制度性差距的消除关系很大。
又比如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我们最大的优势不在原创科技的创新能力,而是量产化的能力。但加工企业的利润所得很低,能在科技企业上市利润中适当回馈给提供量产化能力的加工企业吗?这也是第一次分配中的问题。
我们讲共同富裕,就应该考虑到整个产业链之间的合理的利润分配。总而言之,我们在第一次分配中,应该既创造财富,又有合理分配财富的制度性安排;既强调市场配置资源,又不是市场野蛮生长,然后再靠政策补救或慈善捐款。
在这三次分配的制度性安排中,第二次分配是一个关键调节因素,不但可以做政策兜底,可以提供公共产品,还影响甚至约束着第一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这次将公益慈善放在基础性的制度安排中,提高了公益慈善的社会影响力。
一般来讲,我们习惯将公益慈善看成一个社会发展中拾遗补缺的存在,但公益慈善的功能不仅仅是拾遗补缺。“8.17会议”将三次分配一体化放在基础性制度安排里,考虑的不是公益慈善有多大的量,市场有多大量,政策调剂有多大量——不是量的问题,而是质的问题,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
这次将三次分配放在同一个平台上构建、深化,一个关键着眼点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三次分配的制度对公益慈善事业的影响
中国公益慈善涉及的资金大概占GDP的0.2%,数量相当低。这次会议在第三次分配的制度安排中鼓励高收入人群、企业更多回报社会,将公益慈善提到三次分配统一的平台上考虑,这是一个真正的认知上的提升。这次提升对公益慈善界是一次鼓舞,对企业和高收入人群是一种鞭策。
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对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是个利好信号,但在利好的信号中间,我们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
一个问题是,我们要注意怎样把好事做好,避免把好事做坏。就公益慈善而言,做好的关键是坚持慈善的民间性、自愿性。如果最后鼓励捐款变成在压力之下的捐款,这就不是慈善捐款,这对社会将产生很大的破坏性影响。
我们现在讲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可以回溯到改革初期,改革开放以来,“共同富裕”始终是目标,步骤是什么呢?小平同志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这就是两步走的步骤。先富帮后富,这是应该的,但这应该基于道德和自愿。如果不对先富者予以肯定,就打断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步骤,实现目标也就无从谈起。
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企业家,我们首先要肯定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上、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所做出的贡献,这个群体应该受到尊重。
另一个问题是,公益慈善不能划界封闭,而应该更加开放,不能仅从捐款助困角度考虑问题,还要思考创造更好更创新的慈善形态,融合政府、企业资源来理解当今时代的公益慈善。
这里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思考:我们怎么理解受助对象?仅仅将他们看作待援助者,还是看作新的财富和社会创造者?我们怎么看待所谓“金字塔底部”群体以及他们的能量如何发挥?
这些问题对公益慈善发展都是新的挑战,我们不能仅从捐款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应该用更开放的视角来看待公益慈善的发展。
达不离道“达则兼善天下”,“在商言商”在商者言不尽于商
企业家从“在商言商”到“在商言商+善”
在中国传统社会,张謇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弃官从商的状元。张謇也不只是一个传统商人,他是中国近代民营企业和民间社会事业领域里的先行者和楷模。他办过二十多家企业和三百多所学校。他作为企业家的楷模,不仅是发展企业,拿出利润救助贫困,更是在于他推动丰富社会形态、发展社会建设的事业。他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商人,而是一个卓越的企业家、社会创新家。
企业家从“在商言商”到“在商言商+善”,这个“善”不应该是要求企业家以后不要“在商言商”,成为“在商言善”,而是希望企业家有更大的胸怀和视野,“在商言商”但在商者言不尽于商。
这样,“商”的内涵也会不断发展,将“善”注入“商”中,像获得诺贝尔奖的尤努斯,他开创的小额信贷模式,不是离开“商”来谈“善”,而是把“善”放到了“商”里面来谈。“商”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提升。
“达则兼善天下”是对企业家的要求吗?
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社会地位的序列是“士农工商”。但无论你身处哪个价值序列,中国人的价值观念都由儒家奠定,大家在价值观念上的目标和追求是一致的。无论你是书香门第、农家子弟、达官贵人子弟,还是商贾子弟,大家的启蒙读物都是儒家思想,如果有追求,都是“修身齐家”的理想。
从中国历史来看,一个君子,一个有品质的人,会有两种状态,可能得志,可能不得志。但正如孟子所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当人处在不得志的状态,穷,但穷不拾遗;当人处在有钱有势的状态,达,但达不离道。
对穷者和达者的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对达者观其所为,看达者做了什么,如果只是招摇过市,当然遭人鄙薄。
达时要帮助别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
穷时要观其所不为,一个人落魄时,要看他什么事情不做,为了生存也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啊!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儒家的基本操守,对士、农、工、商的要求都是一样的。严格说来,对士的要求更多,但商人也同样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王阳明曾说过,哪怕整日里做买卖,照样成圣成贤。这一思想大概受大乘佛学人人可以成佛观念的影响,大乘佛学转化到中国语境,深入中国儒家思想体系,就演变出人人可以成圣的思想。商人自然也可以,只要内心有一个“仁”的信念。
王阳明曾经有个精彩的比喻:尧舜万镒之金,凡人而肯为学使心纯乎天理,犹一两之金,但也是纯金!在“阳明心学”的鼓舞下,很多商人愿意支持教育公益和文化公益,支持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在当时成为一个风气。
将社会责任内化为企业追求,企业家精神的最高境界是使利于公众的事成为企业的自身利益
企业家精神是否还要加上社会责任或回报社会?
“企业家”这一概念不是自古就有,不能简单混同于古代“商人”的概念。1801年,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首次提出“企业家”这个概念,认为“企业家”是使经济资源的效率由低转高的特殊人才。从这个角度上讲,“企业家精神”是讲企业家的特殊的气质、技能和禀赋的一种结合。
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将敬业放入企业家精神中,企业家当然是敬业的、执着的。
后来,尤其20世纪中叶以来,现代管理学兴起,企业家精神更多被归纳为“冒险”和“创新”,这可能与两个人有关:熊彼特与德鲁克。熊彼特归纳企业家从事的工作,有过一种说法叫“创造性破坏”。德鲁克认为这种“创造性破坏”的本质其实就是“创新”。
德鲁克是现代管理学大师和奠基人,他认为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集中表现。同时,德鲁克认为企业家的“创造性破坏”具备冒险性,是一种冒险行为。于是,“冒险”和“创新”成为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涵。
企业家精神具备民族性和时代性。从民族性来看,不同文化中的企业家有不同的特质。张謇作为中国文化精神滋养的企业家,他对于企业责任、与雇工关系、商业博弈与道义操守的平衡等等方面当然与西方企业家有众多不同的地方,这就是企业家具有民族性的一面。
在当下中国,问题的关键不是企业家的民族性,而是企业家的时代性。100年前的企业家,将一个科技发明成果社会化、量产化,以解决社会问题,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创造巨大财富,为投资人、股东创造巨大利益就是优秀而成功的企业家。
但现在只有这些,是否足够呢?
近两年,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声明,不仅关注股东利益,同时也关注员工利益、客户利益、供应商利益、社区利益和环境。
对一个当代企业家而言,重要的不仅是产品是否优质这一基础问题,还要关注产品解决了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创造了多少公平就业机会,而且对于更多的关联方,对于公共利益要负起责任,这些问题都很重要。
我们如今强调企业家精神的民族性,更要强调企业家精神的时代性。当下时代与一百年前、五十年前、中国改革开放初都不一样。时代对企业家的要求也不一样,当下的企业家需要一种更高的追求。
企业家对企业管理的最高责任和最高境界是什么?20世纪50年代初,德鲁克在他的现代管理奠基之作《管理实践》一层一层地推论管理者的责任,最后提到“终极责任”高度的是:“商业企业在管理过程中必须把社会利益变成企业的自身利益”。
把社会责任内化为企业的追求,要求企业家“使真正有利于公众的事成为企业的自身利益”,这个境界倘若实现,那便像孔子所言——“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矩内化在欲中,欲不再对抗矩,矩不再压抑欲。企业家可以最大化地追求企业利润,追求企业要实现的发展目标,但这些追求都不会违背社会的公共利益。
(作者为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
文章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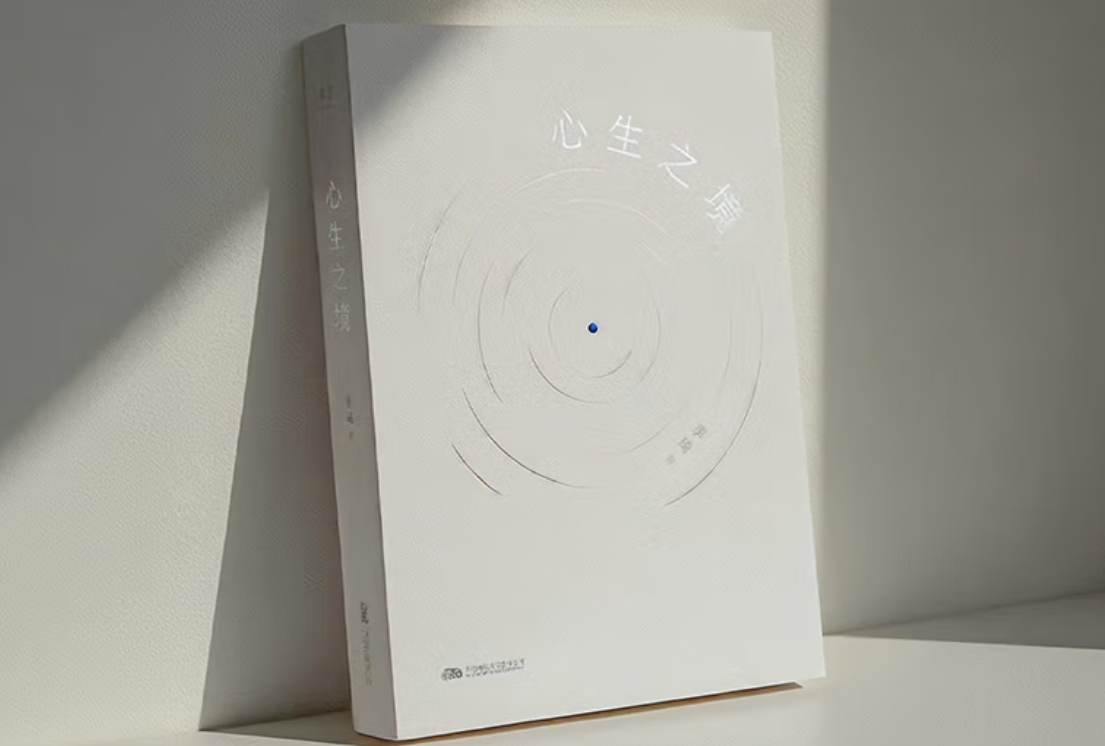
一个企业家的人生归宿,是“见自己”
季琦的成长之路上,经历过三次“至暗时刻”一般的危机。

普京:恢复与美国的全面关系符合俄罗斯国家利益
普京还表示,俄罗斯愿意持续稳定地向美国供应铀。

谨慎筹划遗嘱信托,破解企业家资产传承困局
为了避免家属子女在自己百年之后争夺家产,企业家最好提前立有遗嘱,委托信得过的专业机构或者律师等专业人士作为遗嘱执行人,并且对于接班人的培养和公司人才梯队早做安排,实现平稳过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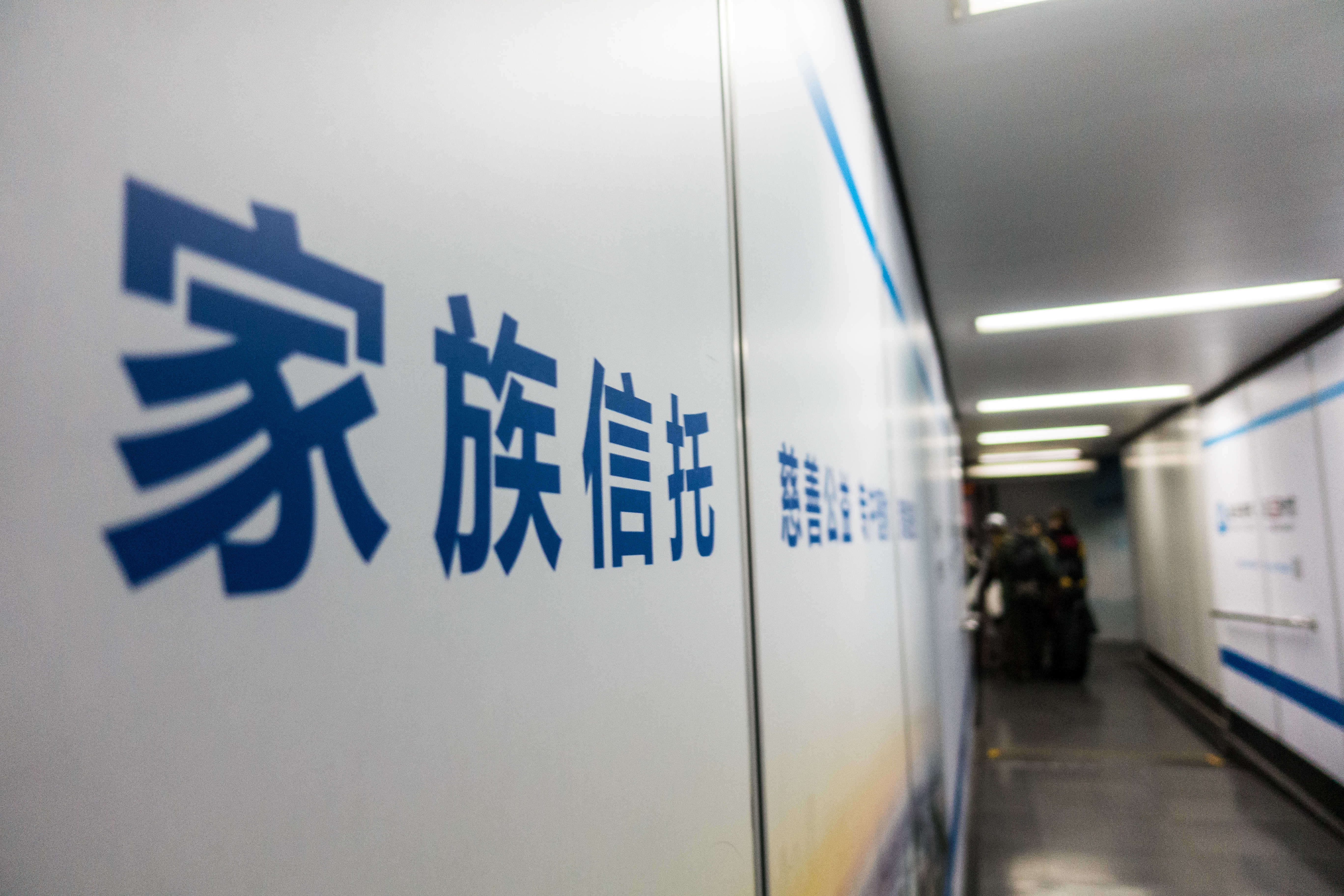
因娃哈哈而引爆,中国富豪热衷的离岸家族信托有多神秘?
所谓的“击穿”可能仅发生在两大类信托里。

复旦孔爱国教授:中国企业家要做卓越的有自己特色的产品,不要抄袭
在中国有14亿人口的大市场和发展的要求,企业家承担着生产与创造财富的使命,也有不输别人的能力,但不应该去抄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