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aisd}}
AI生成 免责声明
“碳减排”与“防风险”之间的关系
就目前如何在稳增长和降碳之间形成平衡,需要我们在更为宏观的角度来把握这些参数之间的科学关系,因此需要我们进行深度的科学研究。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从整体方案、不同的情形假设提出了我们必须在一些积极的方案下面来获得稳增长与碳达峰行动之间的耦合路径。要走出目前的低迷状态,其中一种很重要的方式就是绿色复苏。绿色复苏需要通过我们加大对绿色转型的一些投资和技术创新,使短期有效需求得到扩张,从而形成一种短期需求扩张、中期供给改善的有效路径。
这实际需要我们进行一些科学的规划。为什么绿色复苏更需要顶层规划,顶层设计呢?这与绿色复苏的一些特性有关联:
第一,加大绿色复苏的投入,对于投入企业来讲是一种负担。因为我们整个绿色技术的改造需要相对漫长的过程,它比我们传统的技改可能还要长。所以这些绿色技术的投入很难马上产生收入效应和市场效应。第二,对于大量绿色技术的创新实际是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的,因此它的收益面临巨大的风险。第三,即使我们进行了很好的绿色技术的创新和绿色基础设施的改造,这些改造面临大部分公共品的属性,市场短期很难给予这些绿色产品以完整的市场定价。这样就导致我们所看到的绿色投资与传统投资之间存在很重大的差别。简单地按照市场法则是难以形成短期市场需求的,这是需要高度重视的。
要认识到绿色投资在很多行业对于GDP的拉动,对于我们潜在增速的拉动,对于其他潜在的技术变化具有差别。这种差别体现在:一方面是它的投资层数与传统的投资层数不一样;另一方面是大量的绿色投入在本质上是一个成本概念,就是我们进行碳排放的这种确权。为了减少这种碳排放,实现绿色能源的转型、绿色技术的改造,本质上很难直接从收益端产生作用。
因此,要利用这样一些投入来提升公司价值,往往表现得很不完备。这就要求政府要用更大的力气加大规划,做好一致行动,对于绿色投入给予一定的前期补贴,形成有效运转、平稳转型的内生动力机制。这也就是为何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要求我们顶层设计要更为科学,及时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
更重要的是顶层科学设计要避免层层分解,特别是运动式的层层分解,这也是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为什么我们通过传统的行政监管和运动式的分解,在绿色和“双碳”中间难以达到它的结果呢?这在于:
首先,碳达峰并不要求每个部门、每个区域同步达峰。碳达峰的过程中,有些部门必须率先达峰,有些部门有可能在达峰之后,由于它的特殊性还会继续增长。因此,我们碳达峰的概念是国家碳达峰的概念而不是每个部门碳达峰的概念。
其次,如果考虑这些结构性因素就会发现,同步进行碳达峰会带来很多行业瓶颈性的因素产生,从而导致很多国民经济的循环由于瓶颈效应而出现断裂。这使得我们不是因为技术创新而达峰、在能源体系转型过程中进行的达峰,而是在人为的经济降速过程中进行达峰,这种达峰显然有损于我们生产力的发展,有损于我们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完成的模式。
最后,基于以上几点就要考虑“1+1”是否等于2,很可能会“大于2”。而且要考虑分解过程中,大家会继续忽略技术创新的问题,都会忽略公共投入的问题,会忽略后期的绿色产品完整定价的一系列问题。把这一系列问题考虑进来,我们要考虑到这种简单的减碳模式会比我们社会成本高得多,我们近期采取的社会准则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因此下一步应当在科学测算和一些技术创新上面有更大的作为,在这样一个新的一般均衡模型下,对各个方案和各个部门转型路径进行很好的研究。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文章作者

德国副总理、外长先后访华,德企业家怎么看中德经贸合作
施莱格尔说:“我们不需要所谓的政治考量,未来只有通过加大与中方伙伴的合作才能更好地应对不断涌现的挑战。”

用“巧劲”激发消费,上海打造国际化餐饮文化城市名片
10月份上海餐饮收入今年以来首次单月同比回正。

全球石油需求峰值被延后,中国石化行业“绿色转型”如何加速
刘婧认为,“十五五”期间,中国石化行业在能源结构、技术路线和市场格局上将发生显著变化。

一财社论:城市更新需要“硬件”“软件”相结合
城市更新是房地产发展进入新模式阶段的重要举措,关系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在规划、资金、运营、治理着力是重要抓手,从深层次解决存在的矛盾是加大改革力度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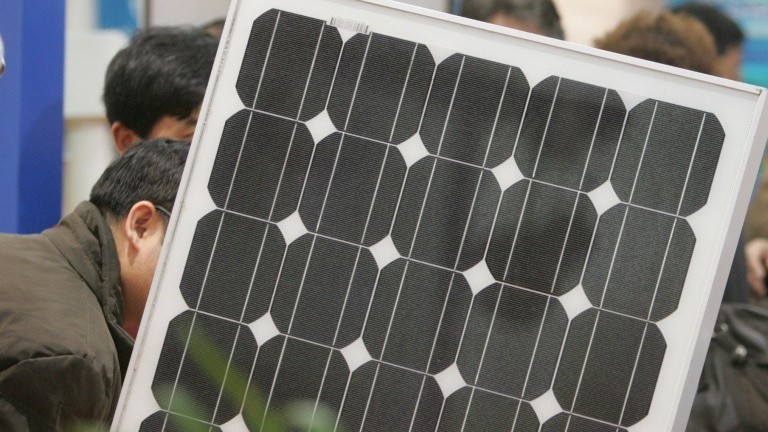
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能源转型有了新要求|“十五五”产业前瞻
《建议》提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提高新能源供给比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