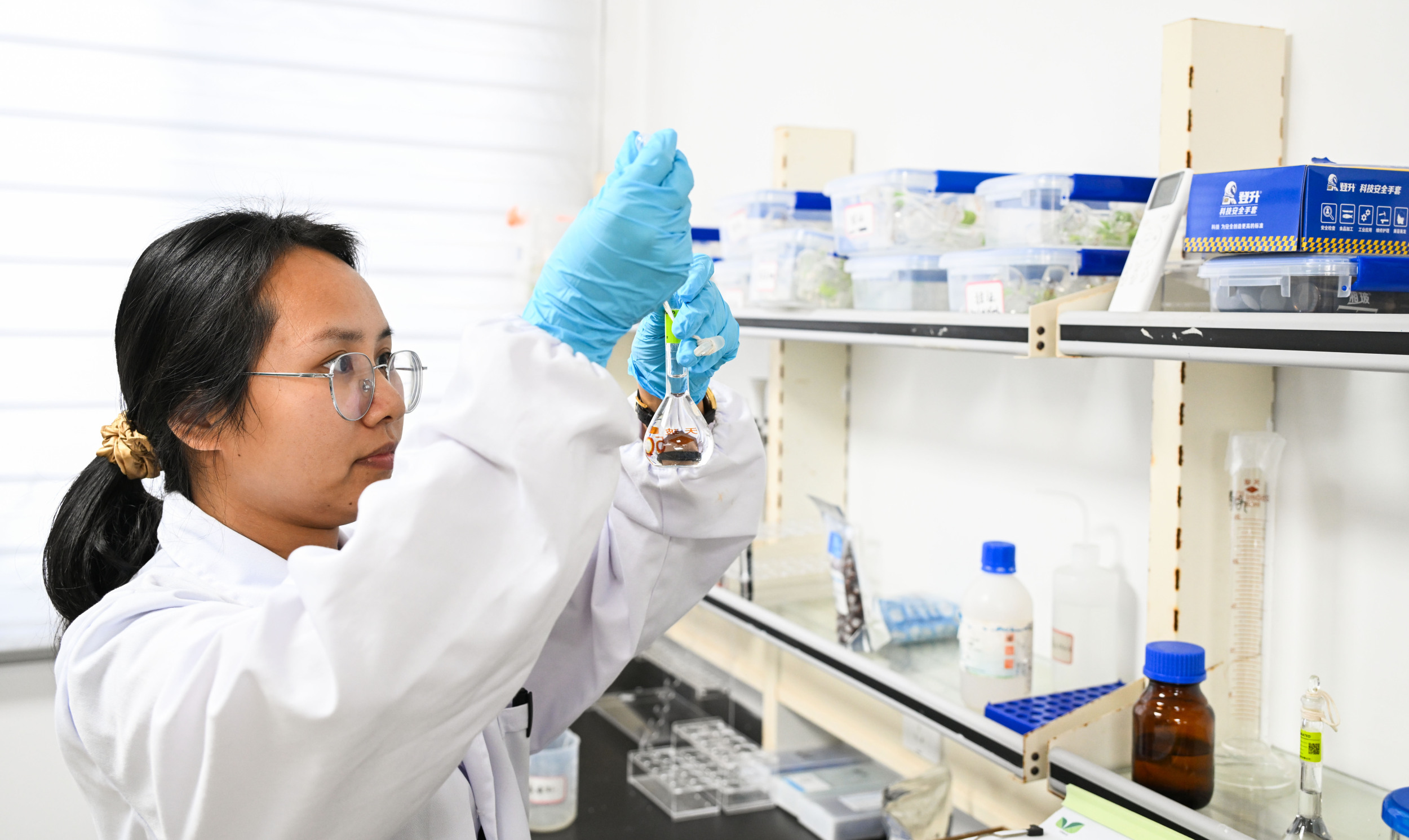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aisd}}
AI生成 免责声明
6月29日,2022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正式公布。自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第五轮全国医保目录调整工作启动了。与此同时,第七批国家组织药品带量集中采购,也将于7月份启动。笔者发现,上述两项国家医保局的年度重磅工作都在规则设计层面逐步脱离唯低价论,更多引入药品质量、理性竞价等因素。然而,各医药企业切不可掉以轻心,价格虚高者仍将被同行挤出市场。
医保基金是全国公立医疗、药品市场的最大埋单方。自2009年新医改启动以来,为遏制药品费用增长过快引发政府、患者巨大负担,医保基金管理方被赋予“控费”职责。通过药品带量采购、医保国家谈判等工作,国家医保局实施“灵魂砍价”,一度将单一产品谈出全国乃至全球最低价。
但问题是,我国的医药产业链面临“双轨制”:上游的医药产业高度市场化、资本化;下游的公立医疗服务业则要求回归公益性,自新冠疫情以来,更是强调去商业化、去资本化。上下游不同的诉求造成以下后果:控费措施在挤压药品流通环节过高营销费用乃至非法医疗回扣的同时,挤压了医药产业合理的回报空间,同时也挤压了创新药企业用于投入后续研发的充足利润空间。
一个鲜明的信号是,今年,国家医保局将稳住经济大盘、支持医药创新作为本职工作。国家医保局近日的专题党课上,该局局长胡静林提出,要坚决贯彻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中央指示,全力发挥医保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笔者认为,2022年国家药品谈判正在“亲创新”方面取得若干突破:一是为罕见病、儿童病等临床急需、价格攀高、供给不足的药品设置了单独的申报通道,离医学界、产业界长期呼吁的给予单独的谈判通道、支付阈值,又近了一步;二是在企业申报资料方面,跳出单一经济性(对医保基金的影响)维度,引入药监部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卫生部门的(健康)公平性、产业和科技部门的创新性等维度,首次提供申报资料幻灯片统一模板,初步实现“三医”主管部门价值模型在评估维度的统一;三是防止企业落选恐慌,竞相报出最低价,国家医保局破天荒地向企业开放自身品种的医保基金支付数据,为各企业理性竞价提供数据支持;四是设置价格保护线,当企业报价低于医保的意愿支付价70%时,将按照后者支付,以避免出现不可预期的超低价,给该企业或同行其他企业后面几年医保谈判带来很大被动。
不光是国家医保目录调整,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也在行动。在国家组织药品带量集采期满后,各地开始组成省际联盟续标。笔者了解到,在长三角的续标方案中,在上海医保局和药监局联动下,首创性地引入“不良反应监测”这一临床疗效指标。在国家医保局将部分品种的采购权下放到省际集采联盟之后,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陈金甫近日要求,坚持国家组织集采、省际联盟集采同等标准推进。近期,部分发达地区的联盟集采在竞价规则中首次引入“规模分”(市场规模占比)、“信用分”(其他地区集采的履约率),以遏制一些低小散医药企业的劣质产品通过恶意低价中标。我们决不能出现为药品安全性、有效性承担成本的合规企业反而丢标的“逆淘汰”局面。
即便“唯低价论”正在告别历史舞台,但笔者提醒广大医药企业不可掉以轻心,有两类企业可能成为医保局的“杀价”对象:一类是长期利用信息不对称中标/进目录企业。国家医保局已经在“十四五”时期启动全国医药价格监测工程,并依托今年建成的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广泛采集真实世界中的数据。国家医保局一旦发现企业低报销量、高报价格,不仅会狠狠地“以量换价”,还会借助医药企业信用评价机制予以惩戒,甚至让信用评级为“严重失信”者丧失区域甚至全国的医保市场。
另一类是继续维持高额医疗回扣“带金销售”模式的企业。它们“重金”收买目标医院、医生,诱导其使用自家集采未中选/未进医保目录品种,排挤已中选/已进医保目录品种。这几年,集采地区所有公立/民营医疗机构甚至连锁药店都参与集采,高价品种的“院外市场”越来越小;医院通过低报用药量以腾出空间用“回扣药”的行为也受到卫健委、医保局严密监控。国家医保局甚至联合财政部将落实集采、目录政策等指标纳入对地方医保局的医保基金绩效评价。从此,规避医保砍价、维持虚高药价的旁门左道有望被完全堵死。
(作者系价值医疗顾问专家委员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