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叱咤的夜云漫溢过了9点半的时钟,我在一条一侧长满杂草的路上骑行。我是第二次走这条路,不少人都在走,因为主干道被封住了,人们不得不循这条斜向的道路绕行。就在我的右侧,出现了一栋7层楼建筑,像教学楼,却更为宽而扁,从正面看,走廊与柱子形成了一个个一样大小的长方格子,每个格子里都有一道门,走廊都打着白灯,亮堂堂的一片。
忽然之间,四面八方,那大楼到处闪烁了起来——似乎是拉灯闸了,每一盏灯都在闪,有的快些,有的迟钝些,有的闪了几下就灭了,像力竭的飞蛾倒地而死,有的持续地闪着就是不灭,有的灭了之后又亮了起来,仿佛知道有人会回来取遗留的物品;一分钟过去,还有零星的灯在倔强地闪动,大部分的格子都灭了,没有熄灭的那几个正式进入守夜模式。
我仔细等待它的终局,觉得这其中的趣味绝不亚于一场节日烟花。每两个格子之间有走廊互通,而里面是比邻的房间,就像是四通八达的血管、脂肪包裹着脏器一样。灭灯的时候,随机产生的图像令我着迷。每个方格似乎都有个性,有的迟疑,有的果断,有的故意拖沓,甚至有情感流露——爽快地灭掉的方格就有一副“爱谁谁”的样子,迟疑的方格似乎在根据周围的方格调整自己的动作。我不时想起段义孚先生,这位地理学教授,也是“地方”的主张者和颂扬者,希望我做好同任何一个地方“相遇”的准备。

最广义的游戏
1998年,段义孚教授结束了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15年教学生涯后,以“首届美国地理学会斯坦利·布鲁恩地理学创意奖获得者”的身份,正式荣休。这个奖,是为表彰“地理学的原创性、创造性和重大智力突破”而设立的,段教授当之无愧,他的书,是我所见到的、继《空间的诗学》的作者加斯东·巴什拉之后最具有“宇宙视野”和“事物想象”的学术写作,其原创性存在于每一个段落的每一个句子里。“地理学家”于他可能仅仅是一个“身份”而已,便于让他被相关的科研机构收入,成为学术体制的一员,但他的光是不能被那区区一个格子所拘束的,而是被许多人感觉到。地理学或许关乎土地形态、气候、水文之类,但段教授将“地方”一词拔到了关键位置——地方的情感基调,地方的社会意义,地方具有的人文解读的潜能。
这些主题毫不抽象。我们都知道,人是很晚才懂得何为“城市”的,之前,人要在土地上谋食物,谋安全,为此制造了工具、建立了家宅,因此地理学家也更多地研究人如何面对自然界,以满足自己在食物、安全这些偏物质、偏经济的需求方面的作为:砍伐树林以开辟农场,清除杂草以播种耕耘……所以,地理学家往往对经济方面的关注较多:物产、人口、资源分布、植被、动物,这些都可以归结到经济上来,一个地方的人生活在那里,就是在依赖资源、创造“财富”。
但段教授讲,人们也为了另一个目的而施展自己的力量和智慧,那就是游戏。游戏,这是一个最广义的游戏,甚至比约翰·赫伊津哈的名著《人:游戏者》中的游戏更为广义。游戏无关经济财富,而有关人的感受,“精神需求”:一家剧院,一个马戏团,一座教堂,是为游戏而存在的,它们本质上无关财富生产;一件雕塑、一幅壁画也同样,推广来看,一根柱子,一棵栽下去的树,甚至一块油漆过的墙面,一个每天都有许多人走来走去的路口,也不妨说是一种游戏式的设计。
它们都耗费了人的精力,它们产生的成果,影响到在这个地方居住的人的精神世界,这影响的意义往往是复杂的,高度地因人而异,例如,一个街区内建起一座喷泉,十年之后,被这喷泉陪伴长大的一代人,在记忆之中存入了很多美好的印象和时刻,却也要面对喷泉在现实中渐渐成为一组再也喷不出水的生锈铁管子的事实。再例如,马戏团在很多人尤其是孩子的心目中,会是他们和地方建立连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一次次观摩演出、一次次欢笑和热烈鼓掌中,他们同这个地方的联系无形中得以深化,有朝一日,当他们的思想成熟到能思考自己与城市的连结时,他们会想到马戏团带来的快乐,但或许也会想到有那么几次,离开演出场所时,看到耍猴人、杂技演员和魔术师疲乏地走在路边、无人问津的模样。如此,他们对地方的感受,就会成为一种绵绵不绝的记忆唤起和反刍的过程。
这种联想尽可以扩大、延伸:一盏路灯也会有游戏的味道,而不仅仅意味着照明的功能,因为灯光有颜色,灯杆有造型;一条道路上,一扇从来不见打开的旧门,也是人反思“地方”的一个抓手,它并不是人为了娱乐或美观而故意立在那里的,它就是各种因素、各种力量加上时间形成的一个事物。段先生讲,我们不单单要探查身边的一样东西的(往往阴暗的)来历——比如一个声名在外的剧场,当初建造的时候闹过工人罢工——重要的是,我们要反复地自问:我对这个地方是什么感受,我的行为习惯、我的心理、我的性格之中,有多少痕迹是因为和“地方”发生密切的互动而留下的?要是用一个更接地气一点的表述来例证他的观点,或许可以问:在一个到处卖烤栗子的城市长起来的人,跟在一个到处卖臭豆腐的城市长起来的人,他们到底有什么不同?
一种持续的相遇
退休后,段教授在麦迪逊大学他任教的系里仍然保留着办公室。他从来不关门,以便任何人可以走进来与他讨论问题。他有一个独特的贡献:几十年间,他持续不断地给他“亲爱的同事”写信——系里系外的同事以及朋友,都读到过他基于一个更大的政治、教育和社会变革的背景,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对其中不变与变的思考和讲述。他的信件都辑到了一本书中,另有700多封信件则被存入档案收藏。他还有一个著名的习惯,就是在寓所附近的星巴克里拿着书,一边读,一边观察周围的人。
在那里,他有一把特别的椅子,有一张最喜欢的桌子。他管这里叫“倾听站”,本科生学习微积分、讨论历史考试的声音,他都能偷听到。当然,对自己所适应的星巴克这个“空间”,他的思考绝对是从第一次进入这里坐下时就已开始,他绝对相信,在这家星巴克里,年轻人探讨学业、寻找答案的方式和感受,和在其他星巴克里、同样的人群做同类的事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现象,是两种不同的独一无二。
在段义孚这里,地理学和人类学是最亲近的学科,两者最大的贡献也是最大的乐趣所在,都在于探察“不同”。说起一个个地方的“不同”,一般人只能想到一些宏观的不同:中国和美国不同,北京和上海不同,农村和城市不同,海洋和陆地不同……也许,你会向一个初次到达你所在的城市的客人介绍你对这城市的了解,告诉他说,某某区多有富人居住,某某区有美食街,某某区小偷出没,某条道路爱堵车而某条道路名人故居林立……无非如此。而我们不妨看段义孚的一番话,感受他的视野。前年5月,他接受一次邮件采访,访问者问他近来的感受如何。他回答说:
“我住在麦迪逊的8楼。我经常向下看我下面的城市景观。在公假日,它的空无一人让我震撼,空旷使它看起来像一个正等待表演开始的舞台。而在工作日,街道上车水马龙,但只有当我推开窗户,听到轰鸣声时,麦迪逊才算真正活了起来——而我也跟着活过来了。封锁,意味着我脚下的城市仍然是一个空无一人的舞台,周而复始、月而复始地毫无生气。但我在想,如果我看到的不是麦迪逊,而是香榭丽舍大街,远处是凯旋门,我还会认为眼前是一个可怕的场景——一个没有生命力的场景吗?也许就不会了,这是因为城市建筑可以是一件艺术作品,而艺术作品有其自身的美和生命。”
这就是段义孚,一段回答访问者的邮件文字,就可以出现在他的任何一本书中,不管是《逃避主义》还是《空间与地方》,是《恐惧的理由》还是《回家记》,是《人文主义地理学》还是《浪漫地理学》;也可以出现在他的一则短札里,或出现在他的一次不成文的聊天中。它谈不上是段先生的“思想”,毋宁说,它是他思考问题的基本方式。这段话的关键,并不在于他用想象巴黎的方法来驱散对封锁期间的麦迪逊的不良感受,更不是像很多人爱说的那样,用文艺青年式的白日梦来自我安慰——而在于他所坚持的一种持续的“相遇”:人与他所居住的地方的相遇,而地方则意味着一个加斯东·巴什拉意义上的物理“空间”。
为什么他说,只有在打开窗户,听到楼下的人车嘈杂后,他自己才“活过来”?这并不是夸大其词。人的活着,应该是一种与一个地方真正相遇了的主观感觉,活着的人,应该类似于一个通了电亮起的灯泡。以我自己的体验来讲,看到一幢大楼熄灯的场景,足以让我对这个地方产生感情,因为在目击的时刻我“活了”,我不需要想象楼里发生了什么,我仅仅是在那里,感官活跃,头脑发亮。
人总要选一个地方生活,就像身体总要选一套衣服穿进去一样,“我心安处”的地方和“合体”的衣装,都是一种涉及纯个人感受的东西。居住、工作、成长、变老,在这个 过程中,人与他所在地方逐渐融为一体,但也可能在饮食起居上相融,心理上则始终格格不入。我曾遇到不止一个人,对我说他对他生活了十几年、几十年的城市厌之入骨,我喜欢他们,因为他们敢于通过厌恶来居住,能够对初次相识的人说出这种态度,是需要相当的自信的,说明他们真正在追求“我心安处”,而不是活在表层。在段义孚的思想中,人充分地成为自己,就要靠和居住的地方持久“相遇”,形成联想、印象、忠诚和厌恶的方式。
人文地理学之父
段义孚被称为人文地理学之“父”,这一点其实令我有些意外,因为我以为,这样一种地理学早就应该有了,在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和城市化生活兴起的时候,这门“分支学科”就应该有了,因为自从有了城市,人与人生活的差异就开始凸显,此“地方”和彼“地方”的生活体验之间有了很大的不同。城市总是“地方性”的,所以像巴黎、维也纳、纽约之类的城市才会前赴后继地以“世界之都”的名号为荣,以让来自各个地方的人产生家园感为自己的骄傲之本。
然而,在读过一些段先生的文字后,我明白这个“之父”的名号为何会落到他头上。实际上,他是不愿意承认这是一门学科的,更不想被人看作什么“创始人”“掌门人”之类,因为他知行合一,他知道只要是学科,就意味着专业化,就意味着僵化的“专门教育”,教师就难免要沦为有学阀味的角色。他在一篇讲“人文地理学”这一名称的文章里,首先就呼吁说,不要去联系那些教条式的科研法,那会令“曾经的解放者变成审查者”,变成只会批改作业、审查答案对错的人;他说,一个人文地理学家应该密切地关注地理现象和人类意识,更认真地对待人对地方的依恋情绪,赞扬人类主动打破习惯模式的力量,进而要澄清与空间有关的概念和符号。
主观和意识和感受,是最难把握的,当然也是更难以“教授”的。段义孚的每本书都像是一篇篇散文,会让我想到那些不能归类的作家,那些文体意味十足、不在乎读者能“读懂”多少、“领会”多少知识的作家,比如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在他的《柏林童年》里,有一篇千字短文,题为“马格德堡广场边上的农贸市场”,他对该市场没有任何“概述”,而是写道:
“在我穿越这个市场的习惯方式之中,该市场所有通常的画面也变得模糊不清,以至于它不再具有原来买和卖的涵义。在推开那扇紧紧的、稍弛即收的弹簧拉门穿过前厅之后,首先入眼帘的,是被养鱼水和冲洗水弄得湿滑的瓷砖地面,走在上面很容易不小心一滑而踩到胡萝卜或莴苣叶。在编了号的铁棚屋后面端坐着那些胖得步履维艰的售货女人,她们是掌管可买卖物品的女祭司,是兜售各种田里长的和树上结的果实,各种可以吃的鸟类、鱼类和哺乳动物的集市女人,是拉皮条的女人。这些被绒线裹着的大块头神秘地在售货棚之间互相交流……”
不需要人人都像本雅明这样写作,但他所示范的与一个地方的“互动”,却正是段义孚的人文地理学书写的样本之一。这个学科讲究的具体,是主观,也因此它才显得飘逸而美丽;像《空间与地方》《浪漫地理学》这样的段氏作品,实际上都应该和巴什拉的《空间的诗学》《火的精神分析》一样,去一段一段地念,让它们填满自己的大脑而不是送来各种结论。
当我慢慢离开那座楼,继续骑行的时候,我想到,读段义孚先生的书就像看那样一座楼,看它在每一夜的窸簌闪耀之后,形成一个怎样的图景。
【人物简介】
段义孚(Yi-Fu Tuan,1930-2022),华裔地理学家,生于天津,曾在伦敦大学学院学习,毕业于牛津大学。
段义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思想在世界地理学界有重大影响。他将人的种种主观情性与客观地理环境的丰富关系进行了极具智慧的阐发,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
美国中部时间2022年8月10日,段义孚逝世,享年92岁。
【段义孚著作中译本】

《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译林出版社2021年7月版

《人文主义地理学:对于意义的个体追寻》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5月版

《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2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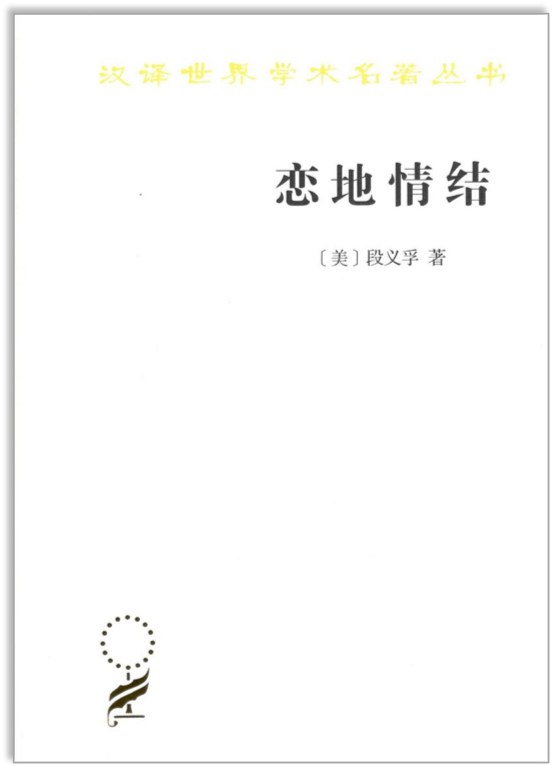
《恋地情结:对环境感知、态度与价值》
商务印书馆2018年5月版

《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2月版

《回家记》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1月版

《无边的恐惧》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

《逃避主义》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