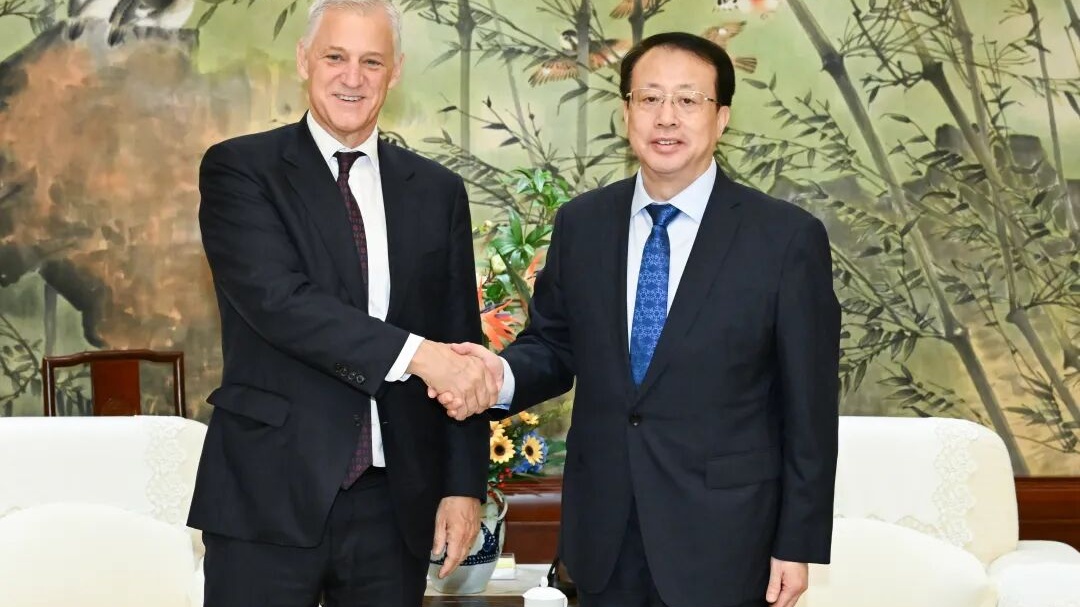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aisd}}
AI生成 免责声明
过年住宝山姨妈家,除了领略了一把吴淞口如同虎门销烟一般的烟花盛况,就是发现可以在大电视上看《繁花》。因为此前只在手机上零星看过几集,就索性霸占着客厅,开了两个通宵一口气看完。
我不太爱追剧,除了太长没空一直跟进,就是因为电视剧拍得再好,哪怕墨镜来拍,跟他自己的电影比,多少也还是粗糙。而且说什么抬高了国产剧的水准、用拍电影的方式拍电视剧之类,也就那样。就举一个例子,你仔细去看看柳云龙多年前的谍战剧《暗算》,那才是刷新国产剧水准的作品,早就用上了“伦勃朗式”的光影,近乎胶片的质感,演员也无可挑剔。但是——转折一下——但是,《繁花》依然非常上头,也的确是好看,否则也不可能三天睡不到十小时来把它一锅端。
重看第一集的时候,80后的表妹正好在旁边,看到爷叔指导宝总赚到第一桶金,她问:一万块在当时应该还是很大一笔钱吧?我说,虽然不如“万元户”那时候大,但对我们普通人,的确也不是小钱了。我正好对那时候的“一万块”有蛮切身的体会,可以讲两个很小的小故事。

一
我是90年代初大学毕业,比阿宝们大概小十岁上下——顺便提一下,《繁花》那拨人,其实就是《芳华》那拨人,也就是我们最小的叔叔阿姨,或者最大的哥哥姐姐。《繁花》高潮段落那几年,我们刚刚开始混社会,适应得很艰难,因为面对的世界,跟仅仅三五年前我们在大学里看到的那一个,已是天翻地覆的不同,变化实在太剧烈了,剧烈到我头脑一片空白,完全手足无措,不知自己到底有什么活下去的理由。
最终我选择了(其实谈不上选择,因为基本没其他可能性)以黄河路的对立面进入社会——今天看来这近乎碰瓷,蛮好笑的。作为本地第一代摇滚青年,宝总们赫然就是我们的假想敌,但是我们是以一种粗糙生猛不计后果的方式站到他们对面的,正如他们粗糙生猛不计后果地一头扎进股市和生意场。30年后回想,其实粗糙生猛不计后果,正是两边共通的时代气质啊。
不少人知道我前些年开过家书店,叫mephisto。很少人晓得,mephisto正是我给30年前我们开的那家摇滚酒吧起的名字。那就是一个情结,所以多年后依然不计后果地要以一家失败的书店来让当年那家失败的酒吧转世。失败就这样循环相生,粗糙生猛不计后果也就这样一次次借胎还魂。
二
几个月前,我请一个老朋友吃饭,吃完,溜溜哒哒去了他家,坐在15楼的阳台上喝他再三推荐的朗姆酒,抽他自己手卷的雪茄,俯瞰延安路高架上稀疏的车流。两个钟头后,大家都有点喝多了,话题开始无限发散。然后他女人突然半开玩笑地说,今晚这顿饭她会记一辈子,因为这是认识30多年我正式请他们吃的第一顿饭(另外据说还非正式地请过碗面,这个我倒是不记得了)。然后她当然又问了下去:为什么从来都是他们请我而不是我请他们吃饭?
我瞬间头脑极为清醒地回答,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表面的,我直接可以告诉你们,因为你们从来比我有钱得多,而我是个上海小市民,我的原则是绝不请比我有钱得多的人吃饭;今晚之所以请你们,是因为经过这几年,你们生意失败,公司破产,虽然其实你们还是比我有钱,但至少在心理上,我们差不多拉平了,我可以“破戒”了。还有一个秘密理由,你们想听伐?想听,我就借着酒劲说出来。
那是1993年,差不多就是宝总最后一战的时候,我们的酒吧在法华镇路银星假日酒店斜对面开业。股东两个,不包括我。一个就是这朋友,出资十来万吧,一个是他当时的领导,正好在法华镇路上有一套空置的街面房,折算入股。我呢,一开始只负责帮他们招揽主要在东北角大学区混的上海滩第一批摇滚乐手,天天过来喝酒,也唱唱歌,聚人气。因为主打摇滚,不肯像当年还很少的普通酒吧那样管自己叫bar,必须要叫pub,好像就高大上一档。但是装修到最后阶段,却发现有一万块钱的资金缺口,问我有伐。我哪儿会有,我当时就是个月薪不到500的大学“青椒”,而且正下岗,500还要腰斩。但是朋友的燃眉之急不能不帮,就让当时的女友(她的绰号就叫“摇滚妞”),问她舅舅(还是叔叔或姨夫?)借了一万块。就此不管别人怎么想,我自认算是这家pub的小股东了。
虽然我们天天玩得很嗨,但无论摇滚还是酒吧,对当时的上海都太超前了,那时候最火的的确是乍浦路黄河路,我们不可能拗得过。也只在想象中他们是对立面,人家根本看都看不到你。所以不到一年,就坚持不下去了。散伙的时候,没人记得要还我借的那一万,别人打水漂了十几二十万,我当然也开不了口。但是女朋友借来的钱必须得还,不得不辞职去了媒体。报社的工资,1000元打底,多写点稿的话1500~2000元,跟三资企业比差点,但是比当老师翻几倍。从进报社的第一天,我就开始省吃俭用存钱,一年刚好存够一万块,还清了债头,也从此落下绝不轻易请人吃饭的病根。
这件事,既然没再想过要朋友还钱,也就烂在肚子里,30年没讲,也算是一种“不响”。但是他们请我吃几百顿饭,小市民都永远心安理得。
三
还有另外一万块。那是我离股市最近的时候。
父母在我高考完毕顺利混进大学之后,放心地出国去做访问学者了。几年后,我偶然从他们的抽屉里,翻出来十张电真空原始股——对,就是帮助阿宝变宝总的那只股票。我发现这十张面值100块的纸头时,它已经从每股2500元以上的高位跌落,但还是长期在800~1200元之间波动,仅次于豫园股份,一直霸占着老二的位置,算下来,十股差不多也是一万块。
到强总发力沪市的时候,我最要好的高中同学,也进了某个大机构,做起了操盘手。他撺掇我在他们那里开个户头,把股票交给他操作,我想也没想就同意了,因为当时我已经进了报社,每天忙得像条狗,每时每刻都在找选题,根本没心思自己炒股。而且摇滚青年已经决定站到黄河路对立面了,怎么可以跟阿宝这种人操持一样的营生呢?
无论如何,我也算是个有股票户头的人了,而且那时候机构的确牛,在熟练的操作和后来一系列配股、送股之下,老同学常常打电话来告诉我又涨了多少,那个我从未见过的户头里据说有了越来越多的钱,估计最多的时候得有个十几二十万吧。
然后,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股市狂跌,楼市腰斩。有一天接到他电话,听他在那头吞吞吐吐,我马上知道发生了什么,干脆地回了一句,就把电话挂了。我说:我不想知道亏了多少,今后也不需要再跟我说,侬只要等将来有一天账户翻回十倍以上了,告诉我一声,就好了。
当然,从此以后我再也没听到过关于这个户头的任何消息。
四
从一开始立项,到预告片流出质疑之声四起,我始终坚持,这片墨镜来导,必成。两个理由。第一个很简单,三流文学作品最适合拿来给好导演改编成一流影视作品,比如王朔纯粹煽情的《永失我爱》和差强人意的《过把瘾就死》,就让赵宝刚捏合成了经典的《过把瘾》;麦家挪用了很多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写出来的堪堪及格的《暗算》,被柳云龙升华成了谍战剧的标杆之作。金老师的小说《繁花》呢,恕我忍不住直言一句,虽然已成现象级的符号,本质上也还是三流,“墨镜”的发挥空间足够。
第二个理由复杂一点。剧版《繁花》里的黄河路其实是架空的,追究它是不是90年代的真实样貌毫无意义,因为90年代的黄河路本身也是架空的,是突兀地出现在这座城市半空的流光溢彩的极乐世界;就像我们开的那家失败的摇滚酒吧,也是架空的,跟这座城市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没有半毛钱关系。
但吊诡的是,历史无数次告诉我们,虽然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某段历史中流淌的某种独属于那个时代的气息,基本上与人民群众现实的日常生活无关——他们在任何朝代都过着相似的将将能够活下去的生活。这种独特的时代气息反而取决于每个时代所能够想象到的最虚无缥缈的东西。
表妹问,为什么他们不请潘虹来演个角色。我说,潘虹一出现,就不是《繁花》,而是《股疯》了。我可以在与我截然不同的阿宝身上看到某种镜像,感受到某种共通的呼吸,但绝对无法对《股疯》里的潘虹有一丝一毫的认同,尽管她也粗糙生猛,甚至粗糙生猛得彻心彻肺贴身贴肉,就像弄堂里贴隔壁的阿嫂一样,每天不仅要碰到她看到她,还要听到她闻到她,但是正因为太“贴”了,太没有距离感了,太现实主义了,就没了“精神气质”的空间,纯然肉身化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是要借着某种距离和空间,才能鲜活地穿堂而过、扑面而来的。这正是墨镜最擅长的。
我最喜欢的“墨镜”作品,并不是《旺角卡门》《重庆森林》这种把香港元素玩得滴溜转的片儿,而是《东邪西毒》和《春光乍泄》。前者套了个武侠壳,后者索性跑去阿根廷拍,都是他作品里香港元素最少的,但恰恰是它们对现实香港的架空,让90年代的香港气质在银幕上元气淋漓横行无阻。
说“墨镜”拍的商战儿戏,有的感情线简直像古偶,都没错,但这就是墨镜的拍法啊。《东邪西毒》里的武打不儿戏吗?套拍和监制的《东成西就》就更不用说了。《春光乍泄》其实也并没有一味在描绘真实的同性恋关系上用力,更多还是套了男同壳的陌路人的无奈和碎碎念。
因为墨镜真正在乎的,从来就只是那阵倏忽而过的时代穿堂风,ashes of time。
《繁花》拍的也就根本不是90年代的上海,而是ashes of Shanghai 90'。
五
我是拿把火钳,在那堆好像已经冷却,又好像随时可能复燃的灰烬里拨弄半天,捞出这八个字:粗糙生猛不计后果。
《繁花》的主角们,貌似都在过各种成功的生活,挫折是暂时的,是为了更大的成功。或至少曾经很成功过。成功是种种感叹或哀伤的背景板。
我和我周围大部分人呢,差不多就是在过一种不断失败的生活。但起码我自己失败得越来越心安理得,并且一点也不影响我再去没心没肺地投入下一次失败。因为其实无论我们的成功还是失败底下,都还是那种属于1990年代的粗糙生猛不计后果——管他成功失败,有爽到,够刺激,就行。
哦,还忘了说一句,粗糙生猛不计后果的,不光是生意或工作,当然也包括感情,这个,就像剧版《繁花》里的宝总、魏总、强总们,诱惑是有的,“革命友谊”是有的,念念不忘也是有的,但细腻温存什么的,真是千方百计也没学会,也学不会了。
六
海明威写《太阳照常升起》,喧嚣的斗牛狂欢、剪不断理还乱的男女情事都只是脚手架,真正重要的,唯有繁华散尽的最后一章,开头是这样的:
早晨,一切都过去了。节日活动已经结束。九点左右我醒过来,洗了澡,穿上衣服,走下楼去。广场空荡荡的,街头没有一个行人。有几个孩子在广场上捡焰火杆……我喝了一杯咖啡,一会儿比尔来了。我看他穿过广场走过来。他在桌边坐下,叫了一杯咖啡。“好了,”他说,“都结束了。”
最后则是:
“唉,杰克,”勃莱特说,“我们要能在一起该多好。”
前面,有个穿卡其制服的骑警在指挥交通。他举起警棍。车子突然慢下来,使勃莱特紧偎在我身上。
“是啊,”我说,“这么想想不也很好吗?”
你有没有从中看到阿宝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