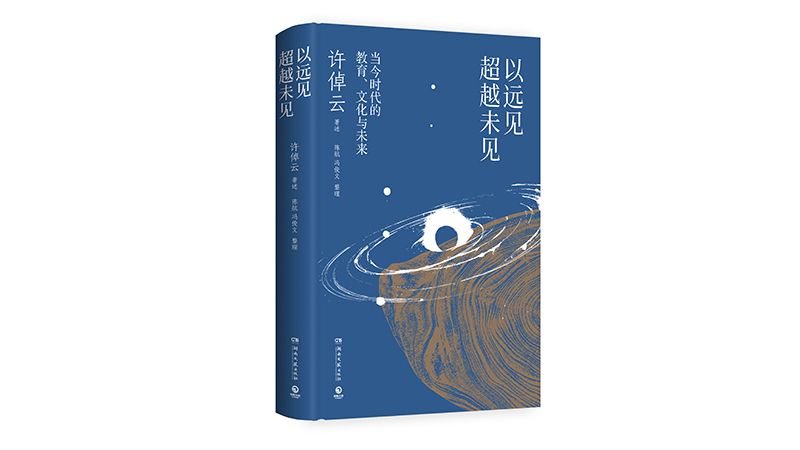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aisd}}
AI生成 免责声明
8月4日,当代华语世界最具影响力之一的史学大家许倬云在美国匹兹堡去世,享年95岁。
作为侨居海外多年的历史学家,许倬云笔耕终生,有《西周史》《万古江河》《中国文化的精神》等几十种著作,90岁以后还出版了新书《许倬云说美国:一个不断变化的西方文明》《许倬云十日谈:当今世界的格局与人类未来》和《经纬华夏》。他心态也非常年轻,关注AI技术最新进展,拥抱新媒体,参加《十三邀》等网络访谈节目,通过短视频平台做直播讲座。
与公众的互动中,许倬云身上散发的浓郁故国情怀,也感染了很多人。《十三邀》主持人许知远曾问许倬云,这一生最重要的遗憾是什么,他停顿了几秒后叹息,“但悲不见九州同啊”,接着又含泪说,“‘中国’两个字,刻在我心里的,七八百万的兵员在阵地上死掉,三四千万的人被杀,被轰炸,不能忘,忘不掉”。
许倬云最后一次公开直播是6月23日,内容是《许倬云回答年轻的朋友们》。他最后一条微博停留在7月24日,回忆川军开拔台儿庄前的几个片段,“长大后我才晓得,当年川军派出一个师直奔前线,在台儿庄全阵亡,从师长到士兵,一个不留”。
对于身后事,许倬云生前多次表示,虽然明知死后无灵,但他宁可相信父母真在无锡老家,早就在父母坟边买好墓地,碑都刻好了。现在,这位史学大家终于回到自己所说的“真正的归属”,“历史上的永远不停的中国”了。

提到打仗就哭得稀里糊涂
许倬云在美国生活了60多年,2019年接受《十三邀》节目第一次访谈时,说到抗战落泪,一下打动了国内很多年轻读者。
在节目的开头,许知远这样介绍许倬云,“是生活在中西两个文明系统之间的人物,他既沐浴着中国旧文化的夕阳,同时又接受了西方现代知识系统的训练,这种中西之间的学习与生活经验,赋予了他治学的最大特色”。
听了这样的介绍,很多观众会以为这是一期再普通不过的学术大家访谈。没想到这样一位海内外闻名的史学家,对着镜头回忆抗战时在湖北逃难途中,亲眼看到走不动的老年人如何把生存机会让给年轻人,由此感受到“中国一定不会亡国”的精神时,哭得像个小孩子一样伤心。妻子孙曼丽见状,连忙来替他擦眼泪,“一提到打仗他就会哭得稀里糊涂”。节目播出后,无数人被许倬云的赤子之心感动,这期访谈也成为《十三邀》的经典作品之一。
确实如孙曼丽所说,抗战最容易牵扯这位治学严谨的史学家的情绪。bilibili网站上有《许倬云讲世界历史》的视频节目,93岁的许倬云讲到近代日本崛起与晚清落后的历史,也是多次连连长叹“惭愧惭愧惭愧”,或者声音颤抖着说,“难过啊各位!”
“抗战期间的经历影响我一辈子”,许倬云多次在书中这样写道。1930年,他出生在无锡的一个书香大族。先祖许松佶在清代做过布政使,父亲许凤藻从江南水师学堂毕业后参与了辛亥革命。许倬云的大姐许留芬毕业于清华大学,她的孙子是歌手王力宏。二姐许婉清的儿子李建复是歌曲《龙的传人》的原唱。许倬云和双胞胎弟弟在家里排行老七、老八,不幸的是他患有先天性肌肉萎缩,一生下来手脚就是弯的,8岁以前没法站起来走路,活动范围最多只能到家门口,唯一的娱乐就是坐在竹筒做的凳子上,手拉着竹筒半寸半寸地跳。
许倬云7岁那年抗战爆发。父亲当时是一个战地军官,被调往离前线很近的地方负责供应军粮民食。每隔一段时间,母亲就要带着大小十余口人奔波,前线吃紧时撤退到后方,等到日本人撤离后再前往父亲的任所团聚。《许倬云问学记》中,记录了“七七事变”后不久他在湖北沙市看到的一幕。
一天早晨,家人带他到大门口,说要送刚到的军队出征上前线。家人忙忙碌碌煮开水,一桶一桶送到门外,许倬云扶着竹凳子站在门边台阶上一望,一排排军人坐在路上一眼望不到边,步枪像小山似的一堆堆架在路边。从早到晚,一批批战士步下码头,登轮往江下驶去。
“这些人是真的出征了,不是调防。”父亲告诉许倬云。母亲一听就念起佛号:“阿弥陀佛,不知道这些人有多少还能够回来。”年幼的许倬云一下就记住了母亲那句话,感觉自己开始懂得生死,原本无忧无虑的童年一下也被切开了,“当时我不过才八九岁,知道他们要去打‘国仗’,所以小孩变大人不是年纪,而是心境”。
抗战逃难中真正懂得农民
拖着残疾之身与家人一起逃难的8年,许倬云无数次在大轰炸中幸运死里逃生,无数次看到死亡在身边突然降临,“死的人没有任何罪,只因为他们是中国人”。有近7年的颠沛流离都是在农村度过,条件虽然艰难,但他感受到唯一的暖光——去农民家借宿时,他们总是受到无私照顾,村民们把少得可怜的粮食拿出来大家一起吃,许倬云对农民充满感情。
因为身体没法随便行动,他常常被摆在一个小土墩、石磨上,于是就搬个小板凳看农民劳作,时间久了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农夫种田,老农夫妻聊天,小孩子在地里抓虫子……多年后,这些场景还在他的著作中不时闪现。
许倬云没法像哥哥姐姐们一样上学,就在家看父亲的书。许凤藻虽是武官,却酷爱文史,家里有很多藏书和报纸。许倬云看武侠小说,看《史记》《左传》《饮冰室文集》,也看时事报刊《大公报》《时与潮》。许凤藻每天还要看战报,或从无线电里听大西洋战争的情形,然后拿出地图告诉许倬云,大西洋的海战在哪里发生,双方战况如何等,让他从中学到很多地理知识。
这段特殊的学习时光直接影响了日后许倬云对历史的喜爱。“父亲给我的这套教育和别人不太一样,他给我的教育就像英国式的全科教育,他教我做一个懂得历史的人,教我战争史、地理、政治学、外交、文辞等。”

1945年抗战胜利后,许倬云回到无锡老家,第一次踏进学校大门,进入无锡辅仁中学读高一。1953年,他从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开始从事历史研究。抗战期间在大陆的颠沛流离经历,深深影响了许倬云此后的历史研究视角及方向,“兴趣最大的是老百姓的事”。多年后,他用英文写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两部名著,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起点。
经济学家张维迎曾对第一财经回忆道,许倬云自豪地告诉他,之所以写《汉代农业》,是因为自己真正了解中国农业。在中国历代王朝中,许倬云认为汉代农民生活得最好,他在《十三邀》访谈里还说:“汉朝将国家的基础放在农村里边独立的农家,人才才能出,财富才能出,这是交通线的末梢。城市都是交通线上打的结,商人、官员都在转接点上。”
许倬云稍后完成的代表作《西周史》也独辟蹊径,没用专门章节来讲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周朝历史上著名的帝王,为此还受到过批评。但他认为,自己治史的着重点是社会史与文化史,注意“一般人的生活及一般人的想法”,何况“已有太多自命英雄的人物,为一般小民百姓添了无数痛苦,我对伟大的人物已不再有敬意与幻想”。
许倬云的历史研究,最后落脚点总是普通老百姓。在《中国文化的精神》中,他不止一次提到“常民”,所谓“常民”,就是老百姓,他们不见于史书记载,自然隐入尘烟。但许倬云认为,正是常民创造的民间传统文化精神,留存了宝贵的价值,他试图由此切入,重新反思和反观中国文化,为中国避免患上西方那样的现代文明病提供一剂药方。他总结自己是“关注常民”“为常民写作”。
对王小波影响最大的老师
1970年,中国台湾地区政治危机四伏,知识分子成为国民党当局的打击对象。此时,许倬云恰好接到去美国匹兹堡大学做客座教授的邀请,台湾大学的师长都劝他“去了不要回来”,许倬云开始在异国侨居。
许倬云在匹大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有一段特别的经历,就是做过作家王小波的老师。1984年,王小波的妻子、社会学家李银河到匹兹堡大学读博士,许倬云是她的导师小组成员之一。当时匹大东亚语文学系主要教外国小孩学中文,完全没有值得王小波修习的课程,王小波就挂在许倬云名下注册上课,整个课程只有他一个学生。
“小波的学习兴趣本不在史学,也不在社会学,于是我们的对谈无所设限,任其所之。”许倬云在文章中回忆,“我们讨论也不完全有教材,即使指定了阅读资料,一谈就跳到别的题目,又派他一些其他资料研读。总之,这是一堂相当自由的讨论课。小波的朋友大约都知道,他坐姿松松散散,我也一直有坐不直的毛病,师生二人东倒西歪,倒也自由自在。”
许倬云评价王小波,“不在我的专业领域之内,却是一位情深义重、好奇心切、求知若渴、领悟力强的青年人”。他还告诉当时在国内文坛上尚未大放异彩的王小波,“文字是矿砂,是铁坯,是绸料,是利剑,全看有没有炼字的淬炼功夫”。
“我印象里当时小波应该是在写《唐人故事》,其中有一篇他给许先生看了,许先生的建议对小波是有影响的。”2020年许倬云九十寿辰前夕,李银河接受过第一财经邮件采访,回忆了夫妻俩与许倬云的交往。她对许倬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文笔特别好,写的东西跟一般学者,尤其跟国内很多学者不一样,“所以许先生给小波提的建议,小波非常重视”。
1991年,许倬云看了王小波的中篇小说《黄金时代》后,推荐给台北《联合报》,后来小说在副刊上连载,并获得第13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在获奖感言里,王小波专门感谢了老师许倬云。
“小波文章里提到‘我的老师’时,都是指许先生。他是非常清高的人,一般的人不会留下很深印象,就不会称为老师,但许先生是他最推崇的那位。”李银河说,那时他们上课实际就是聊天,聊古今中外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小波看的书可杂了,特别多,不光是看正史,也看野史,所以才写《红拂夜奔》那些唐人的奇闻逸事。这两位碰到一起,你说得撞出多少火花?”
李银河说,当时许倬云已是名声斐然的历史家,王小波的历史研究是业余的,那些精神上的交流,对小波后来的文学创作显然有影响。许倬云同时也影响了李银河,“除了自己那点学问之外,还要关注社会。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会忍不住出来说一句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知识分子要做社会的‘看门狗’”。
直到生命尽头仍是个乐观主义者
越是走向人生终点,许倬云身上越是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对故国的关切也更深。
2019年,许倬云接受《十三邀》访谈时,还能拄着拐杖在家里走走。那时他89岁,前一年,许倬云有感“来日不多”,想在没有“昏聩糊涂”前再写一本书。他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的争议和撕裂,于是写下《许倬云说美国》,谈他目睹的美国60多年的风云变幻,希望美国历史能对中国社会有所启发,因为“全世界人类曾走过的路,都算我走过的路”。
跨过鲐背之年,许倬云的身体状况更差了,下身瘫痪导致他的骨头和肌肉融合,医院帮忙在他家设置了一个看病房,有个电动吊兜,把他从轮椅升到床上、从床上提回到轮椅,上下床全靠机器帮忙。“在这种情况下,我与各位共同努力的时间不会太长久了”,许倬云在2023年出版的最后一本书《许倬云十日谈:当今世界的格局与人类未来》中说。
《许倬云十日谈》的写作缘起,是全球爆发的新冠疫情让许倬云感受到人类历史走向一个重要关口,特朗普的执政让美国政治和社会持续出现各种混乱,他也感受到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使得科技与人的关系有了变化,觉察到人心中普遍存在恐慌后,许倬云有话要说。中世纪意大利作家薄伽丘以大瘟疫为背景创作了《十日谈》,于是他也借用这个名字为题,在新冠疫情期间和中国企业界精英做了十次谈话。
对谈的最后,许倬云照旧又从世界谈到中国:“在全世界惊慌失措的局面之下,如果我们将世界问题和中国问题合在一起看,中国能不能在世界混乱之中独善其身呢?中国能不能更进一步,想想如何帮助世界其他民众,大家共同缔造一个真正和平大同的社会?”
这些年来,许倬云还频频和他曾经写的“常民”,现在叫他“许爷爷”的网友互动。他们也愿意告诉许倬云各种人生困惑。他在B站开课《许倬云讲世界历史:五百年大变局》,坐在匹兹堡家中客厅的桌子前,说自己对B站网友的态度,就像对自己的孙子奥利弗,“等于我眼前看见有一大堆奥利弗坐在那里,安静地听我谈话,我的责任就是在下面若干小时里拿我一个老人的经验、老人的观察、老人思虑的方向分享”。
他也十分了解当下年轻人面临的困境,“所以我这几年的功夫最大的中心点,是放在告诉他们利害之外、金钱之外还有什么”,“面对惊涛骇浪,第一,不能慌张;第二,不能放弃”,“自己的知识情感都不要歪曲”,“同志相求,同声相应,找到互相砥砺、互相切磋终生的朋友,就一辈子交下去”。
尽管一生历经战乱、各种政治动荡,最后终老异国,但直到生命尽头,许倬云依然是个乐观主义者。他勉励年轻人,心里的良心是天下最宝贵的东西,“由你这个良心,引起别人的良心,许多良心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四分之一的人口撑得起半个天”。
如需获得授权请联系第一财经版权部:banquan@yica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