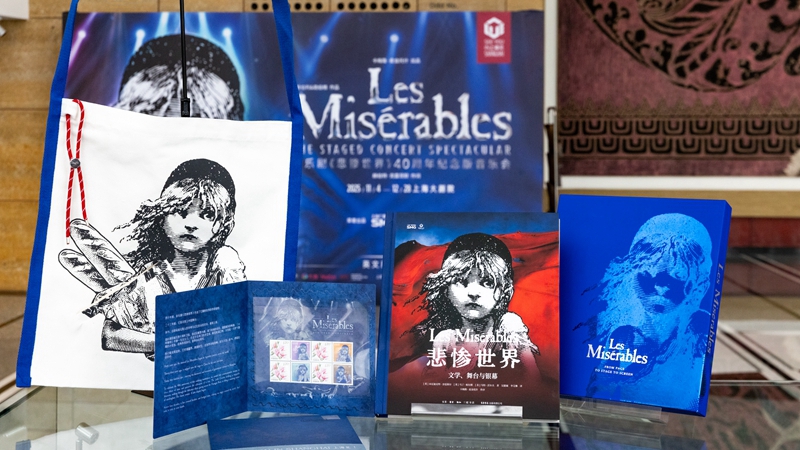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aisd}}
AI生成 免责声明
一个对戏剧几乎一无所知的家庭主妇,也能演《麦克白》吗?在话剧《杂物间里的麦克白》里,43岁的中年女人“王淑芸”完成得十分精彩,她的演绎令这个角色生出了另一种光彩。
第12届乌镇戏剧节期间,《杂物间里的麦克白》连演三场,一票难求。演出场地秀水廊剧院为此开放二楼站票,有观众甚至提前五六个小时来排队。这部剧由林溪儿担任编剧、导演,谢承颖、丁辰西主演,今年早些时候演出积累的良好口碑,使其成为本届戏剧节热门剧目之一。

2023年,林溪儿编剧、导演、出演的独角戏《我和刘红梅在车站》获得第十届乌镇戏剧节青年竞演单元特别关注奖。“我的野心很大,路还很长”,当时她便决定未来以特邀剧目主创身份重返乌镇。两年后,她得偿所愿。
《杂物间里的麦克白》讲述的是29岁的戏剧导演“我”和43岁的素人演员王淑芸,因为排演独角戏《麦克白》短暂交汇,彼此看见,又各自前行的故事。有观众认为,它散发着一种温暖蓬松的“妈妈的感觉”。林溪儿说,她希望自己的作品是柔软而舒适的,“不剧烈、不刺激,给人带来一些细小的触动”。
乌镇戏剧节期间,林溪儿接受第一财经专访,分享了作为新导演一路走来的历程,以及她对戏剧创作和市场的思考。
成为“麦克白”
在大多数版本的《麦克白》中,麦克白弑君篡位,是欲望的象征,林溪儿却能共情他的不甘心。“他爵位很高,有封地、城堡、军队和爱人。他想当国王并非为了某个明确的目的,不为金银珠宝,也不为出兵远征;他想当国王的野心,于我而言很纯粹。”林溪儿说,那种“凭什么不能是我”的不甘心,让她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
在《杂物间里的麦克白》中,这份不甘心在“我”和王淑芸身上暗自生长——“我”不甘心从此远离剧场,王淑云不甘心被家庭所困。她们渴望被看见,渴望改变,渴望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尽管前路困难重重。
在林溪儿看来,“不甘心”是欲望之前的状态,“当你有欲望的时候,就有了欲望的对象,在对象尚未明确之前,那种心情就是不甘”。43岁的王淑芸为了育儿离开职场七年,在漫长的生活中,她将自己的不甘揉碎。她意识到生活的不如意,但并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那种不甘是模糊的,但的确存在”。

在杂物间里,她们开始一整个夏天的排练,彼此交谈,关于创作,也关于生活。“我”向王淑芸施展戏剧的魔法,令她在不知不觉中爱上表演;王淑芸以她的温暖,拥抱处于低潮中的“我”。最后,在这方狭小的杂物间里,属于她们的《麦克白》诞生了。
最后的戏中戏大约20分钟,杂物间是王淑芸的舞台,“我”是她唯一的观众。篝火摇曳,镜面反射出白光,烟雾升腾,芦苇变成森林,欲望和勇气在她的身上逐渐显影,在成为麦克白的过程中,王淑芸完全释放了自己。
林溪儿说,设计戏中戏的目的并非重述故事本身,而在于让观众看见王淑芸的另一面,不同于生活中有些胆怯、退缩的模样,她的身上藏着惊人的爆发力和强烈的生命力。“她的人生不会因此发生剧变,也不会突然找到了意义。在夏天的某个傍晚,她做到了一件无人在意的事情,她将自己的力量全部释放,去嘶吼、去对峙、去叩问。”
29岁的我们
林溪儿今年29岁,与剧中的导演“我”年龄相同。
29岁通常被视作关键节点。这个年龄的人似乎应当有所作为,完成多项阶段性任务,以确保走在“正常”轨道之上。因此,一旦目标未如期达成,便不可避免地陷入焦虑。“我”就这样被社会时钟逼至悬崖,需要在是否继续从事戏剧和找一份稳定工作之间做出抉择。
林溪儿的“29岁”是在二十七八岁那段时间度过的,焦虑提早到来。当时的她好不容易重返戏剧领域,手里的两部作品却反响平平,她形容那段时间的自己,“超级螺旋爆炸焦虑”。“所有问题涌向了我,我该如何走下去。银行卡里就那么点钱,我真的能在社会上生存吗?这个年龄不应该是成熟的大人了吗?我却什么都还没有做出来”。她甚至通过打游戏来逃避现实,“而回到现实的时候,就像是突然掉进了时空的裂隙,那是一种更难以忍受的空无和茫然”。
支撑她熬过那段时间的是父母无条件的支持,他们总是不断告诉她,她的创作是可贵的,“他们真的会来剧场看我的戏,觉得我超棒,无论如何都为我骄傲”。那段时间,林溪儿也曾考虑去做点戏剧之外的事情或做些更商业的项目,又担心思维与审美被磨损,“创作能力像水源一样,它是有限的,有一天可能会季节性地干涸,如果它被污染了,也很难再被复原。我很想保护它”。
2023年,乌镇戏剧节青年竞演成了林溪儿当时唯一能够抓住的机会,去证明自己走的这条路是可行的。《我和刘红梅在车站》凭借真挚情感和精巧构思打动了许多观众,也让很多人看见了她的才华和灵气。“那时的我有想法,有构思,有创作欲,只是没有展现的机会。也确实在那部作品之后,我得到了一些关注,一步步往前走。”
如今,林溪儿进入了新的创作阶段,一切似在平稳中发展,但她会不时反思行业中的种种不合理。《杂物间里的麦克白》中“我”的处境,是她和身边所有热爱戏剧、想要在戏剧领域有所作为的新人导演会面临的处境:就业狭窄,缺乏通道,机会太少。
“绝大多数行业,大家默认你大学刚毕业,技术不成熟,得在行业里面摸爬滚打几年之后,才有可能成为专业领域的佼佼者。我们的行业有点像是,毕业就得是天才,创造出爆款才能往下走,在没有任何实践之前,就得成为拔尖的那个,否则就没有走下去的机会。理论上讲,它很不科学。”和剧中人一样,她也想做点儿什么,改变那些“一直如此”的事情。
让戏剧从高阁走向观众
《我和刘红梅在车站》或是《杂物间里的麦克白》都不是难以理解的戏剧作品,它们距离观众的日常很近,有时就像是生活本身,细腻柔软。
“我们一直在说戏剧市场很小,要如何将它做大。”林溪儿思考的解法之一是降低作品的观演门槛:“做那种爸爸妈妈走进剧场也能看得明白,且觉得好看的戏。那么偶然走进剧场的人也许会喜欢,觉得这种艺术形式没有那么难以接受。如果票价相对便宜的话,下次再去看看,说不定哪天看到特别喜欢的作品,未来看戏就像看电影一样成为生活习惯,一年进剧场三四回,那也是很了不得的事情了。”
她乐观地认为,新导演之困并非全然没有解决方法。她希望未来可以拥有一间自己的剧场,“像‘黑匣子’那样小小的就足够”。
这个剧场在工作日对公众开放,票价约等于一杯奶茶,“年轻导演每个人拿出20到30分钟的片段,几个片段拼在一起做一个小小的展演,每周都演”。
在林溪儿的设想中,如果某个片段在观众当中反响很好,就有资源和机会将之发展成成熟作品,“听上去是不是可行”,她笑着说。它的形式有点像青年竞演的日常化,或是脱口秀开放麦,它可以试错,也鼓励奇思妙想,创作者不必被竞赛逻辑所裹挟,比拼哪个片段更“炸裂”,“它是一个长期的平台,大家能够做一些忠于自我的创作,而观众可以用很低的价格来看最新鲜、最野生的创作者。这里一定会有好东西”。
如需获得授权请联系第一财经版权部:banquan@yica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