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aisd}}
AI生成 免责声明
1
如今越来越多人感觉到,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推动改变的核心是技术。只不过,这改变是福是祸?答案尚未清晰。在一种普遍的迷惘情绪中,把握现实、描写当下变得特别困难。于是很多人(比如我)开始阅读科幻小说,因为那些预言,尤其是以技术为中心的写作,已经变得非常现实了。
去年引进出版的小说《归零》,描写的是科技巨头赛·巴克斯特——他的形象让人想到比尔 ·盖茨、扎克伯格、马斯克等著名宅男,智商很高,却不擅长与人交往,他们相信技术可以解决一切,全世界都是他们的游戏场。故事讲的是,赛·巴克斯特开发了一个监控软件“融合”,可以利用摄像头和大数据,轻易追踪任何人,为了把这套系统卖给美国中央情报局, 巴克斯特设计了“归零”测试,招募十个人,两小时内相继“消失”,如果有人逃亡了一个月, 还没被“融合”抓住,就可以获得300万美元奖金。
这十个人里,有安全专家,也有退役军人、富豪......但逃得最久的,是一个女图书管理员,她平时喜欢看侦探小说,逃亡时带着《安娜·卡列尼娜》。初看起来,这似乎是在求助于印刷时代的智慧,求助于20世纪的革命激情来对抗技术寡头的控制,可惜到了中段,小说突然垮掉,回归了私情复仇。

《归零》
【新西兰】安东尼·麦卡滕 著 陈恬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5年8月
这种垮掉,使得小说对技术监控的反思也变得含混起来,这也许是出于商业考虑——作者原本是电影编剧,小说写得很有画面感,情节也引人入胜,影视的改编企图很明显,因此,这样的故事不能太尖锐、太困难,也不能太绝望。因为看起来,对于这样的发展趋势,人们已是无能为力了。
有趣的是,在几位中国年轻女作家的科幻小说里,我也看到了关于监控系统的想象性描写。不过,她们的看法更加暧昧。在这些作品里,监控系统似乎是一个强大到无孔不入、无法反抗、只能接受的秩序,不仅如此,有时还颇为正面。在小说《蚁群》中,作者想象了一个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女性主导的社会,而这个安全、美好的社会就建立在严格的监控系统之上。这背后的意味,实在令人玩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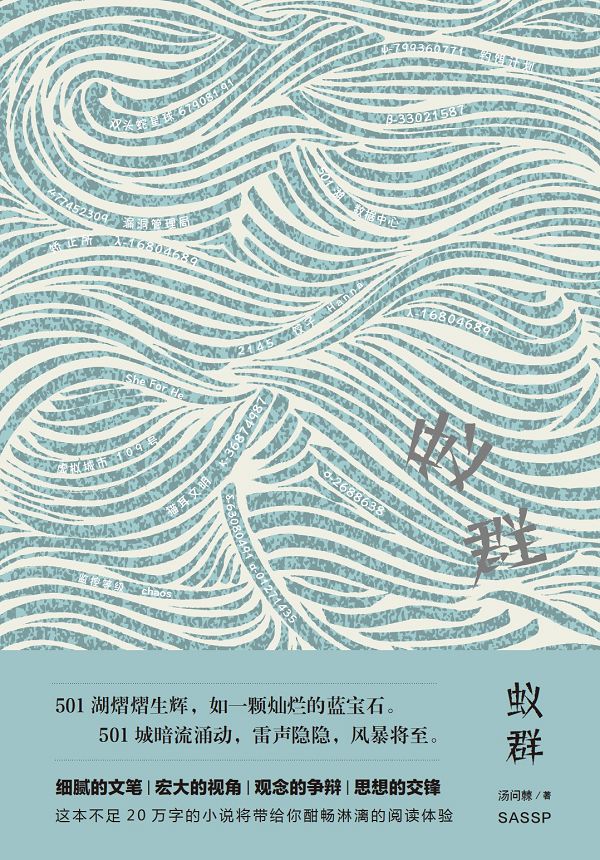
《蚁群》
汤问棘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1年11月
在《归零》中,故事的关键转折点在于,赛·巴克斯特的妻子、公司的另一位创始人撞见他出轨,夫妻感情的变化,导致权力出现了裂隙。这很难不让人想到盖茨夫妻的故事,据说,梅琳达·盖茨提出离婚的原因之一,就是无法忍受比尔·盖茨的婚外情,包括他与爱泼斯坦的私人来往。
《归零》的作者安东尼·麦卡滕在另一本书《沃伦·巴菲特与比尔·盖茨:改变世界的友谊》中提及了这一点。2000年,比尔·盖茨辞去微软首席执行官,将主要精力投入他和妻子共同创立的盖茨基金会。但是夫妻二人除了私人生活,在基金会的运作上也有分歧,梅琳达倾向于直接帮助弱势者,尤其是解决与女性相关的问题,盖茨则希望用技术来解决全球危机,包括饥饿、疾病、气候等,为此他还提出一个概念,“创新资本主义”。只不过,从书中的一些案例来看,这种技术思维常常无视当地的实际情况,从而引发新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是这也是许多人对盖茨基金会的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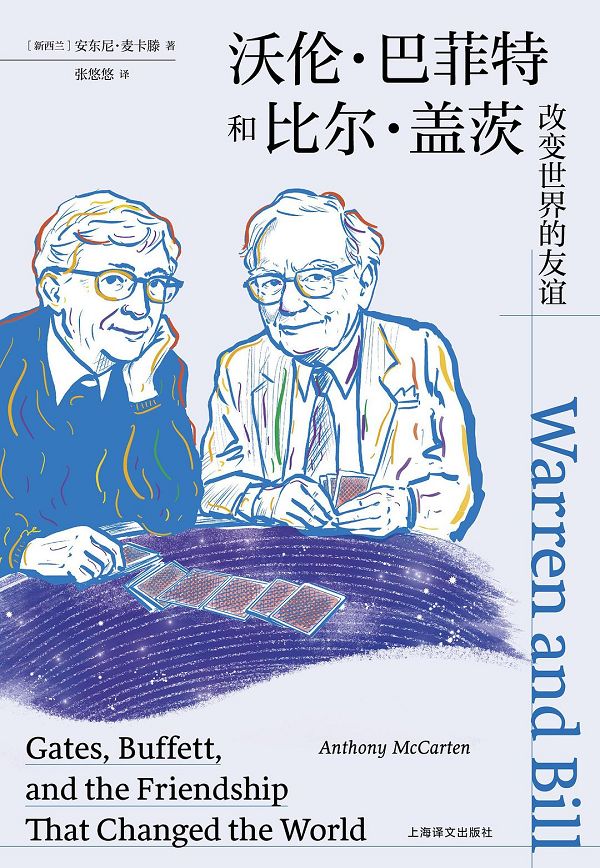
《沃伦·巴菲特与比尔·盖茨:改变世界的友谊》
【新西兰】安东尼·麦卡滕 著 张悠悠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6年1月
并非所有问题都是技术问题,技术也并不能决定一切,人类社会终究由“人”组成,有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综合作用。在技术至上、技术乐观主义的时代,这些常识似乎都被忘记了。
在这本书里,作者提到自己的写作动机:亿万富翁拥有巨额财富,对世界有如此大的影响,我们却对他们所知甚少。他引用了2017年乐施会的数据,八个顶尖富豪拥有世界上一半的财富。八个男人,而不是八十、八百个,他强调说。而且,随着新一轮的技术革命, 他们的财富只会越来越多,“这个世界是怎么变成这样的?现状真的公平吗?维持得下去吗?......在这个失衡的世界里,我们真的安全吗?还是说我们正走向最后的大清算?”没 错,这正是需要提出的问题。
2
互联网已然重塑了人类的社会结构,比如“平台经济”,如今人们已经很难想象一种没有快递和外卖的生活了,但是,也许最深刻的改变不是来自外部,而是人的内心。
西班牙精神分析师玛蒂娜·伯德特(Martina Berdet)在《赛博格时代的爱情面孔》中描述了人的这一变化。她从一个相亲故事讲起:安娜在网站上遇到一个男性,他自称住在比弗利山庄——这意味着他是个大人物,他看起来善良、有礼貌,唯一的问题是,他和安娜相隔一万公里,说着不同的语言。安娜说,她不想谈远距离恋爱,她想找一个随时可以见面的人,一起喝咖啡、看电影、聊天。但是他许诺说,自己很快就会来到她的身边。起初, 安娜很难相信,二十分钟前,他们还不认识,二十分钟后,他就非常确定地表达爱情,向安娜描绘他们的幸福未来。这合理吗?如此优秀的男性,从未谋面,只是凭借电话里的声音和照片,就能编织出爱情?每当安娜开始动摇,他就打来电话,表明自己的决心和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很快,安娜陷入了爱情,每天的电话聊天慰藉了孤独,她也开始想象未来的幸福生活。一个礼拜后,电话停止了。安娜非常痛苦,她立刻进入相亲网站,寻找下一个对象,“哀悼某种并不存在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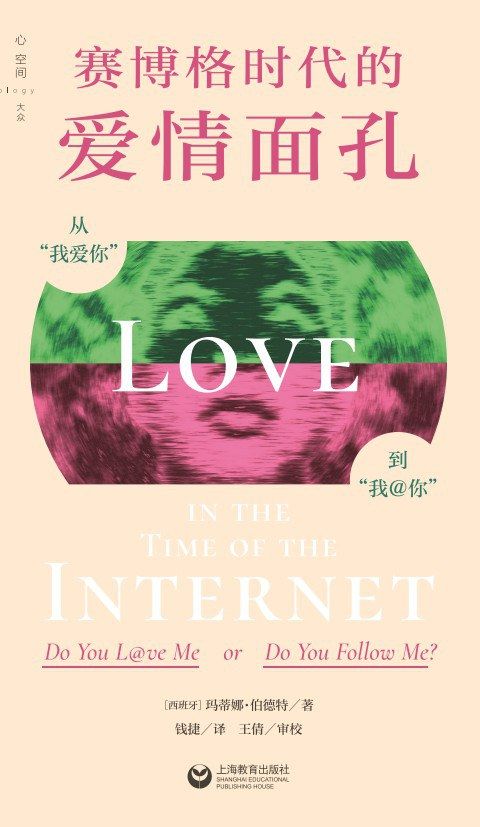
《赛博格时代的爱情面孔》
上海教育出版社/心空间 2024年4月
【西班牙】玛蒂娜·伯德特 著 钱捷 译
作者问道,这位男士究竟是在和谁聊天?他并不了解安娜,似乎也并不想了解,就许下了对于未来的承诺,他许诺的对象,“不是一个被他投射了自身欲望和需要,被他理想化了的女性吗?”作者说,“这就是站在理想化视角的异我(alter ego),浸泡在自恋之中,并对其他所有人的独特性不屑一顾。”
这本书从不同层面展现了互联网革命带来的心灵改变,比如,无限制的享乐、永恒的当下主义、色情制品与性极度泛滥,与之相对应的是,爱消失了,“我们与他人的情感连接变得松弛,与机器或装置的情感纽带则变得更加牢固。”
如今读来,这些句子已经非常可感,它就真切地发生在我们身边,甚至是我们自己内心,这些变化从何而来?作者提供了一个精神分析的角度,她说,人类的爱情模式来源于最初的养育者,幼儿处于极度无助的状态之中,完全依赖于他人的身体,为了活下去,人类爱着帮自己存活的原初客体——通常是母亲(同时,也会在极度受挫的情况下憎恨她们)。这是人最初享乐体验的方式,如果没有完成分离,建立独立的心灵主体,人就会趋向于重复这些体验。
这是一本相当专业的精神分析作品,并不容易阅读,如果予以简单归纳,我们可以说,作者所谓“建立独立的心灵主体”,也就是成长的过程中,挫折、痛苦是不可避免的,每个婴幼儿都会经历几次创伤。作者认为,理想的状况是,养育者将痛苦控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帮助个体完成独立。但是,理想状态很多时候都不存在,因此个体常常很难完成独立,或者,会遭受超出忍受范围的创伤。
对于这部分个体来说,互联网提供了一个空间,帮助人们逃离创伤,同时,它也延迟了成长,助长了沉溺的快感和自恋的快感,使得“人的嘴里可以始终含着乳房而没有饥饿感,始终回避痛苦、悲伤,追求快乐,实际上,这就等于欲望、幻想和思想的死亡”。在中文里,这种娱乐方式被直接地翻译为“奶头乐”。
对于在互联网上长大的新人类来说,他人消失了,爱情消失了,“我爱我自己,你爱你自己,这就是现在我们相爱的方式”。新的需求是:被他人认可。互联网巨头们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并创造出各类平台来满足、鼓励人们的新需求(《归零》中,赛·巴克斯特就是社交媒体巨头)。于是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亿万个“我”,晒出照片,晒出自己的生活,渴望被看见,被认可,被爱,被点赞。作者评论说:“点赞决定了今天是快乐还是抑郁。”如果不被看见,似乎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问题是,当每个人都是演员、所有人都在争夺目光的时候,被看见的只能是少数,那么,孤独、抑郁就是必然的处境。
在这一轮又一轮对新技术的热情欢呼中,学者戴锦华是少有的一直在发出预警的声音,她为《赛博格时代的爱情面孔》写了序言,其中一段问道:
“如果说网络时代有如此众多的社交和交友软件,林林总总的app,令我们拥有了无穷选择,为什么我们却如此难以建立或确立亲密关系,甚至恐惧、拒绝亲密关系的存在?如果说在网络世界中,我们追逐快乐、快感,所谓‘我的地盘我做主’‘今天你多巴胺了吗’,那么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抑郁症成了患者逐年递增的流行病?自杀率居高不下?”
这同样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3
亿万个“我”都在独白,喧闹的声音震耳欲聋,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女作家托卡尔丘克的《温柔的讲述者》中,也出现了这个主题。
这本书收录了托卡尔丘克的一些散文与讲稿。其中,她不可避免地写到了出版业的危机和文学的危机。这几年,出版业每况愈下,哀鸿遍野,全球同此冷暖,东西方都是如此。常见的分析是,短视频流行,导致阅读人数变少了。
互联网改变的不仅是销量,也改变了出版业与写作者的形态。托卡尔丘克回忆说,从前只要写完一本书,交给编辑,之后就是等待了,等待编辑的意见,等待出版,等待批评,等待读者,甚至寄望于未来的历史书写。但是今天的年轻作家都不愿意推迟成功,一切都要握在自己手里(编辑的角色也越来越不重要了),这意味着对自我形象的包装、营销越来越重要。这一点我们也很熟悉,就是网红化了。
托卡尔丘克说:“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前所未见的进程,我们看到,‘我’这个字眼的质量正在变得越来越重。”

《温柔的讲述者》
【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著 黄珊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 2026年1月
在文学中,“我”的出现,意味着第一人称写作。托卡尔丘克说,第一人称的出现曾经是一个创举,它拉近了跟读者之间的距离,是世界必要的锚,是创造平等的基础,但今天它正在不健康地膨胀,“像不断膨胀的野牵牛,令其他观点和视角无法呼吸”。除此之外,“作者不断膨胀的自我(ego)正在彻底改变文学,也许将会是永远的改变。不排除在不久之后,文学中将只剩下两股主要潮流,眼下它们已经在书展和奖项中占据越来越多的空间 ——‘我会告诉你我曾去过哪里’和‘我会告诉你我的家庭’。”
托卡尔丘克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由“我”的自白出发的非虚构是现在最流行的文体。自白的出发点很容易理解,人们希望被关注,希望感觉到自己与众不同,“然而,矛盾的是,它看起来就像一个独唱者自己组成的合唱团——声音重叠复沓,互相争夺注意力,在相似的轨道上移动,最终淹没了彼此。”
与此相对,小说这种更为复杂、“似是还非、亦真亦假”的文体,逐渐地失去了读者。托卡尔丘克悲观地说,再过两三代,也许文学阅读真的会消失。
4
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读到郁达夫的小说《沉沦》,这篇小说写于1921年,艺术上非常稚嫩,却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它第一次出现了“我”,不仅是人称代词“我”,而且是一个自我形象,有着喷薄而出的内心情感——在日本留学的年轻男性,表达着屈辱的民族情绪和压抑的性欲望。
一百年来,这样的情感主题和自我形象在中国文学中经久不衰。不仅如此,如同托卡尔丘克观察到的一样,如今中国的出版市场最畅销的,也是第一人称讲述的非虚构文体。最初,来自底层、不同职业的自我书写,让我们看到社会的不同层面,这当然是好事,可是渐渐地,变成“独唱者组成的合唱团”,很多独白真的变成了自言自语,只有自己,没有他人,即使有他人,也是某种工具性的存在。看见自己,成为自己,跟自己对话......充斥着书籍、小红书、抖音。
爱情的消失,他人的消失,自我的呓语,都是一样的,最终将导致生命力的枯萎。“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豪语,和孤独无依的萎缩是一体两面。因为人终归是社会动物,无法独立存在。
托卡尔丘克说:“从某个时刻起,我们开始以碎片化的方式看待世界,一切被分割开来。世界正在消亡,而我们浑然不觉。世界正在变成各种事物和事件的集合体,变成一个死寂的空间。我们在其中孤独而迷茫地前行,被别人的决定所左右,被难以理解的命运所奴役,感觉自己是历史或偶然性之巨大力量的玩物。”
对于这样割裂、碎片化的世界,对于亿万个孤独的自我,托卡尔丘克强调关联、影响,一种将人类与自然万物、神灵鬼魂联系在一起的整体观——可是,这不就是东方智慧吗?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如今却很少成为我们的力量来源。会不会从郁达夫的《沉沦》,从“自我”浮现之后,我们已经完成了内在的转变,当我们划开自己的皮肤,发现自己实际上变成了西方人?
让我再次借用中国的传统智慧:物极必反。总有一天,人类走到山穷水尽,会意识到心灵的危机、存在的危机,也许这一天不会太远,我们终究需要寻找意义、寻找连续性和整体性。而故事、文学就是在建立意义、连续性和整体性之上,成为人们心灵的归处。
就像托卡尔丘克所说,我们要讲出“一个新的故事,一个普世的、整体的、非排他性的故事,植根于自然,背景完善,同时又容易理解。超越无法沟通的自我牢笼,揭示更大范围的现实,并显示出关联性。”
也就是俗话所说的: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