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aisd}}
AI生成 免责声明
在北美,“观鸟大年”是一场没有裁判、没有奖金、没有奖牌的极限挑战:参与者需要在一年内,在墨西哥以北的美加大陆及近海,凭借肉眼或望远镜目击并记录尽可能多的野生鸟类。比赛规则极其简单,代价却非常昂贵:机票、租车、船票、向导、晕船药、冻伤膏、咖啡与肾上腺素。
1998年,厄尔尼诺爆发带来了很多极端气候,也造成很多反常的鸟类出现在北美,令整个北美观鸟圈陷入疯狂。这一年,把名字写进历史的,是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新泽西工业承包商、百万富翁科米托;阿斯彭退休高管、化学博士莱万廷;马里兰核电站码农、穷游式观鸟的离异男米勒。平均年龄接近六十岁的他们,不约而同地踏上了这场横跨大陆、飞跃重洋、深入垃圾场与雪山之巅的观鸟竞赛。
从1月1日到12月31日,是什么让他们放下日常生活马不停蹄地去追寻?这一年的经历又会如何改变他们的人生?书的主题虽然是一项略显小众的爱好,却也适合所有读者,因为其内核是人类的共性:为了所爱之事进行探索和追寻,千山万水,无远弗届。
经出版社授权,第一财经节选书中部分篇章,以飨读者。
1998年1月1日
桑迪·科米托(Sandy Komito)
桑迪·科米托准备好了。新年第一天,日出前一小时,他独自坐在亚利桑那州诺加莱斯市一家通宵营业的丹尼连锁餐厅里,点了火腿煎蛋,凝视着窗外的一片漆黑。
他认识的一些同龄男人,有的渴望换个新老婆,有的想着买辆保时捷,甚至游艇。科米托对这些都没兴趣。
他只想观鸟。
未来一年里,他将全身心投入唯一的目标——成为历史上在北美洲范围内看到最多鸟种的人。他明白这并不容易实现。他已经盘算好了,未来的三百六十五天,自己将有二百七十天都不在家,四处奔波着追逐这片大陆上那些长有翅膀的生灵。他要去科罗拉多州的大陆分水岭追踪雷鸟;深入亚利桑那州酷热的沙漠寻觅蜂鸟。他将在明尼苏达州北部森林中的月光下潜行,夜探猫头鹰;在佛罗里达州南部黎明时分的滩涂中跋涉,寻找鲣鸟。他计划用各种交通工具追鸟: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乘船,在阿留申群岛踩单车,在内华达州搭直升机。睡眠?不重要。但要是必须睡,那他应该是在阿拉斯加的军用床上辗转反侧;或者在墨西哥湾干龟群岛翻滚的海浪中颠簸。
毕竟,这是场比赛,而科米托想赢。
他点了第二壶咖啡,把相关文件一份份摆在餐垫上。都是从网上打印的,一张来自休斯敦,是北美罕见种鸟讯;另一张来自亚利桑那州南部的图森市,是地区鸟讯。科米托笑了。上周,亚利桑那东南部观察到的罕见鸟种数量超过了北美大陆上的任何其他地区。
凭直觉,他认为这家连锁餐厅正是个好起点。这些年来,他在太多家丹尼餐厅吃过饭,根本不用费神看菜单。更何况,有其他鸟佬报告说,这家丹尼餐厅周边的树上,栖息着大尾拟八哥和黑头美洲鹫。科米托想好了,这两种当地好鸟,无论看到哪一种,都将为他开启美妙的新一年。

科米托坐在窗边,看地平线逐渐亮起灰蒙蒙的光,黎明即将到来。几乎没什么动静。
不过,就在餐厅对面,一列货运火车突然呼啸而过,硬生生打破了这一片寂静。这喧嚣惊得窗外的什么东西振翅而起,正正好落在他的窗前。
科米托心跳加速:这是他比赛中的第一只鸟!
他往前探探身子,想看清到底是什么鸟。
肥圆——灰色——脑袋上下移动着。
“一只倒霉鸽子。”他嘟囔道。
每年的1月1日都有数百人“抛家舍业”,脱离日常生活,参加世界上顶顶古怪的一场比赛。他们的目标是在一年中看到最多的鸟类物种。大多数参赛者只在自己所在县的范围内观鸟。还有些则局限于自己所在的州。然而,最宏大,也最艰苦、最昂贵,偶尔还最激烈的观鸟比赛,范围波及整个北美大陆。
这被称为“观鸟大年”。
观鸟大年比赛,规则很少,也没有裁判。鸟佬们只是在美国和加拿大大陆地区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飞行、驾车或乘船的任何方式,根据传闻去追逐某个罕见鸟种。有时候,鸟佬们能成功拍下“猎物”的照片,但很多时候都只能在笔记本上匆匆记下所见,并但愿其他参赛者相信自己。这一年年末,参赛者会向美国观鸟协会(American Birding Association)自报鸟种总数,协会将结果刊登在一份杂志体量的文件上。这份文件会引发各种各样的闲言碎语,简直比中学更衣室还吵闹。
遇到好的大年,观鸟比赛将充满激情与诡计,恐惧与勇气,来自内心深处去看和去征服的强烈渴望,交织着对胜利无法阻挡的向往。
遇到糟糕的大年,这场比赛只会耗费大量的金钱,留下伤痕累累的人们。
这个故事,写的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或许也是最可怕——的观鸟比赛,1998北美观鸟大年。
淡喉蝇霸鹟是一种外表朴素的灰棕色小鸟,原生于墨西哥中部。它的鸣声很独特,像是在说“咿——”。这种罕见鸟类上一次在国境以北的野外被确认目击时,哈里·杜鲁门还是总统,杰基·鲁宾逊正在全明星棒球赛中击出他的首支本垒打。然而,1997年12月中旬,一个鸟佬在亚利桑那州诺加莱斯附近的一处灌溉水库沿线徒步时,看到了这种蝇霸鹟,并向位于凤凰城的当地奥杜邦分会报告。
马里科帕奥杜邦分会将鸟讯登载在互联网上;图森罕见鸟鸟讯也在二十四小时电话热线上发布了这条讯息;休斯敦的北美罕见鸟鸟讯开始按照“高度警戒”订阅名单,给客户一个个电话通知。
2400英里外,在新泽西州费尔劳恩区的家中,桑迪·科米托接到了这个电话。世上这么多鸟,偏偏就是淡喉蝇霸鹟的目击记录,说服了他去诺加莱斯开始自己的观鸟大年。
他离开丹尼餐厅,驱车穿过长满仙人掌和牧豆树的山丘,来到巴塔哥尼亚湖州立公园的大门前。

一位管理员迎了上来。
“请交5美元。”她对科米托说。
为了到这儿来,科米托已经交了数百美元买机票、租车和住汽车旅馆。不过,在新泽西做工业包工头的多年经验,也让他深谙“办事之道”。于是他清了清在家乡能把在工厂大屋顶另一头作业的工友们吓一跳的洪亮嗓音,让它变得甜一些。
“哎呀,我就是个看鸟的,”科米托对管理员说,“来这儿找一只鸟而已。我只待十分钟。真的非要交5美元吗?”他乞求道。公园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开车经过,逗留不超过十五分钟的人,可以免费。科米托想钻这个空子。
管理员一双眼瞪得他害怕,乖乖交了钱。这种讨价还价的套路几乎从未奏效,但他总是乐此不疲。
科米托从互联网上记下了非常精准的寻鸟指示:“山丘底下右转,穿过露营地。环路的尽头是一条小径的起点,有大约四个停车位的空间。在这里停车,步行约1/3英里。你会在左手边看到湖和柳树;那只鸟通常会在右手边的牧豆树丛中。”
科米托找到了那个停车区,心中突然一反常态地涌起紧张之情。首先,他这次车就没租对。多年来,只要是去州外远行,他都会租一辆“林肯城市”,这也帮他在鸟佬圈中设立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形象:新泽西人,声音洪亮,爱说笑,开着一辆“陆上巨舰”横冲直撞。然而,科米托为这次大年租的却是不同以往的中型车。他的想法很简单:节省差旅预算,钱还是用来多跑点路,舒服就在其次了;租个没林肯那么高档的车,便宜些。不过,观鸟本质上是在做生物分类——长耳鸮总是耳羽长,短耳鸮总是耳羽短——此时此刻他却突然改变了自己一直以来独特的“野外标记”。观鸟界能接受这个开“福特金牛座”的桑迪·科米托吗?
还有另一个突发状况。四个停车位都被占了;还有更多的车沿公园道路狭窄的路肩停着。那些车上有一目了然的贴纸:萨克拉门托奥杜邦;图森奥杜邦。科米托心想:我来晚了吗?希望还不算太晚。
小径其实根本不是“径”。看上去更像是地面夯实的“牛道”——闻着味儿也像。草地鹨在灌木丛中疾飞往来,但科米托没理会它们。他一心只追那一只。
沿着这条路走了300码,他看到两个男人在牧豆树丛中来来回回地走,像是在找什么东西——可能是帽子丢了,也可能是找一朵花,一只蝴蝶。科米托则有别的猜想。
“你们看到那只鸟了吗?”他朝他们喊道。
“没有。”其中一人答道。
科米托挺喜欢这样的交流。在亚利桑那荒漠地带的荆棘丛中,他遇到了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故意说了些模模糊糊的内行话,对方却听得懂,也能回应。
观鸟大年自然是激烈的竞争,但科米托更喜欢与一群人一起追寻罕见鸟种。没错,一群人一起,就意味着会有很多人识别并记录同一只鸟。但对科米托来说,所有这些人不只是鸟佬,也是见证者。名列前茅的鸟佬们多年来都保持着密切的彼此关注,很多都怀疑他人有谎报行为。事实上,北美观鸟史上最激烈险恶、最针锋相对的那些争斗,都是因为在目击鸟种记录上起了争议。
这是科米托的大年啊,他可没心情去蹚这种浑水;但也有心理预期,总是会与质疑挑战狭路相逢的。这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比赛,信誉仿佛贞操——一旦丢了就无法挽回。科米托想要的不仅仅是大年记录,而是无懈可击的大年记录。
他沿着小径往前走,又看到其他鸟佬在灌木丛中找寻。科米托认得其中两位。
迈克尔·奥斯丁博士是位全科医师,几年前从家乡安大略省搬到南得克萨斯,目的就是更轻易地寻觅到难找的鸟种。这个策略很奏效:现在,他的总鸟种数在整个北美大陆排第十六。科米托还在丹尼餐厅吃早饭看日出时,奥斯丁就已身在野外找那只蝇霸鹟了。

另一位在灌木丛中穿梭的熟人鸟佬是克雷格·罗伯茨博士,来自俄勒冈州蒂拉穆克的急诊室医生。罗伯茨生性严肃,带着属于观鸟人的“男子气概”,告诉其他鸟友,自己花了很多时间听录音带,记忆不同的鸟鸣和音调。一听科米托讲笑话,罗伯茨就翻白眼。
科米托看到一丛灌木后面,有个找鸟人正举着一个“德固赛”有机玻璃圆盘;据说用这玩意儿能放大远处的鸟鸣声。目前为止还没什么收获。科米托向后仰起头,扫视高一点的牧豆树枝条。他的脖子早就习惯了这种运动,已经从14.5英寸抻长到了17英寸。鸟佬们给这种情况安了个专有名词:“莺颈”——花太多时间抬头往树顶上看,寻找疾飞的鸣禽。
突然,有人嚷嚷起来:“我找到了!”
科米托马上开跑,双筒望远镜拍打着胸口。万一鸟飞了咋办?他从大陆那头来到这头,成败与否就在最后100码。他紧张得仿佛胃里打了结,更用力地跑起来。
鸟还在?
慢点儿!
他离得很近了。此时此刻最不希望的事情就是把鸟吓跑。他气喘吁吁,满身大汗,心跳加速,小心翼翼地踮着脚往前挪动。
科米托前方20英尺处是克雷格·罗伯茨;罗伯茨前方20英尺处,有一只土褐色的鸟,在灌木丛中时飞时停。科米托迅速调整位置,背向太阳,举起望远镜。他了解罗伯茨,此人天赋异禀,擅长搜寻不容易辨识的鸟种;他不太可能认错。不过,淡喉蝇霸鹟和灰喉蝇霸鹟的确十分相似,而后者要常见得多。科米托仿佛盯梢的警察逐渐接近和锁定嫌疑人,迅速寻找鸟儿的专属特征——脸上的棕色更深,头更圆,鸟喙更短,腹部更黄。

接着,这鸟儿鸣叫起来。
“咿——”
这一叫就没跑了。科米托慌忙从背包里抽出尼康相机,咔咔咔地闪了十几张胶片。
这鸟是他的了,有现场见证人,也有照片。他掏出一个巴掌大小的笔记本,写道:淡喉蝇霸鹟,1/1/98,亚利桑那州,巴塔哥尼亚。
他真想大声欢呼,但鸟可能会被吓跑。
先前的紧张冰消雪融。他闲下心往后退,惊叹于自己周围的“奇观”。
牧豆树丛中冒出了三十多人,形成一股跃动而扭曲的脉冲浪潮,他们带着世界上最精良的光学仪器——徕卡、蔡司、施华洛世奇、兴和——包围了那只蝇霸鹟。相机快门咔哒咔哒狂响,伴随着嗖嗖的闪光灯。这明星鸟也有狗仔队了。
很难不感觉到一丝讽刺。在诺加莱斯,移民局派了1000名边防巡逻专员,阻止墨西哥人跨境入美。然而,同为“移民”,比朗斯代尔雪茄大不了多少的这“独一个”,因为长了翅膀,来自全美各地的数十人,就组成了朝圣队伍,隆重迎接它的光临。
很多鸟佬继续留下来看这只蝇霸鹟,享受看到高级罕见鸟种的喜悦,也和重逢的老友分享观鸟趣闻。“加新”之后的聊天是科米托热爱观鸟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他瞥了眼手表。
即便这只是大年的第一个清晨,桑迪·科米托也明白,时间宝贵不等人。他匆匆赶回去,上了那辆“福特金牛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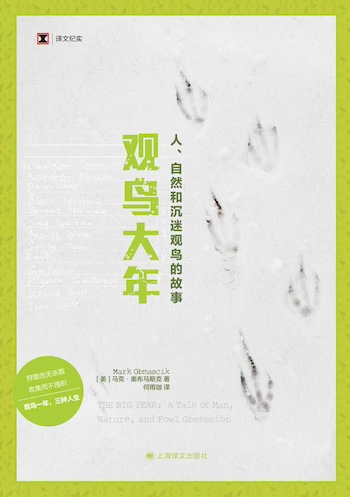
《观鸟大年: 人、自然和沉迷观鸟的故事》
[美] 马克·奥布马斯克 何雨珈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6年1月
文章作者

为什么女性总是那么忙?|新年书摘
想象一下,如果女性能因为负责家务劳动、照顾孩童和老人而获得收入,经济将会呈现出怎样不同的面貌。

为什么AI打桥牌赢不了人类?|荐书
如果说游戏是人类智力发展的关键,那么,它们同样是AI发展的核心。

在韩国,整形为何令人难以抗拒?
21世纪伊始,韩国变成了一个羽翼丰满的“富足”之国,什么是美丽,以及如何变得美丽,已经被韩国人多次重新调整和改造。

当妈妈直言“看不起孩子”,这个家和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
在非虚构写作《要有光》中,梁鸿试图追问一个本质性的问题:什么是爱?我们该如何去爱?到底是什么让孩子“生病”了?

昔日花旗银行头牌交易员:金钱只是游戏,但生活不是
这本书中失败的部分比成功的部分更感人,因为金钱是虚假的,个人的痛苦与挣扎却是真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