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艾滋病人自恃身患艾滋病犯罪,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问题,同时也是司法机关面临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东莞一镇街公安分局负责人无奈地说。
近些年,艾滋病人犯罪,公安机关抓了放,放了抓,抓了再放,循环往复,却迟迟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有恃无恐的艾滋病人
《广州日报》报道,10月29日中午,在东莞市凤岗镇官井头村,治安巡逻人员当场抓获了两名贩毒人员36岁的邹某和老板“地主”,并从他们身上搜出毒品4克多。不过当民警赶到现场后,却当场将邹某释放了。这一幕,被围观的群众拍下了视频。
东莞市凤岗镇油甘埔派出所一位黄副所长表示,“这个邹某怀疑有艾滋病、肺结核,他烂手烂脚,这种人抓了监狱也不收......坐牢也要身体好,烂手烂脚的抓回来,只能我们垫钱去治疗。”
据当地人讲,井头村毒品泛滥,而贩毒老板正是抓着警方的这一痛脚而越发猖狂。
事实上,类似的以艾滋病名义犯罪的案件在其他省市也是屡见不鲜。据《法制日报》早前报道,2010年5月,河南省新密市人民检察院以寻衅滋事罪批捕了名叫纪小英的艾滋病犯罪嫌疑人。经新密市人民检察院审查查明,2009年6月以来,纪小英在每月享受低保和各级政府不定时救济的情况下,利用司法机关无法对其关押的情况,组织儿子许某、姚建、艾滋病患者白广东以看病或需要救助为幌子,多次采取拦截、追逐、语言威胁、掰车牌、砸车玻璃、殴打、恫吓等手段,肆意拦截过往的外地运煤车辆,强行索取钱财。
法律的软肋
面对艾滋病犯罪者,公安机关的“捉放曹”做法实属无奈。艾滋病犯罪者既是特殊病人,同时又是犯罪分子,这种双重身份,让执法者面临一个共同的难题:他们不能和其他罪犯共同关押。目前我国大多数基层办案单位既没有针对艾滋病患者的羁押场所,为不给自身添麻烦,大都想办法给嫌疑人办理取保手续,将其千方百计拒之门外。而我国的多条法律条文无形中也成为了艾滋病犯罪者的“保护伞”。《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规定,“看守所收押犯人,应当进行健康检查,患有精神病或者急性传染病的不予收押”;《监狱法》明确规定,对感染艾滋病等严重疾病的罪犯,在作出劳动改造或劳动教养处罚决定后,可监外执行......”。
看守所不收,劳改场所不收,监狱不收,民警冒着极大的危险逮捕了犯罪嫌疑人,虽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正常审判,但如何关押就成为了司法机关最为头疼的一件事。无奈之下,大多数犯罪嫌疑人会被释放,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不能姑息
上述《法制日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艾滋病感染者中,大约70%是与违法犯罪活动相关联的,如吸毒贩毒、卖淫嫖娼等。如果任由艾滋病犯罪嫌疑人流入社会,那么疾病就会成立不法分子的保护伞。对他们的放纵,同时是对其他社会公民的不公平。2009年3月16日,轰动全国的擦鞋匠怒砍艾滋病敲诈者一案在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据新华网报道,在这起案件当中,被害人管利鸿,一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在当地多次以艾滋病为借口敲诈勒索他人。2008年6月16日晚,因5块鞋擦鞋钱与邱福生店里的打工仔王凯发生争执,并趁机勒索邱福生5000元。6月17日,管找邱福生要钱时,双方发生争执,管利鸿被连砍24刀不治身亡。
事发后,当地多家媒体称之为“一起都是被害人的庭审”。
如今两年多过去了,艾滋病人犯罪的状况似乎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尽管部分地区建立了艾滋病犯人的独立关押监狱,但由于财政、人力等多方面原因,这种做法并未得到广泛的推广。南方周末早前报道称改造艾滋病犯罪者作为一项社会工程,司法不可能承担全部,而应是“各级党委政府”一起来“抓这项工作”。
虽然法律存在空白,监管存在困难,但公安机关不能因惧怕或无法关押等借口不闻不问,司法机关亦不能不审不判,等待与姑息不能解决问题。
管利鸿借自已是艾滋病人的身份,在街坊中四处敲诈。
他连贫困的擦鞋匠邱福生也不放过,屡次以“不给钱,就杀人”威胁。连民警也怕了他,不敢关他,却被他追着跑。
这更使管利鸿无所忌惮,在武力威胁邱福生时,反被邱福生夺刀砍死。
这就是震惊沈阳的擦鞋匠怒剁艾滋患者案。当地多家媒体称之为“一起都是被害人的庭审”,“事关社会正义,事关国家对艾滋病人犯罪的态度”。
在一个不足20平米的擦鞋店里,邱福生5分钟内狂砍艾滋病人管利鸿24刀,被控故意杀人罪一案,于3月16日上午在沈阳市中院第九审判庭开审。
庭审即将结束,杀人者邱福生缓慢起身,向死者家属浅鞠一躬:“希望你们能理解。”
死者管利鸿的姐姐管利萍无法理解眼前的杀人者,她用极端的口吻向南方周末记者表达自己的愤怒:“他(如果)杀人不偿命,我们就杀了他。”
这就是震惊沈阳的擦鞋匠怒剁艾滋患者案。当地多家媒体称之为“一起都是被害人的庭审”,“事关社会正义,事关国家对艾滋病人犯罪的态度”。
“擦错鞋油……错得要命”
管利鸿因寻衅敲诈未得到满足,就把邱福生的擦鞋店砸了。邱福生赶忙求和,不料管利鸿放下狠话,“不给钱就杀了你们”。
庭审开始于人群静默、脚镣哗哗作响的那刻。被羁押9个月的擦鞋店店主邱福生踏上被告席时,棕色棉拖鞋突然掉了,转身找鞋的一瞬,向旁听席亮出一副苍白面孔。
妻子杨丽双手掩面大哭。“他起码瘦了30斤”,出事后她一直没机会见到丈夫。去年夏天邱福生去派出所自首后,就再没回家。
庭审再现了血案细节:地点“邱峰两口子擦鞋店”,时间2008年6月17日。
邱福生原名邱峰,13年前从辽宁农村来沈阳擦鞋谋生。从一元一双擦皮鞋开始入行,攒了11年的钱,赶在2007年冬天前租了门面开了擦鞋店。
警方调查显示,被邱福生乱刀砍死的管利鸿40岁,人称鸿哥的他是鞋店的常客,频繁出没在沈阳五爱市场附近的“温州一条街”。就在出事前一个月,为离开戒毒所,管利鸿吞下饭勺,抢救过程中被意外检出是艾滋病人。
血案发生的6月,走出戒毒所再次高调出现在“温州一条街”的鸿哥,在一家饭馆吃饭“吃坏了肚子”,开价2000元,成功索赔1000元;此前在一家发廊,他开价3000元,成功索赔1500元,理由是”头皮化脓”。
并非所有的索赔都得偿所愿。另有司法材料显示,早在2002年,他因涉嫌敲诈2.8万元被刑拘。
接受法庭调查时,邱福生说他早就认识“鸿哥”,以往擦鞋不敢收费。但夜里守摊的小工王凯不认识他,去年6月16日晚上9点多,鸿哥黑白相间的运动鞋伸过来时,王凯向他要5元擦鞋费,遂遭鸿哥“索赔”。
彼时沈阳《华商晨报》以“擦错鞋油……错得要命”报道了这起索赔事件。第一次登上报纸的管利鸿是这样索赔的:他从身上抽出甩棍抽向王凯的背和头,以及店门、玻璃、鞋架子、修鞋机。“能砸的都砸了。连打带骂,开价5000元。”王凯回忆。
店主邱福生赶回被砸的小店顾不上心疼,赶忙求和,不料管利鸿放下狠话,“不给钱就杀了你们”。邱就报警,管被警察带走了。
在王凯去医院治伤的路上,邱福生接到警方的电话:“管利鸿有艾滋病,你们的医药费可能要不回来了。”
“交互传染怎么办?”
凭着有艾滋病,管利鸿拿着菜刀追民警,被追杀的民警最终破窗而出,子弹上膛,对准管利鸿,他才终于停住。
擦鞋店离它所属的滨河派出所只100米,砸店伤人在先的管利鸿却未被拘留。
司法材料显示,当晚被带到派出所后,管利鸿高调亮出自己的艾滋病患者身份。派出所向家属和沈阳市戒毒所核实的当口,他冲向所里的厨房,抄起菜刀和勺子,大叫着追值班民警。
“我赶到派出所时,他正拎着刀四处追民警”,邱福生回忆,他很快躲到对面一个胡同里,看到刚到派出所的小工王凯肩胛骨挨了管利鸿一刀。
被追杀的民警最终破窗而出,子弹上膛,打开保险,对准管利鸿。他终于停住了。按照派出所提供的《情况说明》:“由于该人患有艾滋病,民警没有对其采取强制措施,该人将菜刀、饭勺扔到派出所门前空地后逃跑。”
派出所一位民警用“史无前例”来形容当晚情形。按照他的说法,这是该所第一起涉艾案,也是民警第一次在所内被追杀。“患者拿着菜刀,一旦发生流血冲突,交互传染怎么办?”另一不愿具名的民警称:“全辽宁没有一个专关艾滋病人的地方。”
姐姐管利萍也不了解管利鸿何时感染了艾滋病,何时开始吸毒。她说,身高1米8的弟弟在家中排行老末,原本是见到父母就一把抱过来亲啊亲啊的孝子,但“吸毒后的管利鸿整个人都变了”。
本报记者获知,2004年管利鸿被沈阳市公安局列入重点人口档案,曾于1998年和2003年两次被强制戒毒。重点人口档案每个季度的追踪栏中,大多写有“居无定所”、“无法找到”的字样。对此管利萍说,“就住在5005厂附近,很好找”。
2008年6月17日,也就是管利鸿抓了又被放的第二天,滨河派出所到沈阳市疾控中心调取管利鸿的化验报告,并打听到抚顺有一家专门管理传染病人的地方。
也正是这天,命案发生了。
我国为艾滋病人提供“四免一关怀”,病人体内的艾滋病病毒可以被有效控制。但夺去他们生命的却可能是其他病痛——即使是一个常规小手术,也会遭到绝大多数医院的拖延或拒绝
年过30岁的黎家明人生有两个转折点,一是7年前感染艾滋,二是3年前患上双侧股骨头坏死。
从公开的文献看,双侧股骨头坏死应该是常见病,一般采用手术治疗,治愈率达93.8%,治疗时间不超过1年半。不过,黎家明熬了3年多,却找不到动手术的医院和医生。
“我可能会死于非艾滋病。”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他平静地对记者说。
从发现感染艾滋伊始,黎家明就发现:“很多病友饱受痛苦,因为一个很小的常规手术辗转多个城市,多个医生,得不到治疗。”
4年前,他有一次病危住院,同病房的一个病友住了两个月,找不到医生动手术。那人每天挂着输液瓶,嘴里不停地唠叨:“怎么还不来?怎么还不来?”
黎家明没有想到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确诊双侧股骨头坏死之后,医生建议动手术。黎家明不敢说明自己是艾滋感染者,偷偷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动手术?”
“能。”
“我有其他病,乙肝,已经控制住了。”
“那没问题。”
“我还有其他病呢?”
“什么病?”
“艾滋病。”
“我们没有先例,做不了。”
其实黎家明没患乙肝,乙肝病毒传染性要强于艾滋,但没那么致命。“我打电话就是想知道,医生为什么会拒绝?”
现在,股骨头坏死的疼痛要远远大于艾滋病。黎家明没法弯腰,只能靠不断甩腿穿鞋。晚上睡觉,他连盖在身上的毛毯都没法挪动。骨头疼起来时,他整晚整晚睡不着觉。
唯有等待
“我还可以等,那其他病友呢?”黎家明说。一些艾滋患者会因此错过手术最佳时机。
2005年4月,37岁的李雪意外怀孕,到医院做引产手术,当时她已有一个小孩。这时候她和丈夫被测出感染艾滋。
这对李雪来说毫无征兆。院方找她谈话,要转院治疗。她糊里糊涂办完手续之后,传染病定点医院却还没准备好接收手续。就这样,她被这家三级甲等医院“赶”了出来。
夫妻俩到区、市卫生部门上访,甚至给当时的上海市长写信,都一直没有得到答复。
他们不得不转到外地求医。南京一家医院有过相同病例,愿意接收李雪。
这段日子是一场噩梦。住院时,李雪不敢拉开窗帘,连走廊都不愿去,一直躲在病房里。她不敢告诉任何亲人,只能和爱人互相鼓励。当压力太大时,夫妻俩抱在一起,嚎啕大哭。“死亡并不可怕,但凭什么把我们当牛鬼蛇神对待!”她回忆说。
7个月过去了。上海相关部门给她来电,说可以为她接生。“原本想引产,就这样被拖成了接生。”她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
回到上海的最初一个月,她失忆了,大小便失禁。“后来家人告诉我:你傻了,连自己爱人、孩子的名字都不记得,天天躲在家里。”她担心是药物副作用,医生说这应该是精神刺激太大的缘故。
这场遭遇不堪回首。“如果再要动什么手术,要再领教这些医院的歧视,我宁可选择等死。”她说。
刘杰是服务艾滋患者的NGO“爱之关怀”一名南宁工作人员。从他与艾滋患者的接触中发现,这是普遍现象。
今年初,“爱之关怀”开通了服务热线。一开始电话不多,但关于看病难题的投诉,他已接到了10至15例。“医院不会直接拒绝,而是说,你是艾滋病人,我先提高你的免疫力再说。然后一直拖。一般要等到行政干预,或者媒体介入之后才行。”他说。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这难题已存在多年。在防艾和关艾宣传多年之后,艾滋病人仍然像瘟疫患者一样被避之唯恐不及。
2006年初颁布实施的《艾滋病防治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医疗机构不得因就诊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人,推诿或拒绝对其其他疾病进行治疗。不过,没有具体实施细则。
一些艾滋感染者的求医经历一度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舆论表达了深切关注。但艾滋维权人士的鼓与呼,却没能改变现状。
去年,一个化名“奇奇”的5岁艾滋男孩再度引起了社会关注。他因食道堵塞急需救治,却被湖南多家大中型医院拒绝,直至到广州儿童医院。
虽然后来儿童医院认为院方一直在为奇奇诊疗,但许多艾滋维权人士更愿意理解为是舆论压力使然。随后奇奇得到了专家会诊,独立病房和医疗器械,病情得到控制。“‘奇奇’闹得那么大,但现在还不是一样?”广州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传染科医生说。
12月1日,就在记者采访进行之时,“爱之关怀”工作人员打来电话,告知一直协助治疗的2岁孤儿圆圆又被南宁一家大型医院拒之门外。
圆圆的右手臂有一块四五厘米见方的溃疡伤口,门诊医生建议住院治疗。但在住院3天后,住院医生却告诉刘杰,医院没有相关医疗条件。“医生说,国家没有拨款保证职业暴露的风险,他们不敢贸然接收。”刘杰说。“圆圆的溃疡还在扩散,甚至会到骨头里面去,可能会截肢的。”刘杰继续说。
现在刘杰不知道该怎么办,除了与病友互相鼓励之外,惟一能做的就只有等待。
谈起四年的“被艾滋”经历,和因此经历的人生变故,李建平常常悲从中来,继而是愤怒
四年的“被艾滋”生活里,李建平定期服用着这种所谓的治疗药物,莫名其妙地又成了“被痊愈”的病例 2003年10月,甘肃天水农民李建平被当地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告知得了艾滋病,4年之后,省市县三级疾控中心的领导来家里向其宣布,他的艾滋病“好了”。
此事一时引起各界震动,有记者专程赴天水采访,试图搞清楚天水——一个普通的地级市——是如何攻下世界医学难题的。
从“被艾滋”到“被痊愈”,事件主角李建平经历了人生的过山车,然而他的命运似乎只能停留在谷底,被宣布“病好了”之后,他奔波于三级疾控中心之间,但至今未得到答案:我的“艾滋病”是怎么得的?又是怎么好的?
得病
确认一个艾滋病人,要经过市、省两级疾控中心。
天水市清水县金集镇瓦寨村村民李建平,能说会道,头脑灵活,曾经是村子里响当当的人物,他十二年前就盖起了瓦房,早在大哥大时代就用上了手机。出事之前,还在天水市麦积区做着贩土鸡的生意,一天能赚二三百块,日子过得非常滋润。
命运因为当年震动天水市的一起公共卫生事件急转直下。2003年下半年,瓦寨村一个叫李卫东(化名)的人,生病住进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由于多日高烧不退,医院检查后发现他患了艾滋病,再一问,原来卖过血。
那个时候,艾滋病虽然已不陌生,在天水却并不多见。防疫部门反应迅速,立即对可疑人群抽血调查,主要目标锁定瓦寨村一带有卖血经历的人。很快,瓦寨村又查出三名艾滋病毒携带者:李卫东的媳妇、李建平、村里另一位卖过血的村民。
李建平从没卖过血,不是疾控中心的重点调查对象。但作为邻居,他出于同情,在李卫东生病期间曾照顾过对方几天,李建平承认那时还是“艾滋盲”,担心因此染病,便主动要求抽血检查。
约一周过后,县疾控中心(防疫站)的工作人员来到家里,郑重向其告知:经检查确认,你得了艾滋病。
据天水市疾控中心主任刘宝录介绍,当年确认艾滋病均需经过市、省两级疾控中心检查,审理确认后才通知病人。刘宝录称,直到现在,也没搞明白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现在只是怀疑,是不是当初送检过程中李建平的血被污染,或者是被搞错了”。
万幸的是,妻子张女商和两个儿子经抽血化验,均证实未感染病毒。张女商说,当年疾控中心通知李建平得病后,紧接着就要给她验血,李建平当时还懵着呢,没告诉对方老婆在哪。结果派出所开着警车去娘家找人,吓得她娘碗都掉在地上。
在全镇当时发现的9名艾滋病毒感染者中,李建平据说是惟一没有卖血经历的。由于性传播是艾滋病毒除血液传播之外的另一主要途径,因此他得病被认为是“生活作风”问题。
当年出于善良照顾李卫东的行为,开始被另一种眼光解读——李建平是不是和他女人有关系?甚至连他的一个弟弟也相信了,还跟嫂子张女商提起过。
等死
然而咋等李建平都没有死。一年多后,倒是他自己不想活了。
被通知得了艾滋病之后,李建平就开始在家里“等死”。妻子张女商说,疾控中心的大夫曾告诉她:李建平多则活两年,少则半年。
痛定思痛之后,两人开始“准备后事”。先是分房而睡,李建平睡正房,妻子睡厢房。李建平吃饭、刷牙用单独的碗筷、牙具。张女商说,她是和一个死人过了四年。
两人经过多年打拼,已经攒下十多万块钱,眼看人都快没了,钱留着也没有用。李建平在家里憋得慌,张女商便将存折交给李建平,让他到外面旅游,临死前快活一阵。
半年多时间里,李建平把他生前去过的地方又走了一遍,见了几个久未见面的老朋友,算是诀别。此外他曾到红色革命根据地大别山,想从革命先烈那里寻找 一点“精神力量”,他也曾到河南上蔡县某著名的艾滋村,想看看那里的艾滋病人如何生活,结果到了县城又觉得自己都快死的人了,看了也没啥意思,又坐车走 了。
那些天里,李建平住过一千块一天的总统套房,对其豪华程度至今仍记忆犹新:带游泳池,房间里还有台球桌,还有人专门擦鞋……
旅游期间,他还因为喝醉了酒,三次被小偷光顾,总共丢了将近两万块钱。
然而等李建平周游各地回来,钱花光了,生活却仍得继续。得病之前,他家境富裕,人又热情,在村里被人高看一等,家里经常热闹得很,但得病之后就成为 村里的另类。不仅再没人上门,路上遇到连打个招呼也怪怪的。李建平自己也知趣,很少去别人家,大多时间都闷在家里看电视。等死的四年里最怕的是过年,“生 艾滋病”期间,李建平落下了另一个病:一到过年就肚子痛,非得吊水不行。
据刘宝录说,为了保护艾滋病人的隐私,李建平得病的事一直保密,村里只有卫生员一个人知道。但李建平说,他得病的事“地球人都知道”,当时通知验血时是村支书用大喇叭喊的,山沟里空谷传音,连十多里外的张女商娘家都听得见。
有人劝张女商和李建平离婚,说这样两个儿子可以更名换姓,跟李建平没关系了,将来才能讨上媳妇。但张女商狠不下心,觉得丈夫没多久好活了,就算是再嫁,也得等他死了。
然而咋等李建平都没有死。一年多后,倒是他自己不想活了,2005年春节前,李建平对张女商说,他想找个没人的地方自己死了算了。张女商急了,一连 跟了他七天,最后买了一包老鼠药,拆开了跟丈夫说,咱把药拌在饭里,等儿子放学回来,全家人一起吃了算了。李建平一听害怕了,这才打消自杀念头。这一年, 金集镇杨郝村一位女艾滋病人,清水县当年查出的包括李建平在内的9名艾滋病人之一,割腕自杀身亡。
李建平的生活越发艰难。得病之后,刚刚好起来的土鸡生意自然做不成了。他做生意内行,种地却是外行,收成本来就少,还得变卖供儿子上学,家里一度穷 得揭不开锅。李建平决定“丢车保帅”,让正上初三的大儿子退学打工,供小儿子上学。这话李建平自己张不开口,便让卫生员李四友替自己跟儿子说,大儿子很懂 事,啥话没说就同意了。
得病等死的四年中,除了旅游,李建平一直呆在瓦寨村,他说,本来他想离开村子,回到麦积区过活,那边的人不知道他得艾滋病,也不会有歧视。但他走不 开,疾控中心要求呆在家里,每年还有四次验血。李建平算了一下,自从被确认得艾滋病之后,他又被疾控中心验了十多次血。每次他接到通知后不论刮风下雨都得 去镇卫生院采血,县疾控中心的车就停在一边,声称要在六个小时内送到省里化验。
关爱
“我们成了大熊猫,要做贡献呢。”
在清水县金集镇2003年发现包括李建平在内的9名艾滋病人之后,当地政府高度重视,次年,清水县被列为天水市仅有的两个全国艾滋病防治示范县区之一。此后,一些艾滋病慈善组织也纷纷到来,和其他病人一样,李建平也成为各界人士的关爱对象。
时至今日,虽然对疾控中心不满,但李建平仍对当地政府心存感激。据悉,清水县曾出台了针对艾滋病人的特殊关怀政策,比如每年有1200元的困难生活 补助。此外,每年还要在县里召开一次艾滋病人座谈会,县领导和疾控中心的领导均参加。李建平记得,有一次他主动发言,在感谢党和政府关怀的同时,强调作为 艾滋病人要自食其力,不能老是向政府伸手。县疾控中心主任张建国对此颇为满意。
四年等死但也是享受关爱的日子里,李建平见过香港人、日本人,还有非洲人。一般都是卫生员李四友提前通知,他和村里的其他两名病毒感染者各自步行十 几公里到镇卫生院参与活动。活动内容很简单,无外是握手、照相,用李建平的话说,是“接受参观”。有一次他对病友们半开玩笑地说:“我们成了大熊猫,要做 贡献呢。”
甘肃省卫生厅网站上一篇题为《情系陇原人 爱洒陇原地》的文章中提到:“2008年5月香港艾滋病基金会为清水县金集乡卫生院捐赠45.38万港币建设住院部。为了方便对感染者和病人的随访与治 疗,基金会为清水县乡村医生补助了10300元,激励了乡村医生更好地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服务。”
此外,南方周末记者查证,知名国际组织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全球艾滋病基金会也均有项目在清水县落户。
每参加一次活动,李建平也都有回报,衣服、文具、白糖等不一而足,有一次也拿过200元的现金。他曾鼓足勇气提出要一张与外来人士的合影,但被告知是内部资料,不方便给。
四年里,作为关爱对象,李建平见过最大的官是一位副省长,最大的专家是甘肃省防艾“首席专家”、省疾控中心主任医师席沧海。他跟后者更为熟悉。李建 平多少“见过世面”,席主任每次来都愿意跟他讲话,李建平见席和蔼可亲,与病人握手从不戴手套,心里很是感激,同时也希望这位专家将来能帮到自己,在 2007春节前举行的联欢会上,他执意送给席医生一条猪腿。那头猪是家里养的,还没长成,因为过年提前杀了。李建平在这次联欢会上收获颇丰,有书包、文 具,两袋奶粉、一斤白糖,一斤茶叶。
几年下来,除了那位自杀的女病人之外,另有几个病人相继死去,李建平印象中最后一次参加活动,只剩6个人了。再过了一年,本村的一个艾滋病人也死去了。
然而不知何故,村里最初确定的艾滋病人李卫东死后,他同样被确诊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妻子,据说由于生活困难(带有两个小孩),竟招了一个上门女婿,并 在村里摆了酒席。那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来自另一个乡镇,到现在还不知道同屋的女人感染了艾滋病毒,村里人没人敢告诉他。村卫生员李四友曾向上汇报过,据说上 面为此还开过会,但并未能阻止这桩不寻常的婚姻。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瓦寨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说,那女人会不会也和李建平一样,当初也诊断错了?因为她身体一直不错,不像患病的样子。这样一想,这位村民便会稍稍心安——她一直觉得那上门的男人可怜,但是又没办法告诉他。
痊愈
村里没人相信,大家更愿意相信李建平给书记送了礼,书记才开的证明
2007年的艾滋病人联欢会也是李建平最后一次参加镇卫生院的“活动”。几个月后,镇卫生院又举行“活动”,但李建平突然被排除在外了。他心里不 服:同样是艾滋病人,为啥不一视同仁?他说,为此还专门找了县疾控中心主任张建国。对方跟他解释,这次活动参加的人比较多,为了保护他(李建平)的名誉, 所以才没通知他。
但很快,李建平便发现,根本不是照顾名誉这么回事,而是疾控中心那时候已经不认为他是一个病人了。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07年9月,李建平的小儿子面临开学,家里没钱,借又没处借,他便再次找到县疾控中心主任张建国,在此之前,张建国曾以个人名义借给他3000元。张建国这次也没拒绝,从工资卡上又取了1500元给他。
然而就是这次在县疾控中心,李建平听到工作人员有意无意地说了一句话:你们村里是不是还有一个叫李建平的?
李建平说他当时脑袋像被人敲了一棍子,一下子惊醒了。没错,他村子里是有另一个跟他同名同姓同年龄的李建平。难道是搞错了?几个曾经不经意的疑问瞬间同时涌出来:为啥前一阵镇卫生院“搞活动”不通知自己,为什么2004年首次验血后一周,他又被单独再抽过一管血?
李建平想起追问时,那人已经再不说话了。
但他已经醒过来了,连滚带爬地回家,拐弯抹角地问同村的那一个李建平,对方承认前一阵曾被稀里糊涂地抽了一管血。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天水市疾控中心主任刘宝录承认,在发现李建平的HIV检测为阳性,而瓦寨村又有两个李建平之后,疾控部门又对另一个李建 平做过检测(该李建平2003年也抽血化验过,当时认定未感染艾滋病毒),证实其确实没有感染艾滋病毒,说明并非两个李建平搞混了。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时至今日,刘宝录主任称自己也不清楚。据他介绍,在省疾控中心确认李建平感染艾滋病毒后,每季度一次的抽血化验只是测李建平 的CD4细胞值(判断艾滋病治疗效果及人体免疫功能的重要指标)变化情况,以观察其病情的发展,而不是HIV检测。一直到了2006年7月,省里发现李建 平的CD4细胞居高不下,产生了怀疑,才给他作了HIV检测,证实为阴性,也就是说已经没有艾滋病毒。
然而无论如何,李建平终于因为县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提及另一个李建平而开始追问。他打电话给席沧海主任,说打算去省上重新检查,看看自己究竟有没有得病。“席主任跟我说,你别来了,我们过去。”
2007年10月19日,省疾控中心主任医师席沧海、市疾控中心主任刘宝录、县疾控中心主任张建国等五人来到李建平家,向其宣布其“病好了”。李建 平尽管有思想准备,但听到“病好”两字之后,还是哆嗦了一下,跟当初宣布其得病时一样大脑一片空白。过了一会,才觉得事情不对头,赶紧把村支书李贵海喊 来,让其做个见证人。
等到三辆车开走了,李建平才回过神来:我为啥不问问我这个病是咋好的呢?
实际上,后来尽管村支书李贵海为李建平开了一个“病好了”的证明,但村里没人相信,大家更愿意相信李建平给书记送了礼。道理很简单,谁也没听说艾滋病能治好。
至于为什么2006年7月就检测出李建平HIV阴性,为何拖了一年多才告诉李,而且不是说其没得病,而是“病好了”,刘宝录说,那是省上的事,他自己也不清楚。
告状
当听他大致讲了后,对方说,“你是不是喝醉了?”
被宣布“病好了”之后,平静下来的李建平越想越不对劲,觉得四年的罪不能白受,总得讨一个说法。他本能意识到问题出在疾控中心,可是前后来过那么多各级领导,他也不知找谁,最后想,应该找官最大的,于是到兰州讨说法。
李建平说,他曾几次找到省疾控中心席主任,席主任说这个事情得地方政府协调解决,他又找到市疾控中心刘主任,刘主任说这事主要问题出在省里,还是得省里解决。
这条路看来走不通,李建平得病几年来一直躲在家里看电视,知道媒体管用,但又担心省内的媒体报不出来,于是给西安一家报纸的热线打电话,当听他大致讲了一下后,对方说,“你是不是喝醉了?”随即挂断。
李建平也曾想过打官司,但不知道该告谁。越发感到走投无路之际,想起兰州有一个本家亲戚,便硬着头皮上门求助,他知道,外地的亲戚也知道他得了艾滋病,自己很可能是个不受欢迎的人。
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熟悉的律师。律师听完后,建议他官司别打了,给他指了两条路:一是到卫生厅直接找厅长;二是向新闻媒体投诉。
李建平先来到卫生厅找厅长,被告知厅长到人民医院开会去了,他又来到人民医院,没人告诉他厅长在哪。他灵机一动,给门卫买了一包烟,对方给他指认了厅长的车。他就在门口等,结果过了三个小时也没见那车动。
于是李建平只能再找媒体。7月底,甘肃省《西部商报》的记者约见了他。8月18日,该报以“甘肃首创‘痊愈’的艾滋病——天水农民戴了4年的‘艾滋帽’”为题刊登了此事。李建平一下买了十几份报纸,回村里到处发,乡亲们这才相信:原来李建平真可能没病。
报道影响巨大。“艾滋病患者痊愈”惊动了北京的“全国电视联播”(《星火科技30分》),并派来一个由资深记者领衔的节目组赶赴天水拍摄,该记者事后对南方周末记者称,本来是想过来好好宣传一下,结果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见报数天后,金集镇卫生院院长李本义给李建平打来电话,李被记者写到了报纸上,当初记者调查时,这位院长听说记者来了,把办公室门反锁上,说自己不 在,结果李建平爬到窗户上发现了他。于是“金集镇卫生院院长‘躲猫猫’”的字样出现在报纸上。李本义显然面临压力,跟李建平说,我是个农村大队长级别的小 官,人家让干啥就干啥。
至今没有人正面给李建平解释其从“被艾滋”到“被痊愈”的蹊跷过程,南方周末记者在当地采访此事时亦倍感阻力。尽管被当地病人指认,但李本义拒绝承 认他是李本义。而此前接受过记者采访的瓦寨村村支书李贵海显然面临压力,“不敢乱接待了”。一直负责通知李建平参加艾滋病人“活动”的村卫生员李四友,则 坚称一直不清楚李建平被确诊患有艾滋病,当年查血是为了查肝炎。而事情的另外几位当事人,清水县疾控中心领导以需要组织同意为名,推脱了采访。
9月2日,南方周末记者辗转甘肃省疾控中心办公室,以及甘肃省卫生厅办公室,采访此事均未遂。
只有刘宝录在经有关部门同意之后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他认为自己在此事中受了委屈,“忍辱负重、冤枉得很”,因为此事主要问题出在省上,报道后挨骂的却是他。至于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他现在仍不清楚。
当年的秘密,现在仍是秘密。
一番折腾过后,“痊愈”的李建平仍然无所适从。他摘掉了艾滋病的帽子,但似乎又背上了别的包袱。据其称,村里人知道他在告状之后,好多都表示不理解:政府能宣布你病好就不错了,你还想怎么着?

攻克“世纪难题”!消灭天花的“天坛株”为艾滋病疫苗研发打开思路
一款DNA-天坛痘苗复合型艾滋病疫苗已经在北京和杭州完成了IIa期临床试验,计划在未来1-2年内开展多种心IIb/III期临床试验以验证疫苗的保护效果。

一年给药两次的艾滋预防药落地博鳌了,但暴露前预防知晓率低问题待解
暴露前预防是指HIV感染风险者通过提前服用或者注射预防药物后,在体内形成屏障,从而阻止HIV感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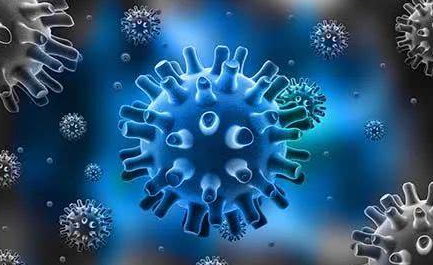
中国加强未知传染病前瞻布局:设立重大专项,提升新发传染病预警
据第一财经获悉,关于新发突发传染病的6项任务包括:未知传染病风险预测、新发突发传染病监测预警、人群防控与临床救治、预防诊断与治疗产品、应用基础研究与共性关键技术储备、研判决策示范应用。

艾滋病流行终结不远了?一年两针、预防HIV近100%有效的药物在美国获批上市了
这是美国FDA批准的首个一年仅需给药两次的HIV预防药物。

长效HIV疗法国内获批上市,会成为艾滋病“终结者”吗
来那帕韦是一款HIV-1衣壳抑制剂,将为对现有疗法无有效应答的HIV感染者提供一种每年仅需给药两次的全新治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