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谁小时候没有坐过拖着两根长长“小辫子”的电车?
一部电车几乎是一座城市的记忆和命脉,连接了几代人的回忆。
然而,它们正在悄悄消失。
也许某天当你想要牵着孩子的手,
带他去看看自己小时候坐过的电车,已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如果我们走太快,要如何割舍,那些年我们一起坐过的辫子车。
1906 年,中国天津创办了有轨电车交通系统。上海于1908年,大连于1909 年,北京于1921 年,沈阳于1924 年,哈尔滨于1927 年,长春于1935 年,相继建成有轨电车系统。直到50年代末,有轨电车仍然是这些城市的重要公共交通工具。随后,无轨电车和内燃机公共汽车发展起来后,这种早期的带铃铛的有轨电车才渐渐消失了。
然而,无论是伴随着开埠而来的有轨电车,还是50 年代初引进的无轨电车,那些划过城市天际的架空线和“小辫子”是他们共同的特征。进入90 年代后,随着我国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和公共交通的迅猛发展,有的城市缩减了电车规模,有的则干脆将电网拆除,“辫子车”逐渐萎缩,淡出人们的视线。1991 年,全国拥有无轨电车的城市尚有26 座,如今,这个数字锐减至11。在这凤毛麟角的11 座城里,“辫子车”的线路更是屈指可数:北京15 条,广州15 条,上海9 条,武汉7 条,太原5 条,济南4 条,青岛3 条,洛阳3 条,杭州2 条,
大连1 条,哈尔滨4 条。这次,我们选取了其中三座城市的故事,这三座城里的那些“辫子车情结”,恰好应了北宋词人晏殊《浣溪沙》里的三句下阕——“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无可奈何花落去
从晚清、民国到共和国,有轨电车见证了这个城市乃至我们民族的血泪、荣耀和传奇。它退役后,无轨电车继续行驶在这座城市里,到明年,正好是整整百年。然而,目前上海无轨电车的数量仅余90 辆,可以说是21 世纪以来,无轨电车系统衰退最明显的城市,没有之一。
“ 那个时候,全国所有城市的电车司机,都要到上海来培训。”
“那个时候,其他地方要开通无轨电车,都要请上海的专家过去考察论证。”
“那个时候,上海电车线路最多达21 条,拥有电车900 多辆,营运规模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三。”
所有人开口跟我谈起上海的“辫子车”,用的都是过去时。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上海已经有6 年没有更新过电车了。”然而,这座城市,却曾是远东最早开始运行无轨电车的城市,拥有着迄今为止世界上持续运行时间最长的无轨电车系统。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1 月31 日,光滑的南京路路面被铺上了锃亮的铁轨,由英商投资的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这条线全程约为6 公里,每天清晨5 点半由外滩开往静安寺。那时的电车是没有车门的,乘客可以根据需要随时上下。车厢分三等,洋人乘坐宽大舒适的头等车厢,中国人只能坐三等。
后来法商的有轨电车,车厢只分头等和三等,没有二等,且座位再没有身份限制。到三十年代,80 多条有轨电车线路遍布了整个上海中心区域,日均运客达48.6 万人次,成为当时市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
旧日有轨电车就如同的今日上海地铁,每天高峰时间里每一节车厢上都塞满了人,罗嗦的寒暄和问候,暧昧的天气和时局,上班的职员和跑单帮的生意人,也许,还有那些我们认识的人。
茅盾《子夜》第一章第一段,写的是电车;张爱玲《封锁》的第一章第一段,写的也是电车。它是《十字街头》中,白杨和赵丹相遇、相知的邂逅地;也是 1927 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夜,小南门警钟楼下电车工人口耳相传的集结信号:“救火钟声响,电车开进厂。”
从晚清、民国到共和国,它见证着这个城市乃至我们民族的血泪、荣耀和传奇。
1975 年,上海最后一条有轨电车线被拆除。它退役后,无轨电车继续行驶在这座城市里。
上海的无轨电车诞生于1914 年,是中国第一个开通无轨电车的城市。到明年,它即将在这座城市里迎来百岁生日。然而,目前上海无轨电车的数量仅余90 辆(1996 年时还有980 多辆),线路数从21 世纪初的全国第一下降到第三;配车数从全国第二下降到倒数第三。可以说是21 世纪以来,无轨电车系统衰退最明显的城市,其发展前景已然到了岌岌可危的境地。
可是,即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还有人从未放弃过对电车的坚守和保护,他们中,有每天工作在电车第一线的50 后,也有本职工作和电车毫无关系的80 后甚至90 后??
1939 年 在鲁迅先生家里做客人,刚开始是从法租界来到虹口,搭电车也要差不多一个钟头的工夫,还记得有一次谈到半夜了,一过十二点电车就没有的,但那天不知讲了些什么,讲到一个段落就看看旁边小长桌上的圆钟,十一点半了,十一点四十五分了,电车没有了。“反正已十二点,电车已没有,那么再坐一会。”许先生如此劝着。鲁迅先生好像听了所讲的什么引起了幻想,安顿的举着象牙烟嘴在沉思着。——萧红《回忆鲁迅先生》
1943 年 我们的公寓近电车厂邻,可是我始终没弄清楚电车是几点钟回家。“电车回家”这句子仿佛不很合适——大家公认电车为没有灵魂的机械,而‘回家’两个字有着无数的情感洋溢的联系。但是你没看见过电车进厂的特殊情形吧?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赖,克赖!”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车里的灯点得雪亮。专做下班的售票员的生意的小贩们曼声兜售着面包。有时候,电车全进了厂了,单剩下一辆,神秘地,像被遗弃了似的,停在街心。从上面望下去,只见它在半夜的月光中袒露着白肚皮。——张爱玲《公寓生活记趣》
吴崇嘉:我和电车打了一辈子交道
1963 年8 月15 日凌晨零时17 分,上海历史上的最后一辆有轨电车末班车从静安寺开出。等候在南京路两旁的工人、干部和解放军战士等这一辆最后的有轨电车开过,立即撬掉电车钢轨。在南京路上行驶了整整55 年的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就这样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凌晨3 时52 分,一辆无轨电车拖着“小辫子”离开静安寺起点站向外滩方向驶去。它就是上海电车20路,上海历史上的第一辆无轨电车。50年来,20 路与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还有如影相随的电车架空线一起,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和交通发展。
40 年来,吴崇嘉老师傅与20 路一起,写下了这座城市里的电车“故事会”。
关于电车啊,你们来问我还真是问对人了。我1972 年从学校毕业进入公交公司,最早在场里的车间里当学徒,修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车子,后来去了隧道5线做技术工作。从13路开始,到15路、16路、19路,再到20路、21路、23路、27路、37路,几乎每条电车路线,我都工作过。每天做到最后一班末班车回家,我也回家了。后年我就退休了,和电车打了一辈子交道,可以讲的故事太多啦??
世界第一水底隧道电车
隧道五线是我一定要介绍的。90 年的时候,隧道五线通车,当时是全中国第一条隧道电车线路,也是世界上第一条在水底隧道通行的无轨电车线路,这是很骄傲的事情。
那个时候大家还都担心电车容易“掉辫子”的问题万一在隧道里发生了怎么办?为此,政府专门组织了一批研究所的研究员进行技术改进。这个事情我也
有幸参与过。我还记得当时的那个工程师姓桑,他来找到我,我那时在21 路修车,专门陪他去了场里实地考察。那时经费有限,其实是完全依靠我们自己国内的技术来改进隧道五线的。
福建路雷击事件
在还没有地铁、出租车的年代,电车是大家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人多的时候,我2 分钟内要放6 部车,我们同时有4 个调度当班还来不及。这里(九江路终点站)车不放得快一点的话,那边南京路等车的人会一直排队堵到江西路,这是真事,人群能把江西路路口都堵塞住。以前人多起来的时候,放巨龙车都不够。
那个时候一条电车线路上,每天同时会有三十几部车一起在跑。我记得八十年代的时候,有一天下雨打雷,就在福建路那个角, 一道雷劈下来,十几部车
全部中标抛锚。那时有电车一场、电车二场、电车三场,场里所有的抢修车都赶到现场去修。
手摇车窗“吃掉”结婚照
老电车都是用摇窗机的,玻璃窗都靠手摇上去。这里有个好笑的事情。以前人家从照相馆拿了拍好的结婚照出来,不是要去坐电车么。电车里人多、又挤,
老式结婚照都尺寸很大又不能折叠,小青年们就把结婚照紧贴着电车的玻璃窗放。结果,路上碰到一个刹车,“噗”地一声,结婚照就掉进手摇窗玻璃的缝隙里去了。
你们不要笑,手摇车窗“吃掉”结婚照的事情我碰到过好多次。等晚上车子回场,他们都要来找我帮忙把板子从里面拆掉,把照片拿出来。
借居民用电的电车“GPS”
最早的时候我们没有GPS,对调度来说,不知道车子什么时候到哪里了。大家就想办法了。拿20 路来
说,我们就从架空线上接了两根线下来,架在外滩边的某棵树上,装了个铃。车子开过,铃响了,我们远远就能知道它快到站了。这办法很原始是不是?
这其实还不算最早的“GPS”,上海电车上最早的“GPS”算起来,应该是出现在15 路上。这个所谓的电车“GPS”,说穿了就是利用红外线来对车辆途经站点进行监控。大概是80 年代末的时候,15 路车顶的接线板上就装置有红外线设备,样子是一条一条的粗细线,有点像现在超市里的条形码。我们当时在几个闹市区路口的墙壁上都装了红外线监测头,车辆经过的时候,就像超市里买东西时扫条形码一样,通过扫“电车条形码”来知道电车位置。这种探头,我记得北站、西藏路、石门路、静安寺、淮海路、徐家汇,还有万体馆都各有一个。
这里还有桩滑稽的事情可以讲。当时,徐家汇天平路肇嘉浜路路口的那个红外线探头,是装在居民楼墙上的,借的是居民用电。那些居民倒是蛮好的,我
们跟他们谈好一个总价,比方讲,一个月就给他们十度电的电费,每个月他们就会帮我们去付掉。因为这个东西没法关,晚上电车也会开过的呀,再说深更半夜的,难道叫居民去每天帮你开开关关的啊。所以我们夜里也不关的,一直借居民的电通着。那个时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这种调度的辅助工具,就算当年上海电车上最早的“GPS”了,只有15 路上有。
@ 阿肯,27 岁,摄影师
小时候第一次坐隧道五线穿梭在延安路隧道时,简直觉得太神奇了。原来电车也能在隧道中行驶。以前坐过隧道二线、三线,都没有这种感觉,只是觉得黑暗冗长无比。可是坐在电车里过江,实在感觉很棒!
@ 胖胖的加菲,29 岁,记者
隧道五线刚开通的时候,是上海电车最风光的年头。那时在延安东路隧道上坡,隧道五线561GF 巨龙电车能轻松超越喘着粗气的隧道三线661F2 汽车,这一幕至今成为电车迷们津津乐道的画面。当时,电车不仅具有“零污染”的优点,在速度上也丝毫不输给公共汽车。
@ 程乃珊 (上海作家)
曾经每天搭乘8 路有轨电车。我特别喜欢电车从南京东路悠悠晃晃地拐入中山东一路外滩,穿过外白渡桥,从桥上回望外滩建筑,再前望越来越近的上海大厦,霎时间,有种超越时光的体验, 尽管五六十年代是个标语口号无处不在的年代,但在这一瞬间,一切都似被过滤掉了??外滩应该是一位庄重肃穆的女皇,而不是国际巨星。而那已消失了的叮叮电车声,曾经那样恰到好处地装饰了她,与外滩的钟声,缓缓流淌的黄浦江水,沿江堤岸郁郁葱葱的绿荫,以及那52幢雍容的建筑,共同织造出百年外滩这顶永远的皇冠??有轨电车渐渐拆除了,但每每看到那些残留的电车轨道,孤寂地在阳光下熠熠闪光时,我总觉得若有所失!
——《上海素描》2011 年
冰与火之歌 上海电车迷的焦灼与期盼
他,走遍了中国内地所有还留着无轨电车的城市,拍摄并记录;他,为电车几年里连续不断地写上访信给市政府;他,在中学地理课上让自己的学生们开展关于电车的调研项目;他,是一个90 后,却也拍完了上海市内电车线路大集合,陆续放到自己工作的门户网站论坛上。
他们,听说某天是XX 型号电车或者XX 路电车的“最后一夜”了,便会自发地赶去那里送行、告别;他们,会选择八十年代上海街头最有代表性的电车型号,筹款后联络广州的工厂,自行组织制作。他们,是一群我采访过的最热情和赤诚的车迷群。听说是为了电车专题而来,每个人都积极主动,帮我寻找素材、联络相关人士。这些人,大多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从事着一份不错的职业:教师、医生、法律顾问、银行金融业人士等等。
他们,从未放弃过对电车的坚守和保护,即使是在上海已经有6 年没有更新过电车、每天都有线路在消失的困境下。为什么肯投入这样大的时间和精力?是什么在维持着这份热爱?——当我这样提问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大多简单而重复:“不为什么,就是很单纯的喜欢”;“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音符点,那些城市里川流不息的电车,犹如一条条五线谱;这点和线,每天每时,
正在奏响这座城市里最让人感动的“冰与火之歌”。
编辑推荐:

任正非:车的最高级别就是安全
任正非表示,汽车行业的根本是要把车造好,车的最高级别就是安全。

中汽协发布供应商账款支付倡议,工信部最新回应
推动缩短货款账期,有助于整车企业提升经营管理质效,加快建立现代化管理体系和做大做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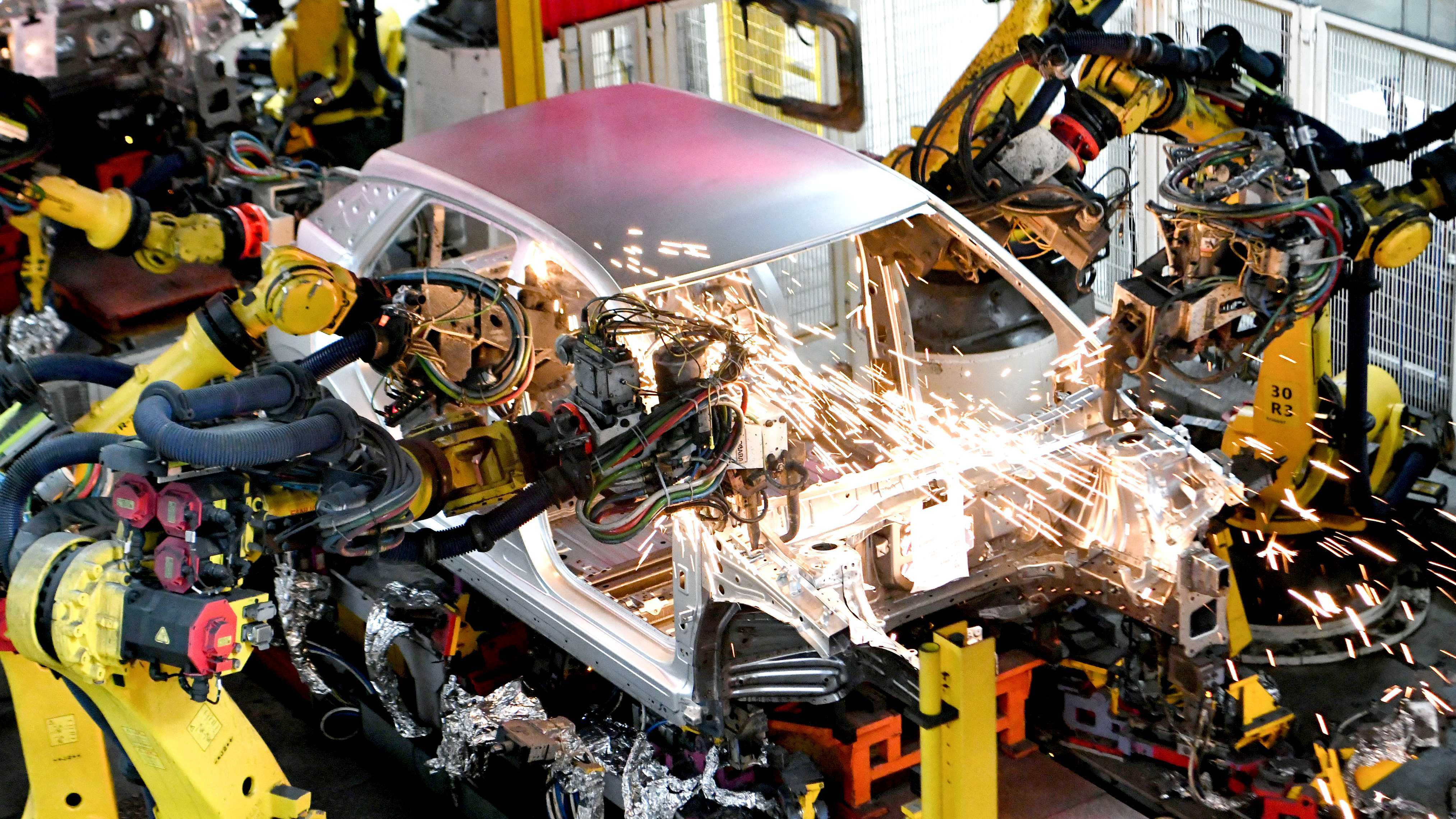
力争全年销量3230万!8部门发布汽车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
新一轮十大行业稳增长方案正在陆续出台。

为期3个月,工信部等6部门开展汽车行业网络乱象专项整治行动
集中整治非法牟利、夸大和虚假宣传、恶意诋毁攻击等网络乱象。

支持龙头做大做强 深化智能网联汽车试点 浙江汽车产销两旺
上半年,全省汽车产量89.6万辆,同比增长18.3%,产量居全国第7位。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51万辆,同比增长58.4%,自4月以来产量稳居全国第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