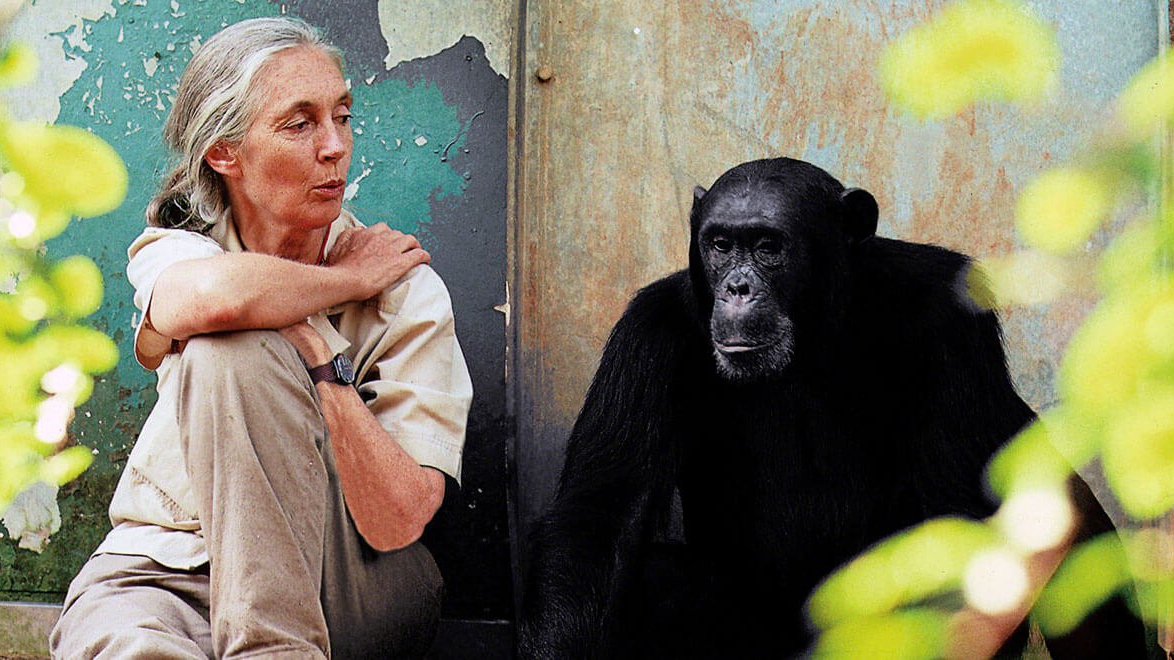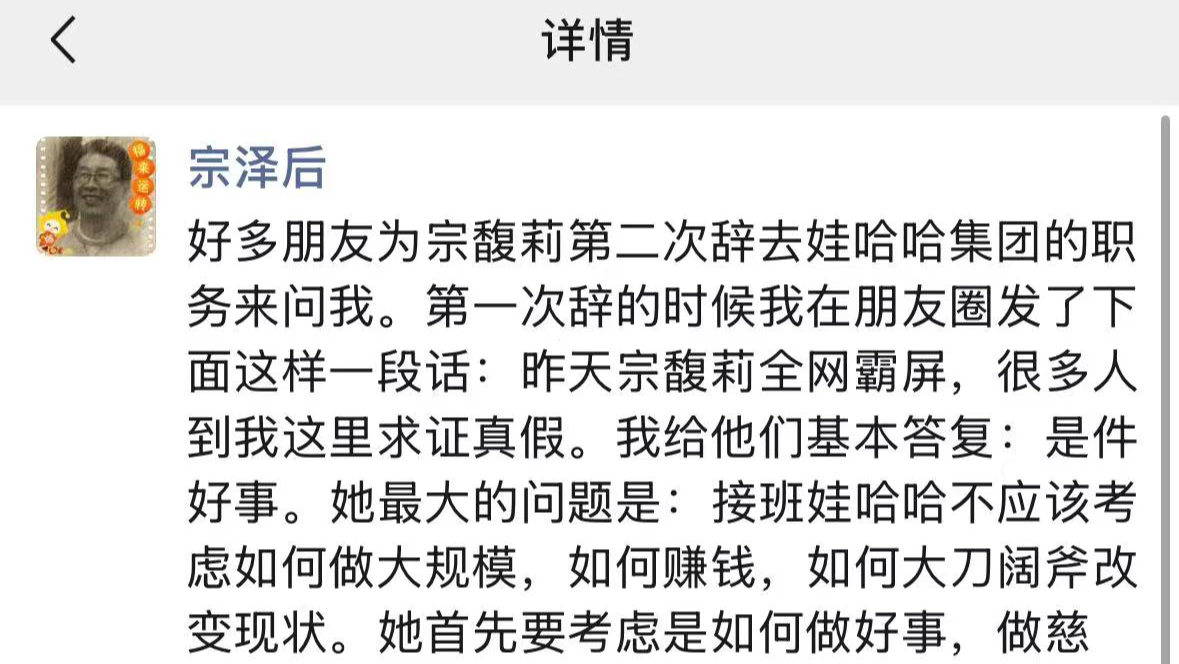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纯白衬衫、灰蓝牛仔裤、黑牛皮鞋、颔首、脊背略弯。在众多西装革履高谈阔论的文化名人与学者专家之中,伊恩·布鲁玛显得朴素而谦逊。不露锋芒的外表与剑走偏锋的观点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冲击着我的视觉与听觉,很怕错过眼前这位“世界人”充满睿智的明晰与富有想象力的洞见。
相较于当今诸多大谈理论的自由主义理论家,伊恩·布鲁玛并未急于绞尽脑汁地为鲜活多变且危机四伏的世界开出灵丹妙药,他似乎总是警觉于任何形式的理想国与乌托邦,那种绝对的、非黑即白的意识形态,在他看来无疑会将现代社会推向危机的渊薮。他始终强调的是自由社会所具有的开放性与多样性,“即使冲突是人类世界的常态,我们仍然需要开放的态度来增强社会的弹性”。在谈到普遍价值与特殊文化之间的张力时,他并没有被伏尔泰眼中的椰子裹挟,“伏尔泰的椰子无法种遍全世界”,相反,他总能以一种局外人的审慎眼光看待这个生活世界。
相传伏尔泰曾将自己的墓地修建得非常奇怪,那是一个插入教堂墙里的棱锥体,上面写着:“聪明人会说,我既不在里面,也不在外面。”布鲁玛就是这样的聪明人,他既不在西方文化里面,也不在西方文化外面。本月,布鲁玛参加上海书展期间,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专访。
普遍性问题的危机
第一财经日报:在最近的著作《驯服诸神:三大洲的宗教与民主》中,你认为只有当宗教信仰与世俗权威彻底分离时,宗教诉求与民主推进才可以并行不悖。埃及安全部队对两处抗议者营地进行“清场”行动,反映出伊斯兰世界民主化进程中面临的各种困难,这些困难是否关乎你一直强调的宗教与民主之间的关系问题?
布鲁玛:埃及的民主化问题非常复杂,从根本上说涉及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但从现实考量,更多的囿于利益各方的力量抗衡与相互牵制。二战之后,穆斯林世界的世俗政权多掌握在独裁军政府手中,与此同时,借由宗教诉求对抗政府的宗教组织屡见不鲜,比如穆斯林兄弟会这样的组织。对于伊斯兰世界的自由主义者来说,一方面支持军政府以武力解除来自宗教组织的威胁,因为在他们看来,极端宗教组织会因其狭隘的宗教主张破坏非宗教人士的利益;但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无法信任独裁军政府,毕竟它本身就体现了一种非自由的统治形式。事实上,对埃及政府以及其他穆斯林政府来说,在伊斯兰宗教与自由民主之间找到妥协的出口是非常困难的。
日报: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这种极端冲突背后,有普遍性的问题?
布鲁玛:是的,普遍性问题是文化研究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也是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但就现实政治生活而言,我认为“普遍”这个提法本身就很有问题。如果有人认为在我们的世界中存在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或宗教信仰,那是非常危险的。
我举个例子,回顾20世纪的现代中国史,你会发现在苏联共产主义者与毛泽东思想之间存在某些很严重的纷争,比如,毛泽东认为结合中国的情况,革命一定要从农村开始,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但苏联共产主义者却坚持教条,认为革命必须以城市为中心。结果一目了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不能直接拿来处理中国的具体情况。
文化拒绝标签
日报:就像你说的,从政治实践角度看,观念与文化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只有通过具体分析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但当不同观念或不同文化发生碰撞时,我们应当怎样把握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呢?
布鲁玛:首先,定义“西方价值”甚至“启蒙价值”都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我们说人权算一种普遍价值的话,要知道,人权的观念来自于基督教,传教士将人权作为一种共同价值传播于世界各地。狭义上讲,无论是日本人、中国人、法国人都会主张人不能被随随便便施以刑罚,如果从人权的这个角度出发,那这种主张无疑具有普遍性。但是如果把人权观念的范围扩大,比如认为男女平等也属于人的基本权利,那这种普遍性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就我们知道的,男女平等的权利诉求仍然不被一些文化所共享。
应然与实然之间、可欲与可行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很多时候,不同文化事实上共享了相同的价值诉求,只不过每种文化的价值在排列次序上存在差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同意存在普遍价值的;但是,如果认为某一种文化所包含的价值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去规约处在不同社会的个人,那是非常危险的。
日报: 我们在对不同文化做出判断与评价时,往往陷入过度概括的窠臼,习惯笼统使用“西方”或“东方”这样的概念,对这些语词的使用存在很多偏见,这类似于你提到的某种冷战思维,怎样避免?
布鲁玛:首先,当我们谈论“文化”的时候,会有很多不同的内涵,比如,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文化可能指的是社会行为,从文学的角度看,文化可能用来指文学作品,即便你让文化研究大家雷蒙·威廉斯来说文化是什么,他也只能告诉你文化最初指什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现在仍然没有固定的说法。
其次,不论文化所指究竟为何,我们必须承认任何文化都不是铁板一块,也不具有统一标准。比如,你不能随随便便说中国人或者中国文化认为什么是怎么样的,因为你口中的中国人是由不同的个人组成,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意见,而中国文化自不必说,在不同阶段同样产生了变化。现实往往是复杂而多样的,我在《西方主义》里提到,西方主义者倾向于简单地给西方文化贴上“工具理性”、“物质主义”、“无根的”、“强调个人私利”等标签,以此作为评判整个西方文化的标准,这种对“他者”的想象,就像你所说的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过度概括,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否认。
最后,谈到怎样避免这种偏见,是个很棘手也很复杂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至少在一个开放的,具备民主和自由精神的社会里,每个人对他人的承认和尊重会多一点,但如果一个社会是封闭的,只能存在一种声音,那么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就很难改变,过度概括或者偏见也很难避免。
法律的权威
日报:在《阿姆斯特丹的谋杀:电影人梵高之死与宽容的限制》中,冲突是讨论的焦点,你说过冲突才是人类生活的常态,面对冲突,你认为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态度?
布鲁玛:相信价值具有普遍性的人,往往认为好的或者善的价值之间必然不会存在冲突,但很多时候,由于利益的分疏,好的价值或者正当的目的之间存在不相容的态势,更有甚者,会发生激烈的冲突。比如,平等与自由这两种价值本身都是无可厚非的,但在现实社会中它们之间的矛盾有时候甚至无法调和。
我认为首先要做到的是承认不同利益的存在,正视各方冲突的发生。事实上,城市人口与乡村人口、富有阶层与穷苦阶层、知识阶层与大众阶层……来自不同区域具有不同身份的每个人,他们的利益诉求是不一样的,只有在承认利益不同的前提下,在不同利益主体间发生冲突时,我们才能找到相互妥协的平衡点。
其次,暴力是最不应当选择的。避免暴力发生的最有效途径是将冲突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任何集体与个人都不能超越法律。另一方面,不同利益主体应当有表达诉求的渠道。比如,国家应当真正发挥政党的政治作用,使政党成为代表利益诉求的和平而有效的方式,从而在不同利益之间达成妥协。谈到妥协,它必将是一个不断试错、谈判、磋商的开放过程。
日报:在中国,文化比较更多的是在对自己的文化不是那么天然自信之后才热衷起来,你的文化比较研究的初衷是什么?作为研究者怎样在情感倾向与学术中立间达到平衡?
布鲁玛:我觉得对自身文化过于消极的反思是不对的。在中国,真正出问题的是其他基础性的问题,绝非文化的问题。当出现社会问题的时候,寻求政治的而非文化的解决方式才是可行和有效的,文化是具有历史性的现象,你怎么可能将文化作为一种对象加以改变呢?
任何人无论身在何处,都不能否认我们生活在自己的文化背景之下,我们的情感、判断都深深受到这种文化背景的影响,但正是这种源自个人体验的经历,为我们以旁观者的角度去研究和学习别的文化知识提供了条件,与此同时,对其他文化的研究和学习能够反过来帮我们更深刻地分析和了解自己所处的文化。就我个人而言,早期在日本的学习以及现在对中国的了解,都使我在反观自己文化的时候受益匪浅。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
当代欧洲知名学者及作家,出生于荷兰海牙,先后在荷兰和日本就学。曾于莱登大学攻读中国文学和历史,后专注于研究日本,游历亚洲各地。曾担任《远东经济评论》和《旁观者》杂志的记者,现为纽约巴德学院教授。先后出版《面具背后》、《上帝的尘土:当代亚洲之旅》、《罪行的报应:德国和日本对战争的回忆》、《伏尔泰的椰子》、《传教士和浪荡子:东方和西方的爱与战争》、《西方主义》、《阿姆斯特丹的谋杀:电影人梵高之死与宽容的限制》、《驯服诸神:三大洲的宗教与民主》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