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查理周刊》血案之后,对“欧洲伊斯兰化”甚至“西方伊斯兰化”的担忧再次凸显。
当然,这种担忧并远不是从《查理周刊》血案开始。实际上近年来随着穆斯林移民增多,多国出现穆斯林青年骚乱,加上国际上极端组织活跃,欧美不少保守派人士对欧洲伊斯兰化或更广泛的西方伊斯兰化感到忧心忡忡。
《查理周刊》案后,这一话题再度激活,连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也有不少类似的讨论。报道、理论和讨论之余,欧洲人已经开始行动,不少城市出现反对“欧洲伊斯兰化”的游行,民间还有各种相应组织,比如专门有“阻止欧洲伊斯兰化”(Stop Islamisation of Europe, 活跃于英国和丹麦) 这样一个非政府组织。
此外,《查理周刊》袭击发生后,犹太人在法国乃至欧洲的处境也再度成为话题,因为一些极端伊斯兰分子袭击是以犹太人为目标的。有些犹太人开始移居以色列。一名移居到以色列的犹太人前两日在接受BBC采访时还说,她在以色列感到更安全,因为以色列知道怎样保护公民。
另一方面,土耳其总统泰伊普?埃尔多安在谈到西方社会“我是查理”支持行动和对“欧洲伊斯兰化”担忧的言行时则说,欧洲充满着“虚伪”,患了“伊斯兰恐惧症”,在叙利亚战乱不休情况下,土耳其已经接纳了一百多万叙利亚难民。而一直号称“人道主义”的欧洲,因为惧怕伊斯兰,在帮助难民问题上缩手缩脚。
到底是担忧“欧洲伊斯兰化”的人担心得有道理,还是因为他们患有“伊斯兰恐惧症”而夸大其词?
笔者以为,反对极端伊斯兰分子是全球应该做的事,欧洲也不例外,但如果因为穆斯林人口增多,担心“欧洲伊斯兰化”,则有些没有必要。
首先,一方面看来,担心欧洲伊斯兰化,实际上是在一种用静止、孤立的眼光看人类的历史。这种观点的前提,是认为今天的欧洲文化模式,就是固定不变的模式;或者认为会导致中世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长期冲突的历史重现。但无论文化还是政治,今天的欧洲远非三百年前的欧洲,三百年前的欧洲也不是五百年前的欧洲。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不断在变化,一直民族融合、文化冲突,在融合冲突过程中形成新的文化。可以肯定,明天的欧洲,不会和今天的欧洲一样。
另一方面,移民欧洲的穆斯林,是生活在欧洲的穆斯林,他们和世界其他各地穆斯林在很多世俗观念上也不一样。绝大多数穆斯林,移居到西方之后,保留自己的信仰和生活习惯,但他们和西方社会没有根本冲突,也认同民主自由平等的基本价值观。欧洲多次穆斯林青年骚乱,多与社会经济有关,不是单纯的宗教冲突。欧洲穆斯林人口增加,并不意味着欧洲要“伊斯兰化”。
其次,对欧洲伊斯兰化的担心,多少把伊斯兰教极端分子和伊斯兰教混为一谈。极端分子并不能代表整个伊斯兰,极端思想的最大受害这是伊斯兰国家,和极端分子进行生死存亡斗争的也是伊斯兰国家。看看横行中东的“伊斯兰国”,看看在尼日利亚屠杀的“博科圣地”,看看诸多伊斯兰国家对基地的打击,就可以知道,极端分子绝对不能代表伊斯兰。因为欧洲出现极端分子的袭击,从而担心欧洲“伊斯兰化”,对大部分生活在欧洲的穆斯林,应该是一种误解。
再次,伊斯兰和现代西方政治制度是不是“天敌”?这个问题应该更全面的看,比如伊斯兰大国印度尼西亚的民主进程,就在东南亚首屈一指。就是经济落后的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国,也都确立民主制度;半岛电视台能在卡塔尔生存并办得如火如荼,也说明伊斯兰世界并非如某些人所说的还处于“中世纪”。
欧洲是否会伊斯兰化,实际上可以用美国来作为参考。美国是个不折不扣的多元文化社会,两百年来,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不断变化,总体趋势持开放宽容态度,保证少数族裔权利。黑人和西班牙裔人口对美国政治和文化影响越来越大。如果你认为美国建国之初白人统治就是“美国”的话,那么今天美国恐怕早已被“黑人化”了,加州已经“西班牙化”了。但美国不是,她就是在不断发展,平等改革愈发深入,形成新的文化,但这种文化还是“美国文化”——基于对平等、自由的认识的文化。各个族群在这个文化里有了话语权,但没有出现“XX化”。
从这个角度看,极端分子在欧洲造成的影响极其负面,让人们有担忧有排斥。但这可能正是人类历史过程的常态。《查理周刊》血案,是这个过程中不快的一笔。
【一财网首发 转载请注明来源】

瑞银全球央行调查:滞涨压力不容忽视,对美联储独立性感到担忧
资产配置多元化升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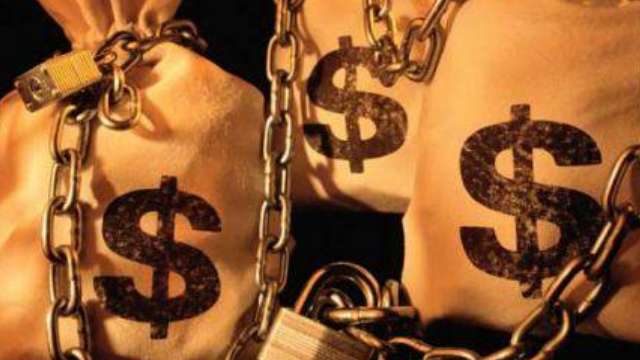
关税和经济衰退担忧下,美国人正在“报复性储蓄”?
部分美国消费者可能正在从所谓的“报复性消费”转向“报复性储蓄”。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美国必须等待严厉的惩罚,并表示将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

欧洲赴美游人数锐减,特朗普政府政策“劝退”欧洲旅客
美国国家旅游办公室的数据显示,5月从丹麦、德国和法国前往美国的旅客量分别下降20%、19%和9%。

筛查留学生“网络足迹”?美国政府升级留学生签证审查,教育界担忧
美国国务院建议适当缩减学生及交流访问学者签证的受理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