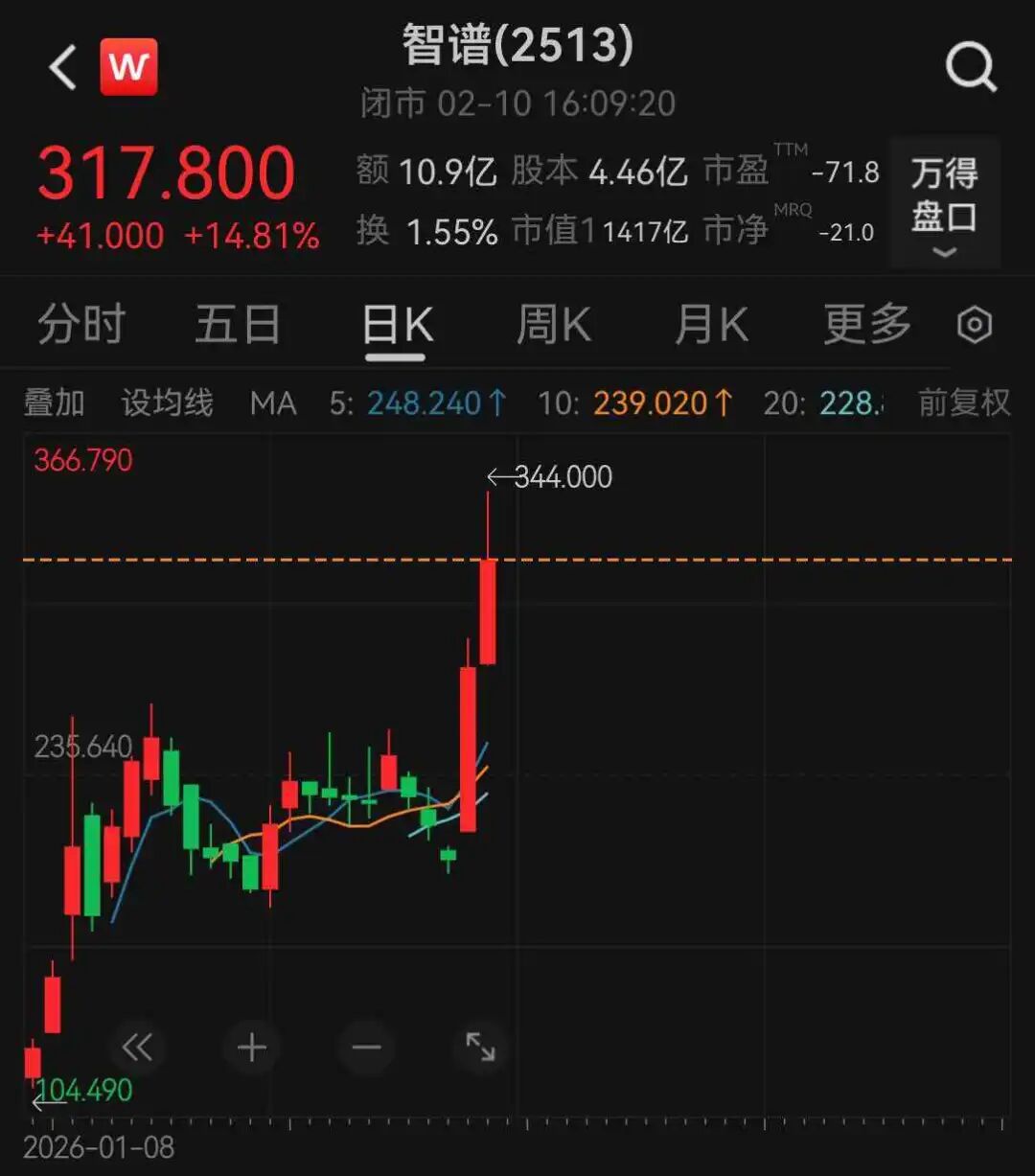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aisd}}
AI生成 免责声明
巴拉杰依的猎民点里有一个神灵“笼头神”,彩色的鹿皮带子,戴在驯鹿头上很美丽(摄影/王晓东)
学者孟慧英研究北方地区萨满30多年,总是忘不了见到萨满妞拉那个夏天。那时,她的生命进入倒计时,完全不能自理,但眼睛异常清澈发亮,泛着淡蓝色的光。第一次对视时,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与人类学研究所教授也发颤了,“我心里就在想,老萨满好厉害!”
使鹿鄂温克信仰东正教和萨满教。他们把萨满称为“沙利”(知者),是能与祖先、神灵对话的人。1997年7月,部落最后一位萨满妞拉去世,带走一个神秘的时代。
几年后,她的族人被现代化生活浸染,年轻人大多远离驯鹿和森林,老者也在快速凋零。目前,公认熟悉部落历史和传统生活的老人可能不会超过三位,分别是最后的家族部落长玛利亚•索,最后的桦皮船制作者安塔•布,还有妞拉74岁的女儿巴拉杰依。她被内蒙古自治区授予“鄂温克族萨满服饰与器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但实际上,除了母亲的相片,巴拉杰依并没有太多和萨满相关的东西。
2012年,巴拉杰依患上宫颈癌后更加想念母亲。从前他们认为,触犯神灵就会犯病。妞拉去世后,再也没有人穿上那件由驯鹿皮和铁片做成的神服,在漆黑的夜晚敲起神鼓招魂。巴拉杰依把对母亲和往事的思念写下来,她担心很多事情不写,以后也没有人知道了。近日,巴拉杰依的自传体小说《驯鹿角上的彩带》在网友众筹下出版。
巴拉杰依(左)和孙子雨果 (摄影/王晓东)
她得“萨满病”了
萨满教是北方少数民族共有的一种原始宗教,相信万物有灵。萨满在通古斯语言中,是极度兴奋、激动不安和疯狂的人。只有得“萨满病”、并得到别的萨满认可,才能成为与神联系的萨满。
使鹿鄂温克萨满和其他民族萨满一样,靠神灵附体得到信息。萨满世代相传,一般是老萨满去世两、三年后才出新萨满。妞拉的哥哥是萨满,没学成就去世。14岁时,她出现异于常人的行为,有时精神失常,有时一睡就是三天三夜,有时光着脚在雪地上跑也不怕冷。
族人们都说,妞拉得“萨满病”啦,只有当萨满才能好。妞拉父亲养育了12个孩子,只有最小的妞拉幸存下来。他一心想保住她,两年后,聘请大萨满教习她各项本领。
后来,妞拉果然成为使鹿鄂温克公认的四位大萨满之一,用不同的“瑟温”(神灵)给族人招魂治病,祈求丰收,还为死者送魂。巴拉杰依记得,小时候只要见有人恭恭敬敬来到他们撮罗子,把毛巾往白桦树杆上一搭,就知道他们家出事了。孩子们自觉去帮妞拉采回一种萨满仪式上需要的达子香花。
现在,根河市使鹿鄂温克博物馆里,还收藏着两件妞拉使用过的神器。1960年代,妞拉用来装过侄女德克莎的“乌麦”。萨满认为,“乌麦”是孩子的灵魂,离开身体就会生病,要到另外一个世界求“乌麦”回来,孩子才能健康成长。
“那时我大概只有四五个月,病得很严重。”德克莎回忆,“后来大姑说治得好,但要取个鸟儿的名字。”鄂温克语中,德克莎是漂亮神鸟的意思。
87岁的孟和老人曾经做过鄂温克民族乡当党委书记,如今在呼伦贝尔市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颐养天年。他也见过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大兴安岭里,妞拉给族人跳神治病。先杀一黑一白两只驯鹿祭神,把心、肝、肺、食道、头等放在祭祀架上,头朝着日出方向。驯鹿带着萨满的灵魂去见神灵,神灵下界后也再骑着两只鹿灵魂附体。求神活动在夜间进行,火光全部熄灭。黑暗中,鼓声咚咚咚,神衣叮叮叮。跳跃狂舞的妞拉还会进入一种癫狂状态,说着只有萨满才懂的神秘语言,整个场面惊心动魄。
熟悉妞拉的人还说,她也是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妮浩萨满的原型。小说中,妮浩萨满知道每救活一个孩子,就必须用另一个孩子去替代。但她依然唱起神歌救人,又亲手把自己死掉的孩子装到白布口袋里。现实中,妞拉的人生经历也同样跌宕离奇。她生育了12个孩子,7个儿子全部夭折,只有5个女儿长大成人。“所以萨满地位非常高,非常受人尊敬。”孟和感慨。
妞拉,最后的萨满旧照 孟和供图
妞拉在跳神 孟和供图
神服卖了5万
妞拉最后一次跳神已是80岁。为了感谢孟和帮她要回文革时被拿走的神服,萨满仪式以给氏族成员和驯鹿祈福的名义举行。
在孟和保存的录像中,身材佝偻的妞拉穿上神服时,整个人被压得仿佛要埋了起来。敲击神鼓的力度变小了,步伐也不复轻盈。但跳神舞时坚持站立,后面就一直有个族人在帮她提着神服,“她也知道是最后一次穿萨满服了,特别认真。”
那次跳神活动快要结束时,妞拉轻轻敲着神鼓告诉神灵,她年事已高,请求神灵收回,“恳请神!恳请族众!随我心愿吧!”后来,妞拉把神鼓交给族弟拉吉米。神鼓是萨满与神灵交流的工具,意味着拉吉米就是氏族下一任萨满。“但当时拉吉米已经五十多岁,年纪大了体力有限,萨满一般是十多岁开始培养。”孟慧英说,而且拉吉米没有经受过3年萨满教仪式训练,也没有举行过领神仪式,并不具备当萨满的资格。
91岁的妞拉去世后,萨满就在使鹿鄂温克中消失了。
“萨满文明没有太过超越性的层面。工具性很强,自然也比较容易消失。”孟慧英解释,萨满教应对的是普遍的人性领域,体现原始社会人类解决那些让人迷茫、焦虑、关心、不时遭遇不确定性的一种努力和能力,希望得到安慰。
孟和也认为,当族人认识自然的能力增加了,萨满教依赖自然界所产生的根源就逐渐被突破,自然也走向消亡。他举例说,18世纪初,使鹿鄂温克迁到中国境内时有300多人,到1957年民族乡成立时仅剩136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森林中条件太差,根本没有医生和药物。解放后,医疗队上山,用现代医疗手段救治和预防了长期困扰族人的结核病。此后,生病向萨满求助的人就越来越少。
“我是不太信的,毕竟她是个人不是神。得病后该好的还是好,该死的还是死。”在阿龙山镇一片原始森林里,大部分时间都得趟着的巴拉杰依也说。她10岁下山上学,中专毕业后在乡卫生院工作到退休。
在孟慧英看来,妞拉萨满留给后世最宝贵的财产是她的神服。那年春天,布谷鸟鸣叫过后,九位妇人、五名铁匠就开始缝制,一直到秋天白桦树掉叶子才停工。三年后妞拉学满归来,神服也终于做成。整套神衣神帽用柔软的鹿皮缝成,胸前挂象征灵魂的铜镜,身上有60多件代表月亮神、天神鹅、启明星神,以及象征人类器官的神偶铜片,是使鹿鄂温克对神灵和自然崇拜、敬畏的象征。
文革时,部落其他三位萨满的神服都被拆毁丢掉了。妞拉不愿交出去,和丈夫翻山越岭,悄悄藏到大兴安岭深处一个老猎场。“这套神服引起很多研究者的兴趣,可惜里面的很多秘密已经被妞拉带走了。”
神服如今去了哪里?巴拉杰依淡淡地说,后来她身体不好,把母亲的萨满服卖给根河市文物馆了,“卖了5万块钱。那时我没办法,需要钱。”
巴拉杰依猎民点上,后辈们用板车将山泉拉回家(摄影/王晓东)
鄂温克最后的萨满?
多年后,敖乡人再提及妞拉,更像是谈起某个传说中的人物。他们都说起她去世那天的情景,午后大兴安岭突然狂风暴雨大作,松树被掀翻,有驯鹿被拍死,“那时我真的害怕了。”巴拉杰依说。曾孙雨果也用夸张的手势比划着,“听说她会飞起来。”他小时候调皮,被妞拉用神鼓打过头。
年岁渐长,巴拉杰依对母亲的思念也与日俱增,“她不跳神时很开朗。我四妹妹和她长得一模一样。”她遗憾地说,如今除了老年人还相信萨满,崇拜传统的神,族人对神灵信仰变淡了,“孩子们都认为要上学,有文化,都不喜欢那些了。”
巴拉杰依的猎民点里还有一个神灵“笼头神”,彩色的鹿皮带子,戴在驯鹿头上很美丽。去年冬天,驯鹿得瘟疫死了20多头, 她祈求“笼头神”保佑鹿群壮大。
史书典籍中,北方居住过的古代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回鹘、女真等,都是古代萨满教的信仰者,萨满在中国历史文化中起了很大作用。但文革时,很多地方的萨满都被打倒,萨满教普遍进入衰落阶段。1980年代,孟慧英走遍了呼伦贝尔和大兴安岭,始终没找到仍在出马的萨满。
2000年以后,中国学术界出现萨满教研究热,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等领域学者纷纷介入,带动文化界和政府的关注,萨满文化又开始活跃。现在,一些地方敖包祭祀式,萨满定期举办法会的“奥米南”还吸引不少游客参观。
在一部讲述使鹿鄂温克历史的《敖鲁古雅》舞台剧中,也出现了萨满舞、萨满教中的祭熊、祭火神。不过在孟慧英看来,热闹只是地方政府与萨满文化的某种偶合罢了,“实际上你在那些地方多呆呆,就知道他们到底信不信。”
孟慧英也去过敖鲁古雅乡,这里早已不是妞拉的时代。小镇街道平坦,房屋整齐,乡村医院近在咫尺。见到鄂温克族乡长时,他正在为发展民俗旅游村操心。孟慧英总觉得,不应该只为消逝的文化唱挽歌,还得做点什么。国际有识之士普遍都把高度尊重地方传统和文化多元性的全球共同体,当作全球化的理性追求,提倡全球共生论。“不同的利益也可以结合在一起,以实现整体利益。差异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孟慧英说。
她也不愿轻易将妞拉列为使鹿鄂温克最后的萨满,“萨满究竟有没有还得看族人,神想来,谁也拦不住。为什么以前北方少数民族没有萨满,现在出来了几百个?最关键的不是萨满有没有,而是族人对信仰保持多少真诚。”
妞拉的后人最近一次看到她是在梦里,她穿着萨满服,和族里老人手拉手围着火塘转。撮罗子外,星光灿烂。
巴拉杰伊家饲养的驯鹿,割掉了鹿角(摄影/吴军)
阿龙山猎民点,巴拉杰伊家(摄影/吴军)
如需获得授权请联系第一财经版权部:banquan@yica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