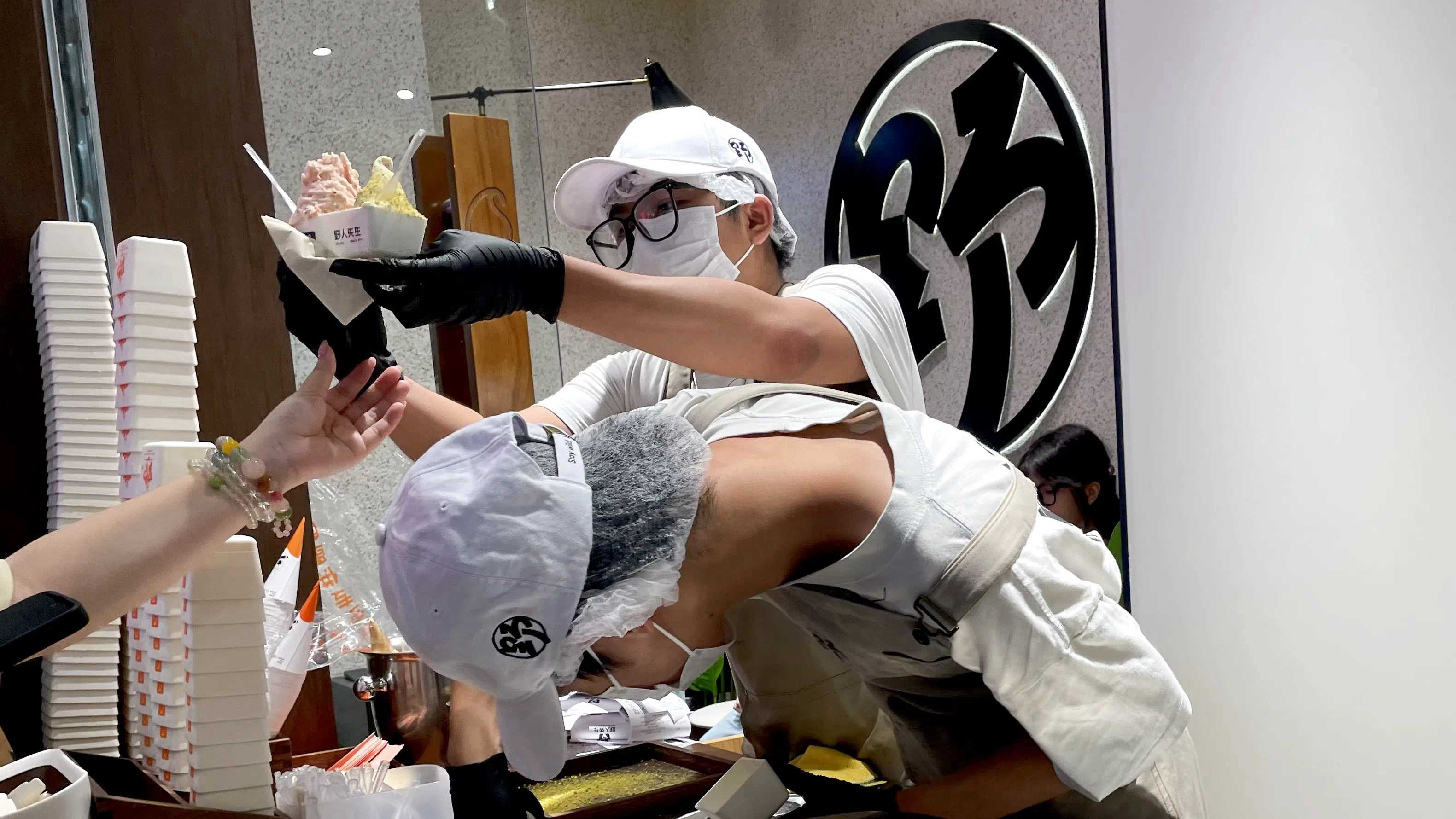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见字如面》现场,张国立读左权写给刘志兰的信
96岁翻译家许渊冲做客《朗读者》圈粉无数
王小波在与李银河的一封书信中写道:“人世间有一种庸俗势力的大合唱,谁一旦对它屈服,就永远沉沦了。“这封信被拿到《见字如面》上,由何冰演绎出来,在网上传开了。节目“拆信人”,香港岭南大学教授许子东这样解读:“这个‘庸俗势力的大合唱’可能是文化的、可能是金钱的,可能是买房子,也可能是综艺节目。“
自2013年《爸爸去哪儿》后,综艺节目陷入了“大合唱”式的喧嚣。跟风兴起的明星竞技类真人秀充斥荧屏,拼资本、拼咖位、拼话题,结果是同质化严重,原创力匮乏。最近,这样的局面似乎有了扭转的迹象,综艺“清流”接二连三地刷了屏。先是《见字如面》,曹禺和黄永玉之间肝胆相照的书信往来,经由张国立和王耀庆的演绎,引发朋友圈的转发热潮。紧接着是霸屏春节长假的《中国诗词大会》,17岁女中学生武亦姝博闻强识,引发多轮讨论。随后,央视主播董卿从《诗词大会》走进《朗读者》,邀名流读书,把96岁的翻译家许渊冲推上网络热搜。一时间,原本被边缘化的综艺类型,风头甚至盖过明星扎堆的真人秀。
二十年前,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吕新雨去台湾地区访问,发现那里的综艺节目非常糟糕,靠不断挑战社会底线来赚取收视率。“当时就觉得大陆的媒体改革不能走这个路。结果,我们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她看来,综艺节目的唯市场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低俗化,不仅与大学、学术界、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人文传统日益分离,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也产生了无法弥补的断裂。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回归是大势所趋:“这三档节目是应运而生,它回归了社会主流价值观,这个主流价值观包含了对人的命运的关注,不管是不是名人,都被放在了普通人的位置上。”
文学是所有艺术的根
“清流”综艺的出现被视为对过去电视节目纯娱乐倾向的一种反抗,而在《见字如面》的总导演关正文看来,所有的精神产品都有娱乐属性,只不过,一种是感官层级的快乐,另一种则是精神层面的愉悦:“如果说人在感官层面上的快乐有点像肌肤之亲,那么人在精神上的快乐就像爱情。精神生活所带来的愉悦,远远超过感官的浅层快乐,能给观众带来更大的满足。”
因此,节目刚起步,关正文就笃定它能在市场上找到自己的观众。他认为,所谓大数据划出了传播的舒适区,不但限定了产品的样式,也描绘了互联网受众的样貌,数亿人都被“没文化”了。他把节目方案带到腾讯,所有人都说好,但也避免不了对大众化前景的担心。在没有广告商赞助的情况下,《见字如面》“裸奔”上线。但事实证明:“市场是个好东西。”第一期合集视频网站点击量已经突破了4000万。一夜之间,人们都在谈论它。
熟悉关正文此前的经历,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执意将《见字如面》带到观众面前。他曾是《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的原创著作权人和总导演,这些项目几乎都是同期竞品中的异数。在跨入电视行业之前,八十年代初,中国文学最活跃的时期,关正文在作家协会当编辑,参与出版了北岛、舒婷、顾城的诗选,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等文学作品。他告诉第一财经:“我分别经历了文学和电视最繁荣的时代,文学是所有艺术的根,离不开。”
何冰与林更新登台《见字如面》
3月16日的那一期《见字如面》选了顾城的书信:四封他与妻子谢烨的情书,一封是他的遗书,节目安排王耀庆先读遗书,再由徐涛和蒋勤勤演绎情书。这样的安排出自关正文:“从故事的终点走向起点,是想告诉人们,虽然它有一个惨痛的结局,但也有一个最美好的开始。”
1993年10月8日,新西兰北部的激流岛,诗人顾城用斧头砍伤妻子谢烨,而后自缢于一棵大树之下。作为朦胧诗的代表人物之一,顾城是文学史绕不开的名字,而悲剧的终结,因其扑朔迷离的过程,有了各式各样的揣测。“没有人会忽略他诗歌的美感,也没有人能够宽容他后来的行为,但是我觉得,八卦的有效期已经过去了,我们能做的是,如何接近一个更真实的人,从他的生命历程中得到一些启示。”
关正文和顾城、谢烨曾是交往密切的朋友,节目录制现场,57岁的他忍不住唏嘘落泪:“那天我在家里看见顾城送给我的画,这么多年过去,忽然想起,物是人非,非常难过,非常想念。”
这几封信对于关正文而言意义特殊,但选择它们的标准和其他信件并无二致:“具有公共传播价值,值得被更多人读到,并且直指人心”。 历时一年多,节目组遍访博物馆、档案馆、资料馆,邀收藏家、文化名人提供书信的来源,从上万封信件中,精选出一百封,分别交予归亚蕾、张国立、何冰、王耀庆等八位读信人。纸上文字经由声音的演绎,重塑了生命。这些戏骨撑起《见字如面》的金字招牌,靠的是打磨多年的台词功底和演绎能力,而非人气或是颜值。
一个人、一张桌子、一封信、一段往事。观众跟随读信人,穿越到鲜为人知的历史瞬间,感知时代洪流中的悲欢离合。正如黄永玉写给曹禺的信中写道的:“人到底太少接触纯真的感情了”。书信因其文体的日常化与私密性,天然具备这样的真诚。在秦军将士黑夫的家书中,抗日将领左权的绝笔中,读到的是赤子之心与家国情怀;陈寅恪与傅斯年,郁达夫与沈从文的来信里,闪耀着的是知识分子的良心与品格;徐志摩与陆小曼,冯亦代与黄宗英的情书,字里行间是爱侣间的情真意切。写信的人,或是读信的人,无论是否名人,都摘去光环,还原为一个普通人。人们得以从那些历史的尘埃中,读懂人心,也看清自己。
一前一后相继推出的《见字如面》和《朗读者》常被拿来一起讨论,在关正文看来,这是两档风格迥异的节目:“各有各的兴趣,各有各的观众,各有各的资源,差别非常大。但多样性的生态中是没有高下之分的。”他肯定了“对手”存在的必要性:“如果一条街上只有一个饭馆,这个饭馆非饿死不可。如果这条街是饭馆一条街,那就最好了,大家都能活下来。”
关正文向第一财经透露,《见字如面》第二季已在筹备之中。除此之外,他们将很快推出一档全新形态的读书节目,这个想法已经在他心中盘旋了很久,听上去他对这档正在孵化中的节目相当自信:“当初困扰我的核心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
“给走夜道儿的人照个亮儿”
即使背靠央视,《朗读者》找投资也并非像外界想的那么一帆风顺,过去一年,制作人董卿带着《朗读者》的理念参加了多次面向广告商的节目推介会,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迟迟没有动静。直到今年1月才找到了赞助商,紧锣密鼓地录制播出,
即使背靠央视,《朗读者》找投资也并不顺利
《朗读者》的舞美请到了世界一流的团队,铁凝、王蒙、余秋雨和冯骥才是文学顾问,幕后班底着实强大。节目嘉宾大多是也是名流,偶尔也会有素人参与。最新一期请到的演员王学圻,作家刘震云,京剧名角王珮瑜,天才棋手柯洁,作曲家许镜清,航天英雄杨利伟。每一位都是响当当的人物。节目中,王珮瑜用京剧韵白朗诵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举手投足尽是潇洒。加之董卿娴熟的控场能力和主持技巧,一档节目下来行云流水,自然流畅,常有动人处,惹人泪下。
耐人寻味的是,《见字如面》和《朗读者》最初都在豆瓣网上获得了9.4的高分,随着节目的推进,它们的评分都有不同程度地下降。关于《见字如面》,批评声集中在主持人和女嘉宾身上,或是对一些读信人的演绎感到失望:“浮夸”、“戏过了”,为了让节目显得更通俗,关正文把文言文的书信翻成白话文,不少观众却希望原文照搬。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副教授吴畅畅一直追看这两档综艺节目,他对于《见字如面》的直观感受是太过“精致”,门槛高,其中一些民国书信让他联想到许鞍华的《黄金时代》:“这种风格特别对某些人的趣味,但不会是大众的文化趣味。电视是一个大众文化,讲究形象大过于讲究声音,视觉文化不太利于传递很深刻的思想。”
《朗读者》遭受的非议则更多。第一期中,董卿和濮存昕对话时,将老舍的名字读成第四声,就引发不小争议。中国老舍研究会官方微博当晚更正:“濮存昕先生将老舍先生的读音念错了,老舍的舍字读三声,舍弃,舍我的意思。”
带着文学诉求来看节目的观众也感到困惑。他们发现,在这档以朗读为名的节目中,故事成了主角,阅读则是点缀。有豆瓣网友统计,节目中真正用于嘉宾朗读的时间仅为节目总长度的四分之一,其余皆为情感对话:”这不是朗读版《艺术人生》或者《感动中国》吗?“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文学与传播系副教授康斌看了几期《朗读者》,也几度被嘉宾们的故事所打动,尤其是许渊冲老先生读林徽因的诗那一段,红了眼眶。然而,他并不认为这是一档读书节目:“它像什么呢?因为要表达某种情感,所以要选择相应的作品来配合它。它的目的不在于引领阅读,而在于精神抚慰或者情感宣泄。他为主流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很好的样板,把慈悲、感恩、爱、责任感等美好品质,用一种比较委婉的方式表现了出来。”
《朗读者》中,与亲情相关的故事分享或是朗读选段,往往能瞬间击中观众的泪腺。当世界小姐张梓琳为女儿读《愿你慢慢长大》,自然流露的母爱美好而真挚:“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作家麦家讲述父子三代人之间隔阂与疏离,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普通的父亲,如何包容和试图接近青春期叛逆的儿子:“到此为止,我不想你,也希望你别想家。如果实在想了,就读本书吧。”徐静蕾读史铁生的《奶奶的星星》,讲人世间最温暖最遥远的守护:“人死了,就变成一个星星。给走夜道儿的人照个亮儿。”
吴畅畅印象最深的是郑渊洁与86岁的父亲郑洪升一同朗读童话故事《父与子》。他认为,朗读以知为名,最重要的还是情感,它能够呼应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中,因为不同的教育,不同的出身所导致的不同的情感结构。在他看来,当下是高度流动的社会,利用空间的距离感,打“亲情牌”尤其能够成为高效的动员方式。“电视的煽情是一种有力的吸引观众的手段,但是用多了也会麻木,观众继而产生免疫力,就会转移。”
在明星天价薪酬横行、进口综艺模式引进受限的环境,《朗读者》、《见字如面》的出现提供了一种新鲜而不失态度的综艺形式,尽管有诸多瑕疵,因其对人文精神的诉求,诞生之初就被人们寄予改善国民阅读生态的厚望。此前,有评论者断言,我国国民疲于奔命,为物质殚精竭虑,根本无暇顾及所谓的阅读生活。在吕新雨看来,情况恰恰相反,正因为太疲于奔命了,精神层面的缺失已经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你看到社会中,大量的精神问题,大量的抑郁症,高自杀率、校园暴力,这个背后恰恰是这个社会对意义的饥渴。”读书本身是一个寻求意义的过程,大众传媒中,寻求意义的过程变成节目来讨论、来引领,而不是简单给出答案。她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寻求意义的历程,我们通过分享对意义的追寻,分享心灵的困惑、人生的艰难困苦,使得意义的追求变成一个寻求对话、寻求共识的过程。这就是有意义的。”
专访吕新雨:回归平实,回归健康的市场
第一财经:您怎样看待《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见字如面》这些文化类节目的走红?
吕新雨:首先,这标志着中国综艺类节目的风头终于开始转向了。它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现象级,是逆势回归的新现象,是好事。其实,综艺节目在原有的市场逻辑下早已经穷途末路,由于把收视率都压在明星身上,对明星的抢拼导致综艺节目的成本不断地攀升,攀升到令人咋舌的程度。少数“颜值”明星从综艺节目中获得的巨额收入既严重违背社会公正,扭曲社会价值,形成劳动价值严重的不对称,也使自己成为被消费的对象。这个恶性市场化模式其实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无以为继的程度。物极必反,这与国家文化政策的转向也有关系,现在是触底反弹。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它们是值得关注的。
综艺节目的唯市场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低俗化,不仅与大学、学术界、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人文传统日益分离,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也产生了无法弥补的断裂。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回归是大势所趋。节目对人的情感与人文的结合、对传统和历史的重新阐释,都做得不错,耳目一新,虽然并不完美。但节目回到了对社会价值观的重建上,就是一种拨乱反正。
回归到电视媒体最朴素的意义,大众传媒的原点,即作为社会交往和沟通的功能。不再是才艺、唱歌之类旨在形式上耍花样,不走心,不走脑,依靠所谓IP、粉丝的非理性消费,而是回到语言的交流上。用朗读的方式去阅读,回到文字,回到文学,回到书籍,回到中国人的诗歌传统,也就是用中国人最普通、最本真、最传统的方式去沟通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历史,这样的沟通本来应该是大众传媒承担的责任。这些在过去综艺节目里,已经严重缺失了,而且大家对这种缺失不以为怪,习以为常。在去年电视业断崖式下跌之后,电视只有迎合年轻人才能赢得市场的神话也破灭了。电视通过阅读的方式回归传统、回归人文、回归社会的知识积累和主流价值观,既是突围,也是物极必反。在省级卫视大战中被动挨打的央视,现在终于开始摸索着找到自己的位置了。而《见字如面》来自被视为三线卫视的黑龙江电视台的小成本制作,也意味着新的洗牌,以及新的可能。大势已变。
第一财经:同样是人与人的沟通,它们与《感动中国》、《艺术人生》这样的节目有什么区别?
吕新雨:以前的那种为感动而感动,容易走向偏执和形式主义,走向窥视和猎奇,走向对明星和权力的崇拜,以及对资本的追捧。现在这些节目返璞归真,不管你是不是明星,都要回到最本真的人的感情,回到“低”位置,这个位置是可以和社会平等交流的。这个过程中,以人文素养为评判标准,而不是以既有的社会地位为评判标准。明显也要通过自己的讲述让大家重新认识你,这种讲述不再是猎奇式,或炫耀性,而需要在公众面前去展示人文素养,让人文素养形成社会共识的基础。
第一财经:这些节目在观众层面也产生了良好的反响,是否意味着他们的诞生顺应了观众的某种精神需求呢?
吕新雨:这就涉及如何去理解市场。我们被市场的怪圈所挟裹,所有人都陷入其中无法自拔。在赢者通吃的市场逻辑下,省级卫视为了争夺头筹,互相血拼。做现象级娱乐节目是死,不做,更是死。现在这些节目回归平实,重新寻找观众的诉求,恰恰是回归了健康的市场。它证明这个社会并非不需要好的节目,不需要温暖人心的、有人文素质的节目,而是我们自己制造了恶质的市场,却以为只有这样才叫市场。就像总有人把迎合低级趣味的软色情、非理性叫做人性,我们往往把那种东西叫做市场。人除了有肉体的生理性,还有精神性,有对意义的需要,这本来不是问题,但是在综艺节目的血拼中,却成了问题。除了消费主义的价值观,什么都不剩,一个社会如何能够长久容忍主流媒体这种现象?起码,这些节目的出现,表明健康的市场是可能的,也是值得追求的。满足人民不断增加的文化精神生活的需求,才是正途。
第一财经:电视综艺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引领观众走向阅读生活呢?
以前的明星节目从来没有往读书这个层面上走。现在这些节目在重新界定名人,不管是什么样的名人,把名人和书做一个建构,起码对整个社会的读书风气和思考,或者是阅读风气的形成是有好处的。节目不再走向小鲜肉,不再靠颜值,不再是一种表面的东西,而在于你的人生经历,作为一个有深度的存在的人,你的阅读和表达。从这个角度来讲,起码对明星类节目风气的改变是有好处的,对明星来讲也有好处,不再是消耗性地消费明星,对明星也是一种尊重。
如需获得授权请联系第一财经版权部:banquan@yica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