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科学技术的发展将颠覆我们很多当下认为无需佐证的“常识”,比如人文主义所推崇的自由意志将面临严峻挑战,机器将会代替人类做出更明智的选择。更重要的,当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日益成熟,人类将面临着从进化到智人以来最大的一次改变,绝大部分人将沦为“无价值的群体”,只有少部分人能进化成特质发生改变的 “神人”。
未来,人类将面临着三大问题:生物本身就是算法,生命是不断处理数据的过程;意识与智能的分离;拥有大数据积累的外部环境将比我们自己更了解自己。如何看待这三大问题,以及如何采取应对措施,将直接影响着人类未来的发展。
新锐历史学家、《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的这部《未来简史》,正是解读这一进程的既震撼人心又趣味盎然的作品。第一财经阅读周刊节选书中部分内容,与读者分享。
《未来简史》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 著 林俊宏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7年1月
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的故事〈一个问题〉(A Problem)正是以叙事自我做为重点。故事的主人翁是唐吉诃德(Don Quixote),与塞万提斯(Miguel Cervantes)著名小说的主角同名。唐吉诃德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想象世界,自己是里面的传奇骑士,四处对抗巨人,拯救托波索的杜尔西内亚(Dulcinea del Toboso)女士。而实际上,唐吉诃德本名叫做阿隆索.吉哈诺(Alonso Quijano),是乡下一位上了年纪的没落贵族;那位高贵的杜尔西内亚女士,是附近村子里一个养猪的村姑;至于巨人,则是一些风车。波赫士就在想,如果唐吉诃德因为相信这些幻想,攻击、杀死了一个真正的人,后续会如何?波赫士提出了关于人类的一个根本问题:如果叙事自我讲出的那套故事,对我们自己或周围的人造成严重伤害,之后会怎样?波赫士认为,主要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没什么影响。虽然唐吉诃德杀了一个真正的人,却毫无悔意。因为这些妄想已经太过鲜明,他一心认为自己在对抗风车巨人,根本无法意识到实际杀了人。第二种可能:在夺走他人生命那一刻,会让唐吉诃德大受惊骇,打破他的妄想。这种情况类似于初上战场的新兵,原本深信为国捐躯是件好事,最后却被战场现实狠狠打醒。
另外还有更为复杂和深远的第三种可能:原本与想象的巨人战斗时,唐吉诃德只是在演戏。但等到真的杀了人,他就会开始坚持他的妄想,因为只有这样,他不幸犯下的错误才会有意义。荒谬的是,我们对一个想象故事做出的牺牲愈多,就可能愈是坚持,只为了让我们的一切牺牲和痛苦有意义。
在政治里,这称为“我们的孩子不能白白牺牲”(Our Boys Didn’t Die in Vain)症候群。1915年,意大利加入协约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参战。意大利宣告的目标是要“解放”由奥匈帝国“不当”占有的特伦托(Trento)和提里雅斯特(Trieste)这两处“意大利领土”。意大利政客在国会里发表义愤填膺的演说,誓言要补正历史的错误、恢复古罗马的光荣。数十万意大利士兵开往前线,高喊“为了特伦托和提里雅斯特!”以为这两地唾手可得。
情况大出意料。奥匈帝国的军队在伊索佐河(Isonzo River)沿岸组织了强大的防线。意大利总共发动了十一次血淋淋的战役,最多只攻下几公里,从未有真正突破。第一场战役,他们失去了15000人。第二场战役,他们失去了4万人。第三场战役,他们失去了6万人。就这样持续了腥风血雨的两年,直到第十一场战役。但接着,奥地利人终于反击了,这第十二场战役一般称为卡波雷托战役(Battle of Caporetto),德奥大败意大利,一路杀到威尼斯门口。光荣出征成了一片血海的溃败。等到战争结束,意大利士兵死亡人数达70万,伤兵人数超过百万。
几位在伊索佐战役的受害者。他们是白白牺牲吗?
输掉第一场伊索佐河战役后,意大利政客有两种选择。他们本来大可承认自己犯了错,要求签署和平条约。奥匈帝国根本和意大利无怨无仇,又正在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和更强大的俄罗斯打个焦头烂额,必然乐意讲和。然而,这些政客怎么能面对这15000位意大利士兵的父母、妻子和孩子,告诉他们:“对不起,出了一点错,你家的乔望尼白死了,还有你家的马克也是,希望你们别太难过。”另一种选择,这些政客可以说:“乔望尼和马克是英雄!他们的死,是为了让提里雅斯特回归意大利,他们的血不能白流!我们会继续战斗,直到胜利为止!”毫不意外,政客挑了第二个选项。因此他们打了第二场战役,又失去了4万人。政客再次决定,最好继续战斗,因为“我们的孩子不能白白牺牲”。
但我们也不能只怪政客,就连群众对战争也是一路支持。就算到了战后,意大利未能得到自己要求的所有领土,意大利人民透过民主,选出的就是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和他的法西斯伙伴们,这些人的选举要求正是要为所有意大利人的牺牲取得适当的赔偿。讲到要承认一切是白白牺牲,政客要对这些人的父母开口已经够难,但父母要对自己承认还要更为困难,而在其中受害的人更是不在话下。失去双腿的残废士兵,会宁愿告诉自己“我的牺牲,都是为了能让意大利民族永存的荣光”,而不是“我之所以没了腿,是因为蠢到相信自私的政客”。活在幻想里是一个远远较为轻松的选项,唯有这样,才能让一切痛苦有了意义。
早在几千年前,神职人员就已经发现了这种原则,许多宗教仪式和诫命都以此为基础。如果想让人相信某些假想实体,像是神、或是国家,就要让他们牺牲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牺牲叫人愈痛苦,他们就愈会相信牺牲奉献的对象确实存在。如果有个贫穷的农民,把自己一头珍贵的牛都献给了宙斯,就会开始对宙斯的存在深信不疑,否则要怎么解释自己竟然蠢成这样?这个农民还会再献出一头、一头、再一头,才不用承认以前所有的牛都是白白牺牲……
经济上也会看到同样的逻辑。1999年,苏格兰决定盖一座新的国会大厦。原本预计施工时间两年,预算四千万英镑。但到头来,施工时间长达五年,成本高达4亿英镑。每当承包商遇到未预期的困难和费用,就会找上苏格兰政府,要求工期展延、增加预算。而每次发生这种情况,政府就会对自己说:“我们已经投入几千万英镑,如果现在停手,只能拿到一个盖到一半的骨架,在人民心中会彻底信用扫地。还是再拨个四千万英镑吧。”再过几个月,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但这时候,建物无法完工的压力也更大了。再过几个月,故事继续重复,就这样下去,直到实际成本足足是原来估计的十倍。
苏格兰国会大厦。我们的英镑不能白白牺牲
不是只有政府会陷入这个陷阱。企业集团也常常把几百万美金丢进失败的子企业,至于个人,也常常依恋着不开心的婚姻、没前途的工作。我们的叙事自我宁可在未来继续痛苦,也不想承认过去的痛苦完全没有意义。最后,如果我们想把过去的错误一笔勾销,叙事自我就一定得在情节中安排某个转折,为错误注入意义。例如,一个和平主义的退伍军人可能告诉自己:“确实,我犯了个错,才没了双腿。但因为这个错,我才看清战争是个地狱;从现在开始,我要奉献我的生命、为和平而战。因此,我受到的伤还是有些正面意义:让我学会重视和平。”
于是我们知道,“自我”也像国家、神祗和金钱一样,都只是个虚构想象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个复杂的系统,会丢下我们大部分的经验,只精挑细选留下几样,再与我们看过的电影、读过的小说、听过的演讲、做过的白日梦全部混和在一起,编织出一个看似一致连贯的故事,告诉我们自己是谁、来自哪里、又要去哪里。正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自己该爱谁、讨厌谁、该怎么对待自己。而如果情节需要,这个故事甚至也可能让我们牺牲自己的生命。每个人的故事都各有文类。有些人活在悲剧之中,有些人上演着永止境的宗教戏剧,有些人的日子过得像是部动作片,也有不少人过着喜剧人生。但到头来,一切就是故事罢了。
这样说的话,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自由主义认为,我们不应期待外界为我们提供现成的意义。每位个别选民、顾客和观者,都应该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创造意义,而且不只是自己生命的意义、更是整个宇宙的意义。
但生命科学却戳破了自由主义的想法,认为所谓的“自由个人”也是个虚构故事,人只是生化算法的组合。每时每刻,大脑的生化机制都会创造经验,但一闪即逝,接着就是更多经验闪现、消失、闪现、消失,彼此快速相连。这些瞬间的经验并不会累积构成什么永续的本质。而在这一片混乱中,叙事自我试着找出秩序,于是编织出一则永无止境的故事,让每项经验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就多少有些长久的意义。只不过,虽然这让一切合理且诱人,却仍然只是虚构故事。中世纪的十字军相信是上帝和天堂让他们的生命有意义;现代自由主义者则认为是个人自由选择让生活有意义。但不论如何,都一样是妄想。
当然,早已有人质疑自由意志和个人的概念。早在两千多年前,印度、中国和希腊的思想家就已经认为个人概念是一种虚妄。然而,除非真正能影响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否则光是怀疑,并不足以改变历史。人类很能应付认知上的矛盾,能允许自己在实验室里信一套,到了法庭或国会又信完全不同的一套。就像是基督教并未在达尔文发表《物种原始》的那天消失,自由主义也不会因为科学家结论认为并没有自由个人便就此灭亡。
事实上,就连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和其他新科学世界观拥护者,也并未放弃自由主义。就算他们已经用丰富的学理、数百页的篇幅解构了所谓自我及自由意志的概念,却接着像是做了一个智识上的完美后空翻,奇迹似地一跃回到十八世纪,好像演化生物学和大脑科学所有惊人的发现完全不会影响洛克、鲁索和杰佛逊所提出的伦理及政治观念。
然而,等到这些异端科学见解逐渐成为每天使用的科技、日常活动和经济结构,也就不可能再这样两面讨好,我们(或后代)很有可能会需要一套全新的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在这第三个千禧年的初端,自由主义受到的威胁不再是来自“没有自由个人”这种哲学问题,而是来自扎扎实实的科技挑战。我们即将拥有各种极实用的设备、工具和制度,但这些设备、工具和制度并不允许个人自由意志的存在。民主、利伯维尔场和人权这些概念,是否真能在这场洪水中存活下来?
尤瓦尔·赫拉利:新锐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国际畅销书《人类简史》 摄影/王晓东
文章作者

打造医学科技创新策源地、顶尖医学人才培育地、产医融合发展示范地!龚正调研上海交大医学院浦东校区
促进医学创新研究与生物医药产业有机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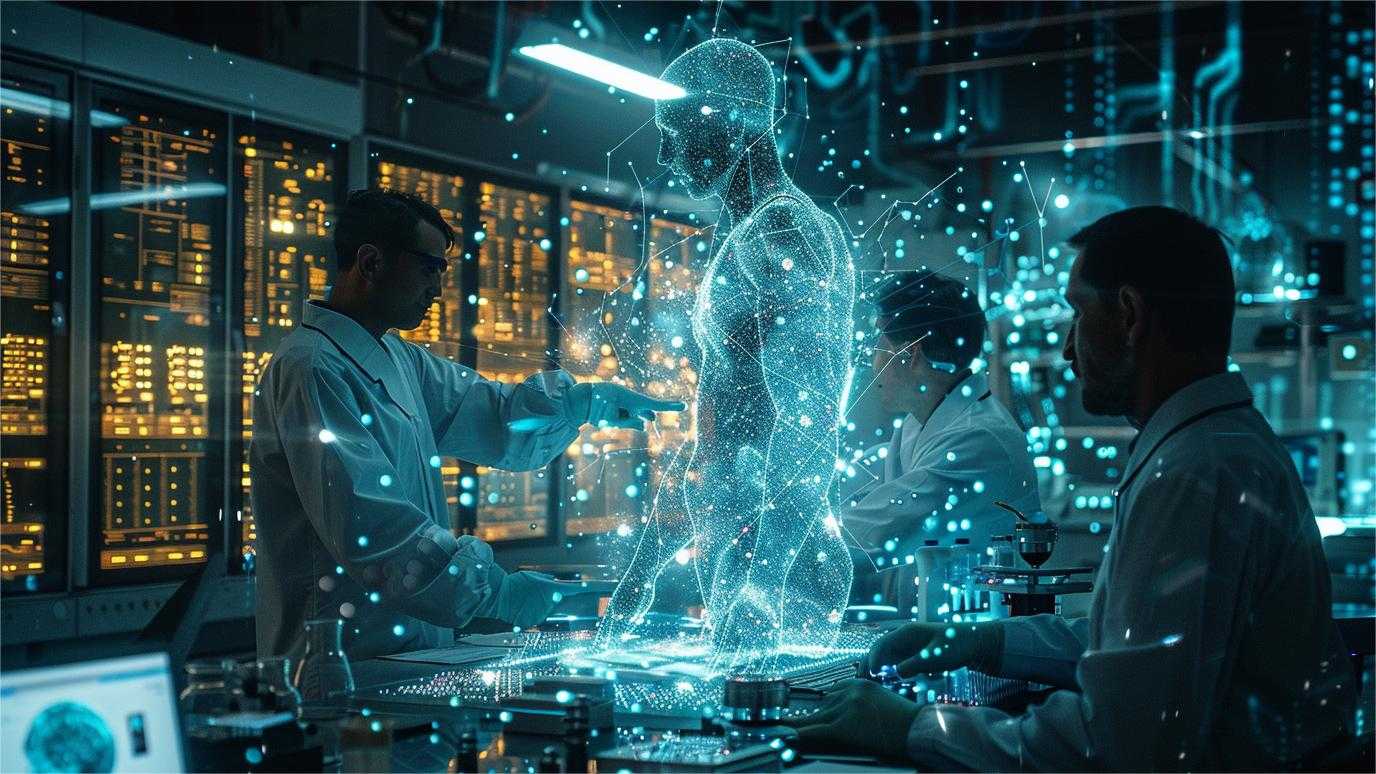
2025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获奖名单在上海公布
在上海发起创设、全球奖金最高的科学奖项之一

科研试剂行业格局生变!跨国巨头“护城河”会被打破吗
越来越多中国的药物研究及开发企业开始转向采购本土公司生产的试剂。但跨国企业发展历史更长,在高端产品的技术方面具有很深的“护城河”。

未来科学大奖十周年庆典在上海盛大启幕,共襄科学盛举
7月8日,未来科学大奖十周年庆典·科学峰会在上海世界会客厅拉开帷幕。

施一公谈AI:自己天天用,叮嘱学生要打好基础并有批判性思维
不管AI也好还是其他领域有多大的进步,最终要有自己批判性的思维,并做好基础研究的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