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无论怎么看,当今社会的所谓“文化”或者说“文明”,确实不再由人完全主导。单个人的智慧与偏好,在打着大数据旗号实则原始的大一统集体思维复兴之下,已被广泛视为无效。上世纪中叶兴起的与社会组织结构意义上的传统彻底断绝关系,并把个人思想从日常生活中解放或者解禁的后现代哲学思潮日渐式微,只因为生存之荒谬的前提下,被激活或者被启蒙的清晰自我意识,无法为哪怕由药物生产出来的幸福作出任何贡献。
基于人类对自己的脑袋相当失望的前提,狂躁的资本膨胀与消费主义丛林法则借了所谓“技术革新”的躯壳卷土重来。人类自己生产的数据,自然而然地在人类的允许之下挟持人类本身的欲望,这时候还谈论幸福当然过时,因为模样貌似幸福感的东西,每天以上亿的级数在人类之中互相传播,连马克•扎克伯格都打不出这过程的明细。
人类面对有些无形的东西相当恐慌,灾难是一种,怪兽是一种,机器是一种,再下来只有所谓人性了。这是为什么科幻这种类型文学,总是充满末世气息,未来之无形,就像再高级的算法也不能预测的股票走势一样,令人心悸。很奇怪,在我们对各种新技术一片欢呼并照单全收纳入生活体系的同时,今天的科幻小说或者影视作品,与阿西莫夫或者奥威尔的年代在情绪上并没有多少区别。近几年受欢迎的《黑镜》《西部世界》或《头号玩家》,讲的都是人类(大众)不自知之下被机器(面目模糊的牵木偶线的幕后大老板)操控的旧道理,从受众反应来看,今天认字极少却读图无数的观众,在视觉审美上十分挑剔,在政治上则比较天真。如果把科幻的成分全部去掉,大部分此类通俗科幻作品也能成立。它们惯用的套路,就是在批判机器强权之黑暗中寻找“人性”的光芒。这无疑是个悖论。倘若人性原本光芒四射,大数据缘何会走上歪路?而倘若,像《西部世界》十分荒唐的剧情所指向的,机器自我意识的最高境界是想“做堂堂正正的人”,那这一切跟阶级上升后又转向剥削一样,是个经典死循环。
最终,我们与机器的羁绊,是实实在在的政治经济问题。科幻小说对科技主导而与人无关的未来之恐惧,很少来自机器本身,而是不得不成为机器的奴隶,为机器日夜打工,被机器腰缠万贯的主人宰割——一个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异化”问题。对此的分析,鲍德里亚式的理论写作无疑有效,只是方法过于浪漫,已经过时。目前时兴的理解问题的方法,全都跟数据分析和调查报告有关。很可惜,近几年声名鹊起的年轻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威廉•戴维斯(William Davies)编辑的这本论文集《经济学科幻小说》(Economic Science Fictions)徒有虚名,连隔靴搔痒都没做到。这本书最大的贡献恐怕是书名——“经济学科幻小说”,而不是更正常的“科幻小说经济学”。戴维斯的立意不仅是分析科幻小说里的经济学,而是要指出“经济学”这一门类或者说“社会经济”本身是部科幻小说。追逐利益从来不是像出拳那么简单,对很多人来说也并非本能,而依靠一套强大的以信念为基础的体系。这种信念,从过去各种形式的上帝,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利益与效率,如今又发展出了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以及各种鲜有当下人类能解释得清楚的名词与缩写——遥指一种能最大程度避免人类缺陷的未来社会。
立意如此之高,《经济学科幻小说》却很悲哀地暴露了如今学术界的虚弱乏力。17篇文章当中领会戴维斯之意的是少数,大多沾染如今欧美学术写作把论点与议题越压越扁的狭隘习惯和意识形态“圈地自萌”的态度,多的是粗浅的文本分析和偏实验性质的乌托邦宣言,少的是能谈得上严肃思想的具备复杂性的内容。其反资本主义的理想主义姿态,也并未从经典左翼理论当中发展出与当下(与大工业时代相比复杂得多的)现实紧密相关的更新。
《经济学科幻小说》由去年自杀的英国著名文化理论家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作序,奠定了其高举大旗反新自由主义的基调。费舍尔生前最著名的概念是“资本主义实在论”,认为西方新自由主义政治结构下,人类已经无法把资本主义的一套现实准则与真正的现实分开。人类理所当然认为逐利是唯一生存的守则,消费是唯一取得幸福的渠道,一切与资本无关的啰嗦情感都是阻碍“发展”的绊脚石。最后费舍尔指引读者(或者说曾经以他为首的一小圈英美学界、文化界人士)从科幻小说的未来叙事当中寻找新的可能。
戴维斯本人的论文延续了他过去两本颇受欢迎的书《新自由主义的限制:权威、主权与竞争的逻辑》和《幸福工业:政府与大公司如何卖掉了我们的福祉》当中的论点:“当我们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讨论乌托邦的命运,最显要的事实是控制论与软件带来的巨大失望(或者更糟)。与社会主义者对非市场化的计算所寄予的希望恰恰相反,电脑成为了金融投资者的最佳武器,以至于机器如今很乐意自顾自交易。与提供一种民主经济的基础或者一种不同的未来当中不同的社会恰恰相反,所谓的‘智慧’基础建设如今在‘监控资本’掌握之下,提取我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数据,以此让任何政治变革更不可能。”戴维斯最后难以免俗地引用弗雷德里克•詹明信著名的“未来考古学”说法,为此书提供了宏大的野心。
无论费舍尔还是戴维斯,基于的现实是以英美为主要背景的。反新自由主义遇到的第一大困境是经典的路线问题,走资还是走社,而如果坚定走社,则是否存在一种“民主社会主义经济”的未来,这种“新民主”,又依靠什么政治经济体系来支持。谢里尔•温特的文章《社会组织的流通货币:钱的未来》,标题十分吸引人,实际只是分析了安德鲁•尼科尔(Andrew Niccol)的科幻电影《时间规划局》(In Time),其中人类的时间被用来当做流通货币,并引来美国大片式的反抗;还有查尔斯•斯特罗斯(Charles Stross)的科幻小说《海王星的沉思》(Neptune’s Brood),这本乌托邦小说显然受了左翼理论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的《债》(Debt: The First Five Thousand Years)影响,有关一场全人类债务大赦。温特并未从中得出什么这两部作品本身没有得出的结论,就好像布莱安•威莱姆斯的文章《自动化经济革命》(同样非常吸引人的标题)也没能从美国早期科幻小说鼻祖罗伯特•海因莱因的小说当中找出什么上世纪60年代没人想到的问题,但威莱姆斯至少提到了社会主义路线的历史问题。苏联和智利是两个在上世纪中叶,计算行业远远谈不上发达的时候,就尝试采用所谓由电脑进行的经济计划的国家。赫鲁晓夫时代,苏联发展过一套电脑系统,意在监控所有经济活动、所有供需关系,以便完全消灭钱的存在。十分乌托邦的想法,与斯特罗斯的债务大赦没有多大区别。欧文•海瑟利的《预制共产主义:大规模生产与苏维埃城市》,从城市规划的角度讲述了一些冷战时期大规模建起的苏维埃小城市住宅区域,在转向市场经济之后并未打破原先大一统规划时代的格局,反而更为大一统,更缺乏公共空间,且更没有个人选择的自由。海瑟利的结论恐怕很多人会赞同,但文章本身论证的过程太过结论预设,很难让人信服。
总的来说,《经济学科幻小说》读起来更像乌托邦宣言而非理论文集。这批大多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相对年轻的学者,可能是过去20年学术界转向文化研究和所谓跨界研究的产物,习惯于通过文本分析输出意识形态,却不注重自身有意义的理论探索。毕竟我们对自己的脑袋已经失望多年,思考无法得到算法的认证,显得十分滑稽。就是这样,人类对科幻的热情不减,对未来的思考也不会停止。几个我个人认为有必要讨论的问题,比如当下通俗科幻类作品中总不会少的所谓“邪恶势力”和对此剧烈反抗的代表“善”的那一对立面,其具体的构成各自代表着怎样的经济意识形态背景,在科幻小说流行起来的过去七八十年里是否经历过剧变;在越来越与人无关的经济系统当中,普通劳动人民、资本家、投机者究竟各在扮演怎样的角色,而大数据集体主义与过往各种形式的集体主义又是否存在本质区别……这些问题,恐怕无法从目前自信程度只能靠乌托邦支撑的学界得到答案,也许这是对人类恶意最深的时代,敌人是谁,真正难以名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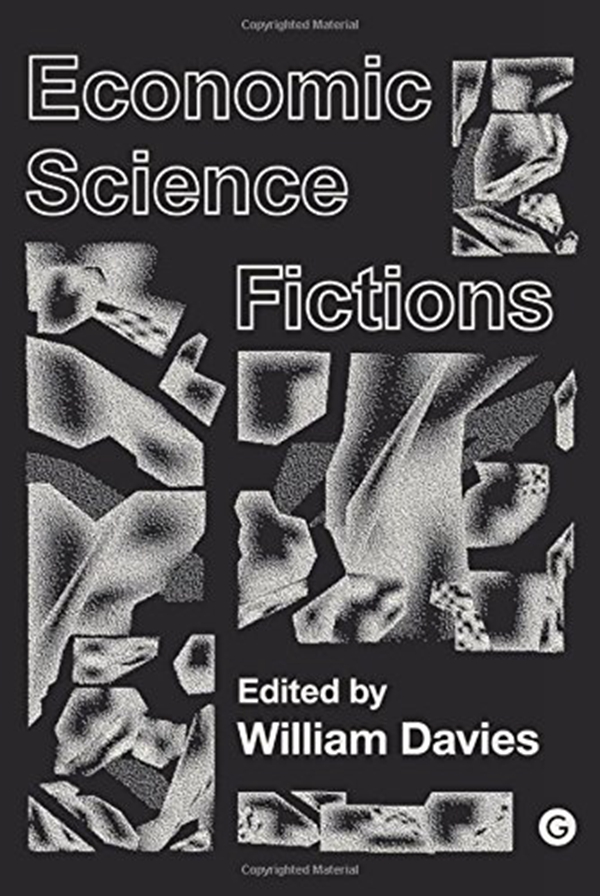
《经济学科幻小说》
(Economic Science Fictions)
威廉•戴维斯(William Davies)主编
Goldsmiths Press 2018年4月版
文章作者

最富女歌手与橄榄球明星将组超级夫妻,“泰勒效应”升级
一对“超级夫妻”所能创造的商业价值,所能带来的跨界营销和联合品牌建设,也将持续放大“泰勒效应”。

从撒哈拉海到人造火山:巨型“地球工程”的利与弊
各种各样的地球工程和技术革命,在成本核算的审视目光下,终究不那么靠谱。

通过关税迫使制造业回流?特朗普“对等关税”的成本与挑战几何|解码特朗普关税
如果对等关税按计划推进,美国乃至全世界可能将付出比上世纪大萧条时期更高的代价。

江小涓:AI发展方向的评判核心标准是什么
由于技术演进及其对经济社会规则的冲击很可能快于相应强监管能力的提升,仅靠政府力量难以有效行动,强监管可能一时跟不上,各种弱规则很可能是治理主力。

朱亦凡:理性选民是一个神话|年度阅读
《理性选民的神话》直到今天仍然非常值得参考,它主要从经济学的视角考察了美国选民票选制度的运行情况,以及人们对这一制度的认识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