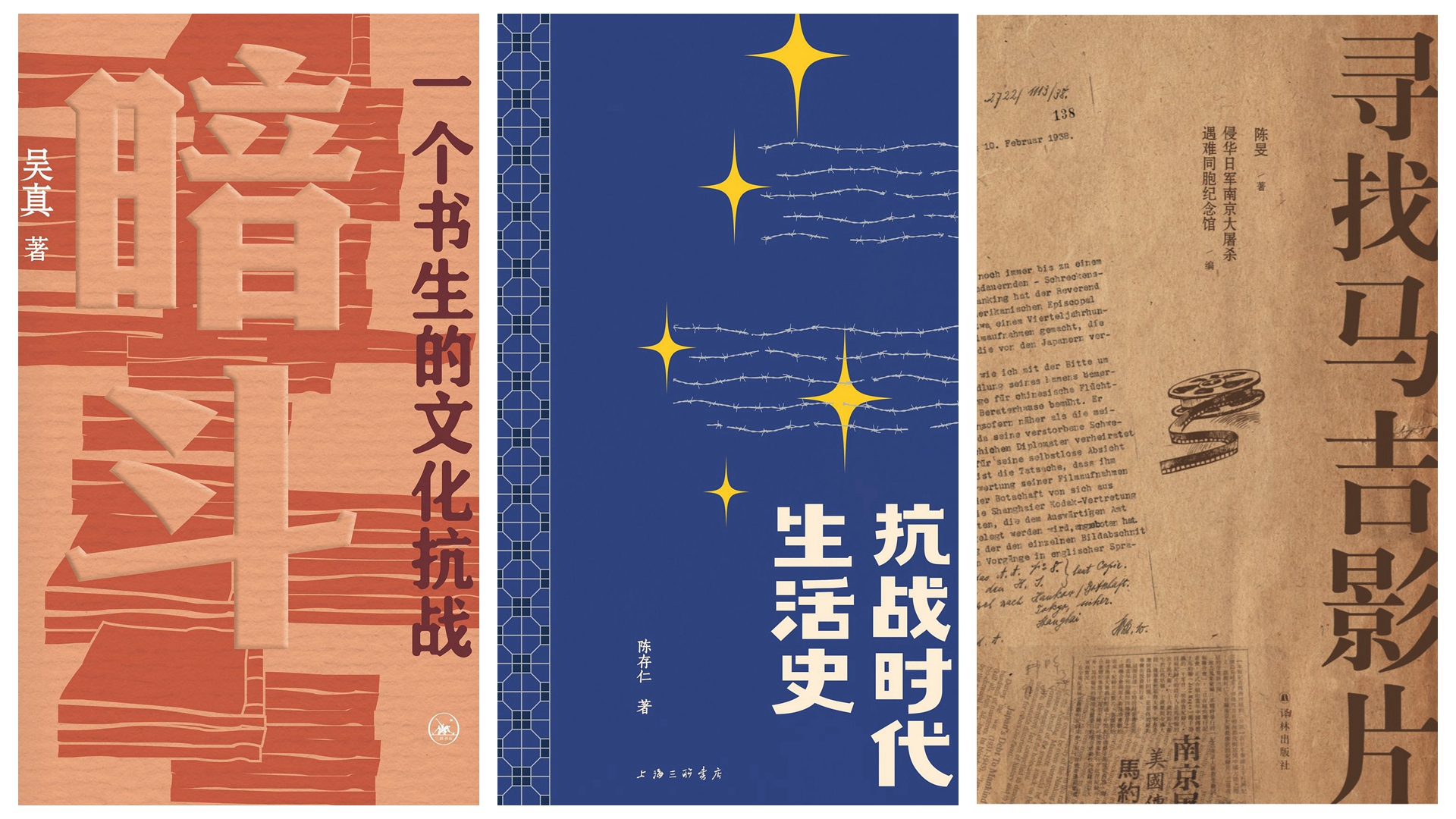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长城是国人最熟悉的文化遗产,但绝大多数人对长城的了解又非常有限,就好像著名的八达岭、慕田峪长城,在绵延万里的长城全程里同样占比极小。
长城最初的功能是军事防御,可以说是一项国防工程,从诸侯国之间的拼杀,到游牧和农耕两大族群的生存空间博弈,再到对丝绸之路这样经济文化通道的保护,以及后来的沿长城贸易流通和民族融合等衍生作用,长城早已不仅仅是一条单纯的防线,两千多年金戈铁马与文化交融,让它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产生深远影响。
连达自1999年起,利用零散时间徒步寻访长城和山西各地古建筑,走遍了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西和陕西一部分的明代长城,并自学绘画进行记录。在新书《不一样的长城》中,他将长城的前世今生娓娓道来,并亲手绘制了书中所有插图。
春节假期,第一财经获得机械工业出版社授权,节选《不一样的长城》以餮读者,这是系列书摘第二篇。


暗门
在长城上的一些隐蔽段落会开设有朝向关外的矮小门洞,即是暗门,其隐秘的特性甚至在长城外侧也很难被发现,很显然不是给大部队和普通人通行的。在处处严防死守的长城上冒着被敌人突袭的风险开设这些门洞绝不寻常,我在河北省和山西省漫长的长城沿线多次遇到过这类暗门,说明这绝不是偶然的个例。
暗门,顾名思义就是暗中通行的、做秘密事情的门,自然不会大张旗鼓地让所有人都知道和使用。这些暗门都特别低矮,在植物浓密的地方基本就被树丛遮挡住了,属于自然掩护。有的门洞甚至要猫着腰才能钻进去,内部或与开设在长城内侧的登城入口一样,进门就爬台阶,并设有门板和很粗的门栓孔,有的简直类似地道的出口。
其实这种暗门是明军探子们悄悄出入关内外的通道,只有足够隐秘,才能不被敌方发觉,也才能有机会去敌人的地盘上刺探情报,甚至干点特种兵的偷袭、骚扰和刺杀之类的特殊行动。如果己方探子大摇大摆地从关口出去,岂不是片刻就被敌军侦知,不要说办事,恐怕转眼间就会被除掉了。
明朝这边秘密潜出边外的通常有急步、健步、尖哨、缉事、通事等类人员,其活动范围也是极广的,据记载,蓟镇的尖哨活动范围最远可达400里到600里。最具传奇色彩的则名为“夜不收”,顾名思义,不受时间限制,可以在外公干直至完成任务为止。这是一项风险极高的差事,史书中也常有夜不收遭敌擒杀的记录。
如成化九年(1473)五月十三日,(夜不收小旗)与同一班夜不收魏克成等九名,前去暖泉山墩爪探,被贼射讫二十七箭……其魏克成等六名,亦被重伤,当即身死。
万历九年(1581)三月初八日,永宁堡沿边沟内突出掩伏窃贼约有十数余骑,撞遇预差出哨夜不收洪阻二、薛祥等二名……躲避不及,被贼掳去……
在史书中有关夜不收最神奇的出现是在土木堡之变后,瓦剌大军挟持被俘的明英宗来到大同,威逼大同守将郭登开城迎接。郭登表面借故拖延时间,晚上派出精干夜不收5人,竟然混入瓦剌大营,与英宗身边的袁彬成功接头,要带英宗先躲入第三地点石佛寺,待瓦剌寻不见人,混乱之后,再择机撤入大同。可惜明英宗胆怯,不敢行动,夜不收只得撤回,否则历史必将被改写。
夜不收是明军的常设编制,在各部队的人员数量也都有相对固定的比例,是重要的情报工作人员,虽然风险大,但起到的作用也是普通军兵无法替代的,他们就是明朝边军的耳朵和眼睛,是随时刺出的尖刀和无孔不入的特工人员,更是在长城内外相对和平时期仍然处于高风险的作战一线的勇士。这些在长城上残存的暗门实际上就是他们传奇经历的真实见证。
戚继光镇守蓟镇时,还制定过以精锐的小股部队利用暗门对靠近边墙的敌人进行突然袭杀的战术,但他“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蒙古根本不敢入寇,大约出暗门突袭的方法也没有机会实施吧。

悬眼
这种防御设施原本应该并不罕见,我曾在一些古城的老照片里见过,可惜现在国内的古城墙大多已经拆除,仍然能够见到的悬眼主要就是在明长城上了。明茅元仪《武备志·城制》载“悬眼,制每垛当中,自城面平为孔,高九寸,约砖三层,砖厚用二层,平面以下,两方砖对中为弯,渐渐下缩……必有此悬眼,贼远则瞭之,垛口铳矢射之。贼近,我兵不出头,以身藏垛下,于悬眼内下视。攻城者虽有铳矢无所施,若到城下,一见无遗,即将矢石铳子火桶掷之,无不可者。”
就是在垛墙底部与城墙顶面相交的位置设一个小孔,下边连接城墙外立面上内凹的半弧形槽。守军蹲在垛墙内无需起身就能通过这个内凹的孔洞看见城墙下敌人的动静,但敌人的弓箭却难以射进来。如果敌人迫近,还能够通过这个孔洞向外发射弓箭和火铳,并投掷陶雷、石雷、铁炸炮之类爆炸性武器,因而也被俗称为雷石口。
悬眼通常由烧制时就已编好顺序的特制砖配件砌成,编号就直接刻在泥坯上,工匠最后按照编号进行组装即可。今天在北京市的古北口到金山岭一线长城的外立面上仍然能看到大批并排而列、充满韵律感的悬眼凹槽。

文字砖
在有些地方的砖城墙上还能够见到文字砖,上面大多写着城砖的烧制时间以及施工部队的名称等。这类文字砖就是明确施工责任制的一种体现,以便城墙如果出现了质量问题,可以按照砖上的记载来追溯责任人。
明长城上所见的文字砖绝大多数是万历年间留下的,这些文字砖大多是将文字印制在砖的窄面上,以下凹的阴文为主,字的四周会加一个矩形框,写时间“万历ⅩⅩ年”和施工队伍“ⅩⅩ营造”等。
这是我在长城上所见过的一些文字砖,大部分都是把修建时间写在前边,如“万历四年(1576)”“万历九年(1581)”“万历十年(1582)”等。之后是修建部队的名字,如“通州营”“宁山营”“天津营”“延绥营”等。还有的文字砖更简单,只写了部队的名称,如“河大营”“沈阳营”等。关于史书上某年修缮了某一地区或某一段长城的记载大多也就是一两句话,所以实地看到的这些文字砖,是对史料的一种有机补充,也使得那些在漫长年代里已经被人们所遗忘的甚至消失了的老地名重新浮出水面,令历史也鲜活起来。而另一个重要信息便是明长城并非如秦、汉、齐、隋等朝代的长城一样,要征发大量民夫参与建设,而主要是由各地的戍边屯垦将士和轮防调动的外来军兵共同修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