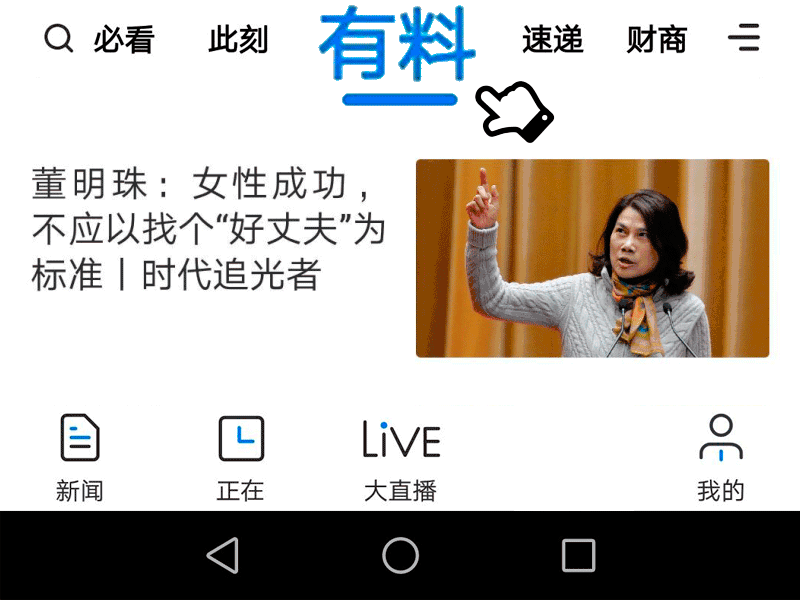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aisd}}
AI生成 免责声明

本期嘉宾
中科新松总裁 杨跞
特约评论员
普华永道工业行业咨询主管合伙人 沈宇峰
精彩看点
“机器人”梦想成真
刘晔:我知道杨总您从小是在科研大院的环境当中长大。小的时候阿童木、变形金刚其实也是您非常喜欢的偶像,那后来加入到中科新松是不是也圆了小时候的“机器人”的梦想?
杨跞:对,我们因为小的时候,我父亲他们所是属于偏化学类的,所以从小科学院那时候研究所早期住的都是一个类似筒子楼,然后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我们家旁边几个邻居都是研究员,都是正研究员,孩子基本上都非常优秀。中国人一直讲,“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难”,对吧?所以那时候就想学这个理工科的内容。这个阿童木也好,或者是所有的机器人,我理解都属于一个,我们以前讲每个男孩可能都会有一个机器人梦想,所以其实这个就代表人对未来创造一个更加像自己的这样一个产品,或者智能化产品的一个追求。
那么从中科新松我们所做的协作机器人来讲,我们现在按照这个七轴的形态来说,全球也只有两个团队有。按照精度来讲,我们现在精度到0.02,也就是头发丝的十分之一左右,那么按照这种方式来讲, 我们精度也是足够高的,这个在技术形态我们目前是领先的。
然后从族谱来讲,因为我们机器人,我们经常希望大家选择的时候就像是有一个菜单化选择,种类比较多,对吧?你觉得谁能帮你,这种可能比较好。那么按照这个族谱来讲,从单双臂、六七轴到人形,包括复合。按照这个族谱架构,我们目前是在行业里面最全的。
在国内协作机器人领域的创新
刘晔:其实在当时的一个国际国内的环境当中,六轴是已经比较领先,而且很多人认为已经够用了。那为什么在2015年,当时我们决定要从七轴开始,而且要推出这样的一个产品,这背后代表了中科新松一种什么样的决策思路?
杨跞: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当时在说,我们要制定自己的研发路线图。我们经过半年的论证,我们当时所做的方向,大家理解的机器人都是越来越像人,但是早期的工业六轴呢,可能更像个机器,所以当时想的第一个,从七轴开始,就是用人的这个胳膊,从手腕往上算是有七个方向,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臂更像人的胳膊一样,更灵活,更加精巧,在复杂环境下更柔性,那所以我们当时开发的产品叫七轴。
那我们内部代码叫七轴,学名很长,叫七自由度多关节冗余协作机器人,那时候还不叫协作,叫冗余机器人。那“协作”这个词儿是到后面才有,到2016年以后才陆陆续续叫起来,我们在2015年参加展会的时候,我们也就是按七轴来叫的。
当时在工博会,我们参展工博会,我印象非常深,我们跟人开玩笑讲,我说这个机器人是新鲜出炉,还热乎着呢,原因在于刚从实验室刚组完,刚跑完,到展会的时候刚连跑不到一周,所以那天拿到这个展会现场的时候,大家压力也很大,项目组压力非常大,很担心没有验证充分的产品在这个展示过程中如果突然出现一些漏洞,怕对这个自信心影响很深,所以他们很担心,一直非常关注。但是我后来也在讲,正是因为一开始底子打得比较好,所以在现场的这一周期间没有任何的故障,等于是经受了所有的这种考验。所以当时我们展这款产品的时候,展馆就我们一台,大家觉得这个很多的质疑,这个有没有意义?等到现在来讲大家都不用再怀疑了,因为这已经被论证为确实是属于机器人发展的一个方向。
沈宇峰:我对原创这一点我觉得特别认同,我觉得这一点能够坚持下来,就代表说这个平台将来的生命力是非常旺盛的。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应用市场,不管是我们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都有大量的场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可能中国的整个市场规模要占到全球将近一半左右,所以你在中国能够生存下来,在中国能够解决那么复杂的应用场景,你在国际市场我觉得应该是很容易可以走出去的。
资本涌入的利弊
刘晔:这些年,其实很多的这个资本在纷纷涌入到机器人这个领域当中, 有一些企业,可能它的产品还没有出来就已经估值几十亿,也融了很多的钱,所以您如何来看待机器人领域当中资本的涌入?
杨跞:那从资本来讲,现在涌入这个行业,快速涌入是一个好事儿。但是我们技术迭代过程中周期很长,那如果资本进来以后追求短期逐利,非常短期,我非常希望今天来了以后,明天我能套现走人,那么尤其是这种游资过重的进入以后,会导致研发出现无序状态,这时候就是说这种复制,这种无效复制如果占比过多,会影响到原创的东西出现。
我们希望做一个2C的产品,我不得已要从2B到2C,因为它这个路径也很长。那如果说是过重的这个资本的冲击引导这个,假如说是不按这个合理的规则来引导,那么其实时间长,你会发现反倒走了一条弯路,让这条路径走得更长。我们欢迎资本进入到这个产业,但是我们希望它更有理性,有它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规则,那么这种情况下,它将真正助力于我们机器人行业的一个大的迭代和升级。
未来的机器人长什么样
刘晔:这两年我们看到很多说哪个国家出现了一个人形机器人,这个机器人长得越来越像人,这是不是代表着机器人越来越厉害?如果不是的话,什么是代表它的这种科技的更高等级呢?
杨跞:我们这么讲,这个长得越来越像人,叫完全的拟人化,不代表这个技术水平的进展,这是两个概念,因为很多时候这个方式可能是叫满足一个噱头,让大家觉得很好奇,很新鲜,但跟技术不挂钩。我们把“机器人”这三个字,我们组成两个词,“机器”和“人”,这个其实代表了机器人的所有产品路线发展的两个流派。
我们其实理解,“人”这个流派不是说要长得跟人一模一样,我们分不出来这是不是人,这个不是这样,而是从它的这个行为方式上,我们叫图灵实验。越来越像人, 就是未来的机器人应该在功能上更像人,而不是说长得更像人。
刘晔:形态上。
杨跞:对,不是有人一样的皮肤,长得像这个概念。而且可能在未来,这个在伦理上会有更多的风险。
刘晔:未来的五到十年,机器人将会在 哪些领域当中代替人工的劳作?您的答案是什么呢?
杨跞:对于大类预测确实很难,但是对于一些肯定能够发生的场景,我们做几个判断:第一个判断,我们说五到十年之内一定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手术机器人,就是确实可以取代外科大夫。为什么这么讲?在一些微创手术,尤其是在一些医美手术过程中,现在更多地在做一些探索,那么这个在十年之内是稳定能看到的。尤其是一些微创疾病,做很好的这种患病后的处理。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在提的是这种工厂里的装配。我们现在在很多的装配过程中仍然是靠机构来做,那五到十年之内一定会出现能够大规模取代人,完成一些既定动作装配的这种产品,我们叫装配工或者搬运工。
沈宇峰:我希望能够在五年或者说至少可能在十年之内,我们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现在今天讲的这个电脑,时至今日,各行各业,你不管干哪一行,你肯定都得有一台电脑,我们一般把它定义成叫基础设施,就是把它定义成这个环节。未来大家都可能很自然的认为说我今天开一个餐馆也好,我做一个酒店也好,或者我开一个这个工作室,我建一个工厂,我都想的是说这个机器人我肯定是要的,那么机器人用来干嘛?就是大家这个认知能够到那样一个状态的话,我觉得这个拐点是真正的到来了。换句话来讲,就是这个渗透已经是完全达成了。
第一财经《中国经营者》出品
编导 康菊霜
责编 朱琳
制片人 蔡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