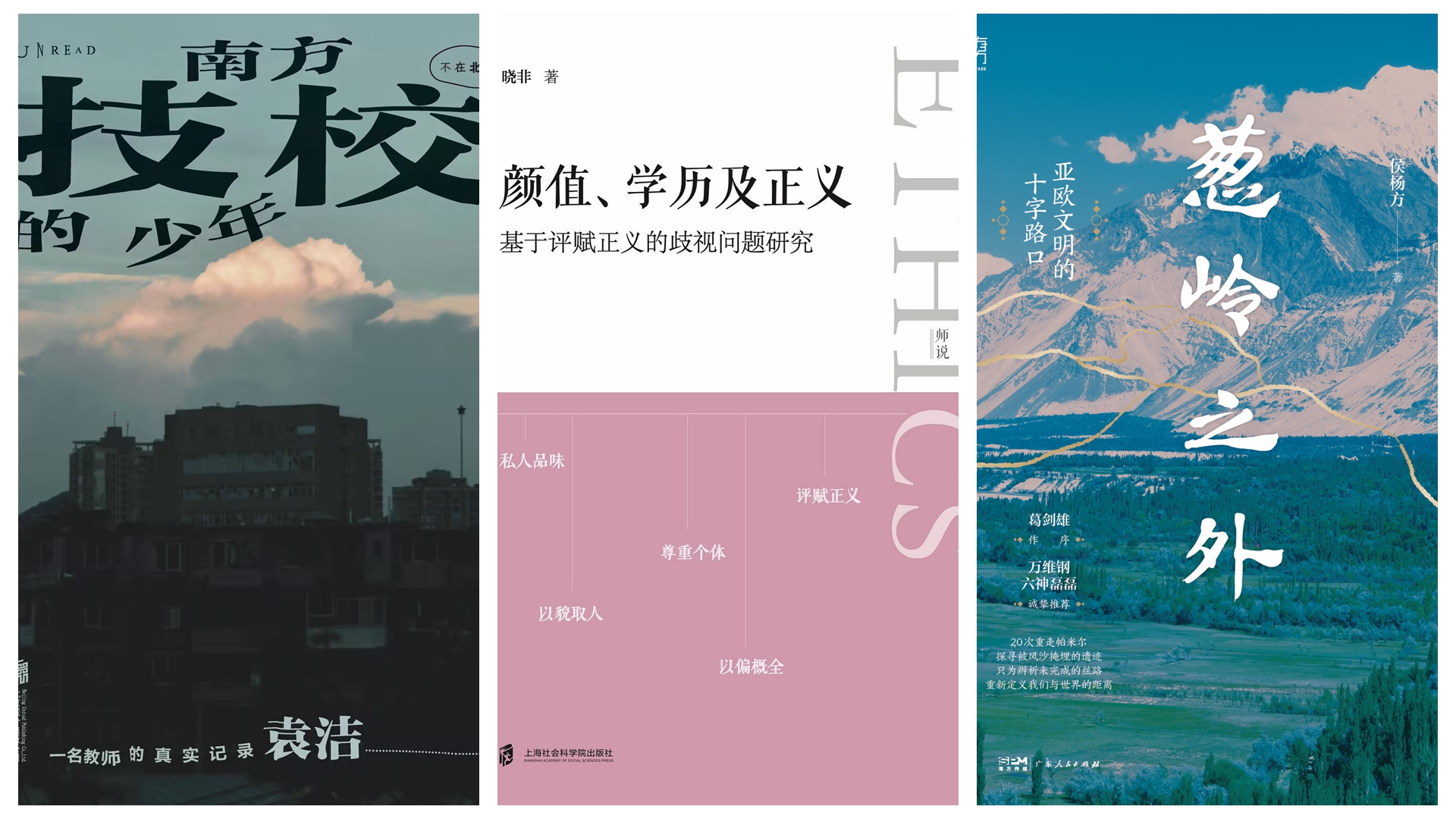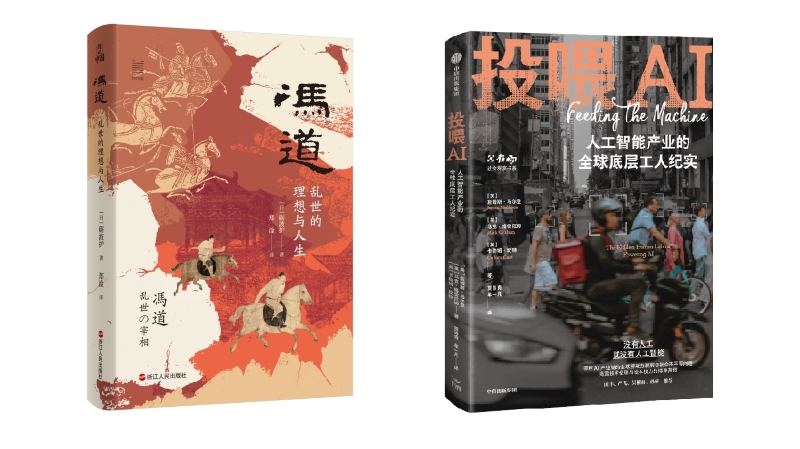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是于赓哲的最新著作,但他不想把这本书看成一部简单的“中国医学史”或者“中国疾病史”,而是希望将疾病和应对疾病的手段作为“读史”的窗口,不仅呈现疾病如何在不经意间改变中国历史,还有古人为了对抗疾病、追求健康与长生所采取的手段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以及对古代中国思想的冲击。
东西方对瘟疫的记忆方式不同
第一财经:有人认为,与黑死病对中世纪欧洲,以及天花等传染病对美洲的影响相比,中国没有哪一次疾病或者瘟疫流行对历史的影响有那么大,所以中国人对瘟疫不是那么“敏感”。你赞同这种说法吗?
于赓哲:疾病对中国历史影响肯定也非常大,比方说,东汉后期那场大瘟疫持续了几代皇帝,明末大鼠疫对历史影响也非常深远。但为什么在历史记录中,中国的这些瘟疫看起来都没有黑死病那么触目惊心呢?这就涉及东西方对历史记忆的方式不同。西方人之所以对黑死病有不可磨灭的印象,主要有两个缘故,一是黑死病确实蔓延了几百年,持续时间长,死亡人数也非常多。更重要的一点是,当时宗教生活在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中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性,而黑死病造成了教会权威的衰落,促进了人们的反思,间接引发了文艺复兴。所以对西方人来说,黑死病是他们的一个历史节点、里程碑,被反复提及、反复强化,直到今天变成一个符号化的东西。
而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历史上可以说是“无疫不在”。也正因为灾害太多,中国人自古心理承受能力也相当强。而且中国的正史记载中,往往把包括瘟疫在内的灾害放到五行志部分记录,在“天人合一”的大框架下,和旱灾、水灾、地震等放一块儿。也就是说,古人认为瘟疫是一种阴阳变化,视之为王朝更替、统治者道德缺失的标志。再加上我们又是一个世俗社会,多次出现的瘟疫也没有造成思想上有什么本质变化。因此在历史记忆当中,我们只知道中华民族曾经有很多灾难,但瘟疫从不会单独拿出来进行强调。
第一财经:你刚才也提到中国是个世俗社会,而历史上西班牙人带去的天花,摧毁了印第安人原有的信念,黑死病同样也动摇了教会对欧洲的统治。为什么除了东汉末年大瘟疫导致道教兴起,整体上中国因疾病而造成的“信仰改变”或者“信仰危机”不多呢?
于赓哲:可以这么说,其实我们的宗教信仰早已变换着自己来应对疾病,中国人才没有因为疾病而怀疑原来的信仰。比方说,道教自诞生之初,就与祛病消灾密切相关。道教为什么要发明长生药、金丹?说白了就是为了迎合人们对消病长生的愿望。佛教原本对今世肉体是不重视的,崇尚来生轮回,这是佛教的根本教义。但是我们看到,佛教传入中国后适应了中国人世俗化的要求,越来越强调消灾避难的作用。观世音崇拜就是一个典型,我们强调他救苦救难,几位菩萨中观世音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也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说,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很灵活,一直有种功利性,也一直服务于人对消灾祛病的要求。毕竟古人应对瘟疫的手段有限,尤其是瘟疫怎么起来?为什么有的人得有的人不得?这些问题往往会给他们带来一些宗教上的思考。在这种情况之下,原本就已经迎合中国人消灾祛病愿望的这些宗教,反倒会借此吸引大量信徒。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再强悍的瘟疫也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感染,这种差异性就带来了各思想流派的思考,像儒家特别强调德行与瘟疫之间的关系,认为有德行、有正气的人就可以避免瘟疫。
东汉和明末瘟疫对历史的影响
第一财经:在你看来,哪场疾病或者瘟疫对中国历史影响是非常大的?
于赓哲:当然是明朝末年的大鼠疫,这种影响不是很多人以为的明朝灭亡导致中国跟西方拉开距离,其实清朝前期也是比较有作为的,中国文化走到后来之所以不可能发生西方那种工业革命,是因为中国根本不具备那种社会结构和思想。但明末鼠疫在新旧王朝交替方面,还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这方面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专门写过一篇论文。当时南北方都有鼠疫,北方尤为严重。这场鼠疫的关键点在于,如果发生在太平时期,虽然也会造成很多人死亡,但不会带来那么严重的后果,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草。但当时明朝已经千疮百孔,一方面内部腐败,官民矛盾尖锐,有农民起义,关外满洲人虎视眈眈。瘟疫之前还暴发了持续多年的旱灾——旱灾和鼠疫往往是前后脚发生,这在历史上是个普遍现象。果然,鼠疫很快就暴发了,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破坏了明朝政府的税源和兵源,而且造成了大范围流民。流民又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所利用,作战时把流民放在前头作为第一波冲锋。这种情况之下,你可以想见,明朝根本经受不起打击,历史进入一个谁都无法解开的死结,于是崇祯皇帝无回天之力,明朝很快就在鼠疫、农民起义军和满洲铁骑三方势力联合作用之下垮台。
第一财经: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哪场疾病或者瘟疫,使得原有的思想观念发生很大改变呢?
于赓哲:东汉末的那场大瘟疫导致了东汉分崩离析,此后出现了一个分裂时代,并且带来了思想方面的巨变,当然,这个巨变肯定赶不上黑死病对欧洲的影响,但也对中国人影响很大。我们可以注意到,魏晋名士那种看淡生死、放浪形骸的生活态度,背后就是瘟疫造成大量死亡而对人生失望。东汉末三国初的人对待生命的态度跟今天截然不同,他们认为人生苦短,有抱负有理想就要尽早实现。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里面说魏晋时出现了“人的觉醒”,其实就是当时的人“看破红尘”,对名教、原有的思想体系失望,这也是人在面对大量死亡时往往会有的心态。前面我讲过,儒家认为有德行、有正气的人就可以避免瘟疫,但当时的“建安七子”在同一年就有好几个死于瘟疫,大家一看天下名士尚且如此,就会想原先这套名教的东西有什么用?于是人生态度发生了剧烈变化,此后要激荡几百年,等隋唐重新统一,国家再也没有发生大瘟疫,于是孔颖达主持编写《五经正义》,儒家就此“收拾旧山河”,重新占据重要思想位置。
疾病在历史研究中被忽视了
第一财经:正如你在书里指出的,朝代灭亡背后有时也有疾病的影响。但很多历史书提到王朝更替,更多是谈朝政腐败、民不聊生、农民起义等人为因素,对瘟疫、疾病这些非人为因素谈得比较少。为什么会这样?
于赓哲:传统史学强调君臣得失,也就是强调人治,唯物史观强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因此疾病这个因素是两头不靠,就容易被忽视。尤其是二战后人类进入一个非常幸福的阶段,不仅大多数人能吃饱饭,人类还有六七十年没遭遇过大危险,就很容易丧失对疾病的警惕。这种情况下,要强调疾病对历史进程影响有多大,说瘟疫在历史上曾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即便把死亡数据放出来,很多人都很难感同身受。对他们来说,那也只不过是一串数字,不会思考瘟疫会带来怎样深层的影响,不仅是经济、政治变化,更重要的是造成了思想和思维模式变化。
但2003年的“非典”,以及至今还没结束的新冠肺炎疫情,某种程度上是在警告人类,还远远没有战胜瘟疫,瘟疫对人类历史影响其实非常大,古代有,现在也有,尤其在你放松警惕的时候,它往往会来恶狠狠的一击。
第一财经:你在书中提出一个观点,“人治社会里,君主个人秉性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确实存在,而疾病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樊树志在《晚明史》中也说,万历皇帝从年轻时奋发有为到后来长期不上朝,一个原因就是身体越来越差。而万历皇帝的所作所为,也为明朝灭亡埋下了种子。这样说来,其实有些非常偶然的因素会左右历史的进程?
于赓哲:是这样的。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是唯物史观,对经济基础很重视,当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毫无疑问是非常合理的。但我们还有必要做一点补充,有时环境、疾病、气候方面的因素,往往也会影响历史发展。而原先历史研究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把所有的历史人物都预先设定为一个理性人,他的一切行为都是有历史规律的。其实不是这样,人有时候会做出一些没规律的事,就像我们谁不干几件后来想着都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们必须注意到历史发展中的这些偶然性。
而且什么叫“人治社会”?人治社会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君主的个人意志占据主导地位,整个社会、整个政治机制当中缺乏对这种非理性行为的纠错。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想见君主的很多因素会左右他的决策,比方说他的世界观,他的受教育程度,他的性格,当然疾病也会影响他,因为疾病直接影响人的心智,我们自己有时候得了病心情就烦躁了,更不要说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再来点相关的影响,比方说吃个丹药,那就会变得脾气暴躁,有一系列疯狂的举动,最后可能会变成政治大事。
所以历史进程非常复杂,就像人性一样,既有大的规律性,就是历史发展方向,又有很多意外,很多分支,一些非规律性的因素。对学者来说也算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因为全部都找得到规律的话,有时也有点索然无趣了。
古代无法走向流行病学研究
第一财经:历史学者余新忠在《瘟疫与人》的译者序中提出一个问题:“魏晋和宋金元时期,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而这几个时期恰好是中国历史上疫病高发期,同时也是欧亚大陆传染病模式动荡调整时期,这是巧合还是有必然联系?若有联系,是瘟疫促成了统一,还是统一阻止了瘟疫?”你怎么看?
于赓哲:恐怕跟统一不统一没有多大关系,关键还是战争。战争会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环境失衡,环境失衡就往往引发瘟疫,然后流民以及军队又变成了传播瘟疫的最佳渠道,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一般来讲战乱往往伴随着瘟疫。
第一财经:你在书中分析了古代无法诞生真正的现代医院的原因。这也是中国即便自古疫病不断,但传统中医始终没有能走向流行病学研究的原因吗?因为即便是控制住清末东北大鼠疫的伍连德,也是在剑桥大学获得的西医博士。
于赓哲:传统的中医对于传染病的机理研究始终是在伤寒、六淫框架内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传染病的病原问题和感染渠道存在认识模糊的地方。但也有认识比较清晰的时候,比如明末大鼠疫当中,医人吴又可在《瘟疫论》中提出,伤寒之外天地间别有一种戾气,而且明确指出这种戾气由口鼻传入,将原先模糊的邪气致病渠道说明确化了,那他极有可能是意识到了那场瘟疫是一场肺鼠疫,而不是腺鼠疫,认识就比较先进。
但话又说回来,不是说某个人有了先进的观念,就立刻能够把它变成全民共识。所以吴又可之后,古代中国对待瘟疫的思想仍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另外,古人还把瘟疫看作是鬼神之病,尤其是民间,老百姓更加相信这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既然对瘟疫缺乏明确认知,治疗预防当然也就缺乏理论支持。
但是这里我必须要强调,请你在报道当中也一定要写出来,中国自古以来通过实践,也有很多行之有效的防止瘟疫的方法。比如说,农业生产当中大量使用人的粪便追肥,带来的意外结果是城市粪便得到及时清理,而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卫生就很差。消灭天花的种痘之术,也是中国人发明的。从先秦开始,我们也建立起隔离制。但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有很多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防止瘟疫的方法,却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手段去推广。换句话说,就是没有诞生出公共卫生机制来。公共卫生机制西方人原来也没有,是19世纪时随着国家近代化完成后在西方建立起来的,这种机制是遏制瘟疫传播的最有效手段。
公共卫生机制跟一般的医疗卫生区别在哪里呢?最主要的特点是,一定要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并且全民参与。但中国古代缺乏这样一个机制,所以很多行之有效的方式都得不到大规模的强制性运用。中国公共卫生机制从清末就已经有了,真正行之有效是从中央苏区根据地开始建立,新中国成立后就变成了全国性的制度,这时公共卫生机制比较健全,发挥的功效也越来越大。

《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
于赓哲 著
中华书局 2021年4月版
如需获得授权请联系第一财经版权部:banquan@yica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