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aisd}}
AI生成 免责声明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随着现代公共卫生的进步,世人普遍乐观地相信人类已一劳永逸地远离了困扰祖祖辈辈的传染病。然而现实是:我们这个星球的角落里还隐藏着无数种病毒,只不过原本可能被封闭在热带雨林和极地冰盖之下,当生态遭到破坏,它们就可能进入到一个联系更趋紧密的全球网络之中,引发一场严重危机。
正因此,微生物学家约书亚·卢米斯在新冠疫情暴发前两年就发出警告:那种认为现代科技已经可以使我们未来免受新流行病威胁的假设“非常危险”,“下一个疾病大流行可能就在眼前”。他在《传染病与人类历史》一书中列出史上最严重的十种流行病,它们都曾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改变了历史走向,我们这个世界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应对这些疫情冲击的结果。
自农业时代以来,这是人类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定居生活固然催生了文明,但稠密人口中暴发传染病的风险几率也随之大增。没人能在一个无菌的真空环境下生活,因而上万年演化的结果,是人体免疫系统每天都会与数千万个病原体做斗争,只不过有了疫苗、抗生素和现代诊断工具,我们现在可以更好地借助技术来增强群体的免疫能力罢了。
在药物和种痘技术出现之前,人们对付传染病几乎就只有最原始的一招:通过隔离来阻断传播。现代卫生检疫制度出现于黑死病时期的意大利,“检疫”的英文quarantine一词就源于拉丁语“40”,因为当时意大利港口为了免受感染,让外来船只接受40天的隔离。由于缺乏临床实践的古老教义无法有效应对这场席卷欧洲的大瘟疫,现代医学应运而生。这是一个永不过时的历史教训:若不是蒙古征服带来“第一个全球化时代”,黑死病本不可能传遍欧亚大陆,造成全世界1/5的人口死亡。越是开放流动,就越是需要有一套公共卫生制度来管理随之而来的风险。

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研究了历史上各种文明形态之后,曾归纳出“挑战-回应模式”,认定所有人类社会都是在回应各种挑战中进步的。如果挑战太大,可能遭致覆灭,但挑战太小又可能难以推动发展,最好的情形就是在承受一定冲击之后脱胎换骨——用尼采的话说,“那些不能杀死我们的,将使我们更强大”。
对传染病医学来说,这其实是常识:每一次传染病的暴发,虽然可能在短期内造成了惨重的伤亡和损失,但只要应对得当,最终实际上是强化了社会机体的免疫力,使我们更好地做好了应对下一次冲击的准备。虽然看着可怕,但事实是没有一种病毒能灭绝人类,因为灭绝宿主并不是其目的,否则它也活不成,而在反复博弈的过程中,公共医学水平也得以大幅提升。
历史一再印证了这一规律:天花催生了种痘术,疫苗由此诞生;疟疾的横行不仅推动了热带医学的发展,还首次证明原生生物会致病,而蚊子是最危险的传播媒介;正是对肺结核病的研究带来了一场抗生素革命;18世纪末黄热病在费城的几度暴发,促使当地官员开始建立永久性检疫医院,确认所有移民“无病”后才能进入城市,这种特殊的传染病医院其实就是方舱医院的雏形。现在人所共知的重症监护病房(ICU),原本是丹麦麻醉师比约·易卜生为了应对1952年哥本哈根毁灭性的脊髓灰质炎流行而创建的,最终却开创了一个全新医护模式,传遍了全世界。
不难看出,每一次进步,其实都是在“老办法”失效之后被逼出来的创新之举,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事后被证明为重大进步的创新,也不是一开始就能得到承认的,相反,遭受误解、忽视有时像是先知的宿命。像这样的事例,可以说比比皆是——
年轻的英国全科医生乔治·伯丁顿在1830年代就提出疗养院有助于肺结核病人康复,但却遭到同行蔑视,直到1854年才被承认为作出了开创性工作;苏格兰医生托马斯·拉塔1832年发明了静脉注射方法,能非常有效地治疗霍乱,然而由于当时大多数医学研究都设计得很差,实施得也不恰当,其结果是这一重大医学技术创新被埋没了60年之久;英国麻醉师约翰·斯诺正确地认识到霍乱流行是通过水源传播的,并牵涉到城市基础设施和地理情况、患者的陈述、天气模式、水流和化学、社会经济等整体问题,但一开始却几乎谁都不相信他;意大利解剖学家菲利波·帕西尼1854年就发现了霍乱弧菌,但数十年里都没能得到注意。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真理最初出现的时候,受到正统观念强大影响的人们往往难以辨别,甚至反倒把创新看作是对原有信条的偏离或错误。也正因此,能勇于开辟新道路的,往往是那些不循规蹈矩的边缘人:伯丁顿提出疗养院设想、拉塔发明静脉注射时都只有三十来岁,发现链霉素的艾伯特·沙茨是个刚进实验室三个月的研究生,提出治疗脊髓灰质炎运动疗法的伊丽莎白·肯尼只是一位自学成才的非专业护士。他们的边缘身份既使他们有“不走寻常路”的勇气,却也更容易遭受现有权威的质疑、指责或无视。
在面对一种陌生的棘手难题时,起初谁也不知道什么办法能奏效,这就需要有一个容错的环境,让人们得以在实践中不断检验。18世纪末美国黄热病肆虐时,一些城市设置了武装路障,以阻止疫区的来客进入,但事实却证明这些阻断措施根本无效,因为这种疾病可以随风传播。在大流感时期,束手无策的医生们用了许多民间偏方来对付,此时几乎所有办法都会拿来一试,但事后证明,这些偏方往好了说是没用,往坏了说就是有毒;还有英国医生尝试放血疗法,尽管这毫无效果,但固守教条的医生不愿意相信自己的方法有误,却认为是自己试得晚了。
更麻烦的是,就算方法乍看是有效的,但连专业人员也不知道那个“度”在哪里。1918年西班牙流感暴发时,阿司匹林几乎被视为万能药,然而由于这种药刚问世,连医生也不知道如何安全地控制剂量,其结果是很多人没死于流感,反倒死于用药过量。当时大量生病的士兵被集中转到战地医院里,然而这些病房拥挤而混乱,非但不能帮助患者康复,反倒成了繁衍疾病的大型培养皿。芝加哥医生詹姆斯·赫里克1919年夏天最早质疑种种治疗流感的做法,认为大多数医生们“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疾病是有自限性的,即它常常能够自愈”。
在医学还很落后的年代里,世人常常以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接受那些自己无能为力的传染病,将之视为神灵降下的惩罚——实际上,即便是现代社会,这种心态仍然时隐时现。1987年,面对艾滋病这一无法治愈的全新绝症,高达43%的美国人认为这是上帝对不道德性行为的惩罚。可想而知,这会引发对患者的歧视,时常还阻碍对治疗实践的探索,但现代医学的发展可能让人倒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随时准备尝试最新的药物或手术,趋于更激进的过度治疗。杰瑞米·布朗在《致命流感》一书中说,美国医疗服务的一条最重要原则便是“过度反应要好于反应不足”,虽然最终未必真正改善患者的状况,但“我们之所以做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能力,否则的话会被视为放弃”。
技术的发展,时常会带来完全意想不到的后果,特别是那些反馈链条很长、逐步显现的后果。二战期间,热带丛林战场上的6万美军死于疟疾,为此人们研发出一种新型杀虫剂滴滴涕(DDT),它确实能非常有效地抑制蚊子和体虱(携带致命的斑疹伤寒)的潜在活性,但直到一代人之后,《寂静的春天》这一环保主义的圣经才让人意识到,这种极难降解的化学物质对生态环境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性影响。同样,抗生素一度被视为治疗细菌的万能药,但正是因为每一次流鼻涕、擦伤和喉咙痛都会先用抗生素治疗,这种长期滥用催生出了对所有已知抗生素都具有抗药性的菌株,这是一个绝对令人恐惧的新变化。
从这一点来说,“那些不能杀死我们的,将使我们更强大”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病毒:人类制造的每一种药品,在不能彻底杀灭病毒的情况下,可能会反过来使得它们进化出适应性更强的毒株。这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博弈远未结束,病毒可以通过基因重组(即所谓“抗原位移”)迅速变异出全新的大流行毒株,且这一变异是随机的,无法事先预测,遑论控制。
既然我们不可能生活在一个无菌环境中,这种风险就将始终伴随着人类,我们确实不可能完全控制所有潜在风险,但又何必做到完全控制?千百年来,人类社会仍然不断进步,甚至可以说,若不是这些传染病带来的挑战,极有可能还未必会出现相应的进步。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尊重自然规律和科学,作为地球生物圈负责任的一员,和所有物种一起更好地在这个日益拥挤的星球上生存下去。

《传染病与人类历史:从文明起源到21世纪》
[美]约书亚·S.卢米斯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2021年5月版
文章作者

专访新加坡学者:猪是尼帕病毒“放大器”,但中国猪群感染风险极低
尼帕病毒“人传人”依然是极小概率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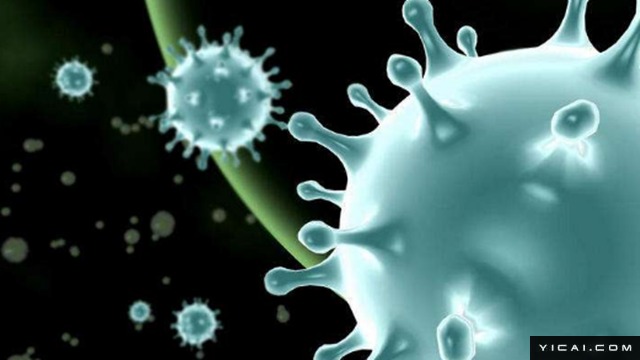
“孟加拉株”尼帕病毒致死率更高、更可能“人传人”,印度疫情有何启示
尼帕病毒不是一个新敌人,而是一个不断进化、寻找机会突破防线的“老对手”。

我国尼帕病毒检测能力如何?张文宏:二代测序检测足够应对
中国已将尼帕病毒纳入重点监测和防控体系,防控重视程度处于较高水平,但实际投入和准备仍面临挑战。

美国新生儿不用接种乙肝疫苗了?专家:疫苗仍是中国肝炎防控重要手段!
目前全球结核病低发的国家中已经有一部分不接种结核病疫苗了,美国提出取消肝炎疫苗的接种是基于美国的慢性乙肝处于很低的流行水平。但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

聚焦防治三大传染病,全球基金在南非G20峰会前筹资113亿美元
目前因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死亡的人数较二十年前已至少减少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