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aisd}}
AI生成 免责声明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上海“宛平南路600号”是一个被人忌讳提起的地址,这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所在地。
不过近年来,人们对心理和精神健康的需求越来越突出,“600号”也随之“出圈”,过去“以看精神科医生为耻”的现象逐渐淡化,心理门诊的需求量也开始激增。

从“谈600号色变”到“门庭若市”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门诊部主任王勇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自5月底以来,医院宛平南路大门口每天进出车辆都会大排长龙,一到周末车辆就更多了,这还是在外地来沪就诊患者减少的情况下。
据王勇介绍,截至7月底,该院的住院和门急诊服务已基本恢复到疫情前70%左右的水平。而针对儿少、老年、睡眠等亚专科服务,以及高端心理治疗等特需服务的需求明显增大,因防控需要等对服务提供模式、新技术应用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王勇管理“600号”门诊部已经有第十个年头了,经历了精神卫生行业在中国的变迁。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过去很多人去精神卫生中心,总怕被误以为是得了“精神病”,还担心会留下记录、进入档案、影响找工作等等。
“大家知道在上海医疗资源是最为丰富的,托熟人看病的现象也很多见,但以往托我看病的人真的不太多。”王勇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即使有也往往像搞’地下工作’,怕被别人知道,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病耻感’作祟,这些担心实际上是毫无必要的。”
据他介绍,这几年来,就诊精神卫生中心的人明显增加了,很多医院的干部和专家也都会找到他,希望解决一些情绪和睡眠方面的问题;也有一些未雨绸缪的家长找他解决孩子的心理问题,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升。
“我们很高兴看到这种变化,心理健康越来越受到公众的重视。”王勇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并不是说来问诊的都是得了病的,但是精神疾病和心理问题近些年发病率日益增高,这会对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
王勇长期研究抑郁障碍和睡眠障碍,从他近期的接诊情况来看,与疫情相关的以下几类的患者明显增多,主要包括:原有疾病恶化或者复发、情绪障碍(例如孤独无助、无聊无趣、悲观绝望、自责自卑、烦躁易怒、兴奋话多等情绪变化)、神经症性障碍(例如疑病症状,焦虑症状、强迫症状等)、睡眠障碍(例如入睡困难、眠浅多梦、早醒、日夜颠倒等睡眠节律紊乱)以及应激障碍等。
“疫情对任何人而言都是一种重大应激事件,尤其是整个社会层面都出现了很多变化,人们因此出现一些心理问题是非常正常的。”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诊疗水平的提升,在大多数情况下,患者是可以通过治疗摆脱病痛的。”

“网红书记”自称有些“凡尔赛”
说到“600号”,就一定要提一个人,他就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书记谢斌。谢斌曾因一句“控制灵魂对自由的渴望”成为“600号网红”。
在今年上海疫情期间,谢斌还说了“隔离期间不要有浪费生命的负疚感”、“即便居家生活也不能潦草”等金句,拉近了心理健康专业服务和普通大众需求之间的距离。
谢斌自毕业后就一直在“600号”任职,虽然是四川人,但他对上海拥有深厚感情。他现在每天工作完最大的放松就是沿着黄浦江西岸夜跑。
疫情持续近三年以来,医务人员的压力很大,不仅要面对患者,还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作为这样一个团队的领导,谢斌称自己有些“凡尔赛”。
“我对我们的员工的心理健康总体上比较’凡尔赛’地充满信心。我们医院传统上也比较重视创造和谐的工作环境,不给人太大的压力。”谢斌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我们的医院文化建设强调整体能力,有这样一种整体心态,我们就可以尽可能地避免’内卷’。”
谢斌称,作为精神心理专业人员,基本上都经过长期的职业训练,能够把工作和生活区分开。“我们也相对更容易觉察自身的情绪等问题,知道很多自我调整的方法,包括在实在走不出来时,主动寻求同行的医生为自己做治疗,甚至也有使用药物治疗的。”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此外,“600号”也有专业的机制来保障本专业人员的心理健康,比如心理咨询和治疗人员有定期开展督导的机制,接受有经验同行的分析和指导,包括处理自身的心理困扰。
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为满足更加多样化对心理需求,目前业内正在开展由资深专家领衔的“长程心理治疗”,尤其如精神分析治疗、动力性家庭治疗等新领域的治疗。
“这是一种新兴的高端服务形态,主要是针对改善自身人格缺陷等心理功能,或者对抑郁等病后心理康复效果要求较高,而且对隐私保护较为重视,自身经济条件又能够支撑较高收费标准的人群进行的。”谢斌向第一财经记者介绍称。
近年来,“600号”出圈,除了热销的月饼、咖啡之外,各种电商平台上都在卖与“600号”相关的文创用品,例如T恤、“出院留念”茶缸等,其中有真有假,但不管如何,“600号”已经成为了上海的一种文化符号,这也是谢斌引以为傲的。他将这种现象归功于6年前医院开始的一波转型。
“2016年起,上海精神卫生服务开始经历向心理健康服务的转型,传统精神病院是这波转型的主力军,也是最坚固的堡垒,社会对我们有了更多需要、也有了更高要求。”谢斌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作为服务提供者,我们过去习惯等病人被五花大绑送上门,习惯以监护人的姿态看待服务对象。现在,我们需要转身站在服务对象的角度来看,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心理健康服务?尤其今天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人群,这些玩抖音、王者荣耀、虚拟现实VR长大的人,我们要试图理解他们眼中的心理健康服务是什么样的。”

新冠的“病耻感”尚未消除
就在8月14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10名医护出发前往三亚抗疫。守护患者和医生的精神健康,一直是“600号”在新冠疫情中担负的重任。
在上海生活回归正常后,谢斌曾多次呼吁,社会应给予新冠康复者关怀和尊重,解除“心理防备”,消除他们的“病耻感”。
在他看来,不仅仅是重大传染病,任何天灾人祸,比如战争、洪水、地震,只要波及范围够广、影响时间够长,都可能在人群中导致心理问题的上升。
“这些重大事件在急性期,一般是由于突然的心理刺激,导致恐慌、焦虑等情绪问题;在慢性期,则主要是环境、日常生活的变化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无望无助等导致的焦虑抑郁甚至烦躁易怒、冲动,有的人可能铤而走险产生自残或暴力攻击等行为。”谢斌说道。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患者体验与智慧医疗部主任陈俊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由于长久以来对精神疾病的歧视和“病耻感”,很多医院为了让老百姓更好理解和接纳,有称之为“心理科”的,也有叫“精神心理科”、“心身科”、“心理咨询科”等等。
“虽然有不同的叫法,但是目的都是为了不要歧视疾病,更不要歧视患者。”陈俊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陈俊在“600号”工作了20多年,早已关注到对于精神障碍患者的歧视问题。他曾在汶川大地震时赴灾区进行灾后心理重建方面的支援;在新冠疫情暴发早期,陈俊还前往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隔离区进行支援;这次上海疫情期间,陈俊支援了上海六院。
丰富的人生经历让他有了比别人更深的思考,尤其是对“歧视”的社会文化现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与其他灾难性事件不同的是,传染性疾病的流行往往会割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导致社会的撕裂。”
陈俊举例称,他在对新冠康复患者的门诊随访中,明显感受到新冠康复者的一些困惑。例如一位之前重症康复的老伯向他倾诉,自从回家之后,邻居见他都躲着,导致他几乎不敢出门,包括家里人也基本不出门,以往融洽的邻里关系在他得病后疏远了。
陈俊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其实这种歧视不仅仅针对病毒和患者,甚至所有与此相关的事物都会受到牵连。”
在应对新冠危机干预的过程中,陈俊曾与一线医护人员并肩战斗,但是当身着“大白”的他真正出现在封闭的隔离病区中,仍然会遭受异样的眼光。“一些人不理解,看到我们这些’大白’甚至会情绪激动,认为我们是’有害’的,可能携带病毒,宁可不需要我们的帮助。”陈俊有些无奈地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他强调,人们要防范两个病毒,一个是新冠病毒,一个是我们心理的病毒。只有从科学的角度去认识疾病,了解疾病,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战胜病毒,迎来疫情后的心理重建。

儿少精神医生仍然稀缺
谢斌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疫情之下的精神健康工作,有很多新情况需要面对。“有些需求并不是真正达到诊断标准的严重问题,求助者可能只是为了换取倾听;再比如,儿童青少年的情绪和行为问题,疫情期间显著增加,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他说道。
由于平时儿少(儿童青少年)精神科服务资源配置相比成年人精神科要少很多,这方面需求大幅度上升,使医院的医护人员、床位都显得格外紧张。谢斌介绍称,“600号”原来仅拥有儿少病房20张床位,今年7月,又在闵行院区新启用了一个34张床位的儿少病房,仍然供不应求。
拥有20多年从业经历的程文红现在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精神科主任。她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当年自己选择精神科从业时,很多大学同学对这门学科还是比较避讳的。
“我从来就觉得这个领域很重要,要让大家理解它。”程文红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近十年我明显感觉到随着社会的进步,互联网发展,年轻人越来越愿意接受。青少年愿意主动接受心理咨询的人、向父母提出来的人数不断有增加,甚至还有小学生,他们对心理健康服务的接纳与开放度明显高于父母辈。”
程文红曾遇到一位老人,反复来医院“打探”,不放心让孙女来心理咨询,怕被学校误解歧视。“最后孩子来就诊后,在学校里开心地告诉同学自己有心理医生了,后来老人又介绍另一位小患者来就诊。”她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从今年的这轮疫情开始以来,她也接到很多家长的咨询,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孩子在居家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家长非常着急,比如由于缺乏学校老师的监督,孩子在家学习学不进去,出现了’学习困难’。”她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近期一些医院近期也开设了类似“学习困难”门诊。对此,程文红表示,学习困难只是一种表象,背后有各种原因。“在临床上,广义的学习困难是指各种精神症状、行为情绪问题等导致学习功能受到影响,狭义指学习技能相关脑功能障碍导致极端偏科等。这是长期存在的临床问题。”她向第一财经记者解释称。
程文红强调,对于学习困难的儿童青少年,需要找出表象背后的症结给予治疗,家长不能对此报有不恰当期望。
像程文红这样的儿童青少年医生在国内极其稀缺。根据2019年《柳叶刀》刊发的一项数据,我国儿少精神科专业医生数量不超过500人!不仅如此,国内的优质儿少精神科医生的确大部分集中在一、二线城市的大三甲医院。
谢斌向第一财经记者解释了合格的儿少精神医生数量如此稀少的原因。他表示:“一是因为儿少精神专科医生历来属于小科而未得到重视与培养,第二是执业大环境不佳,儿少精神医生收入相对其他科室没有竞争力,但工作压力和责任反而更大。”
谢斌援引最新数据称,虽然到目前我国儿少精神科医生已增长到了上千人,但与庞大的需求相比仍是杯水车薪,而且迄今仅有不到6%的精神专科医院开设了有住院病房的儿少精神科,比老年精神科12%的开设比例更低!“专科医院都不开设相关的科室,其他医院就更没有了。”谢斌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即使是上海,也只有儿科医院设有儿保科或儿童心理门诊,但数量非常少,例如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新华医院和交大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上海市儿童医院等。
相关儿童医院人士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儿保科顾名思义偏保健,主要靠门诊,大部分就是咨询下,结合儿童的生长发育情况,没有手术、检查,也不能随便用药,效益偏低。”
谢斌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现在批准用于儿少的特色诊疗项目少,那么开展科研也较为困难,晋升等方面就受到一定限制,职业发展存在天花板。”他强调,作为一种以助人为生的职业,培养职业认同感、职业荣誉感和成就感也极为重要。
据程文红观察,近几年这种现象正在改善,越来越多精神科医生也对儿少科感兴趣,尤其是在一些毕业的医学生中,男生愿意从事儿少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的人也开始多起来。
如需获得授权请联系第一财经版权部:banquan@yicai.com
文章作者

大三甲陷在数据里:AI论文数量飙升、信息科被动转型、半条命交给大厂
三甲医院临床医生的科研重点正从传统药械研究转向真实世界数据、人工智能模型和医疗智能体研究。

国家卫健委:基层医生四年增加54万
县域医共体配备的药品品种数普遍达到了800~1200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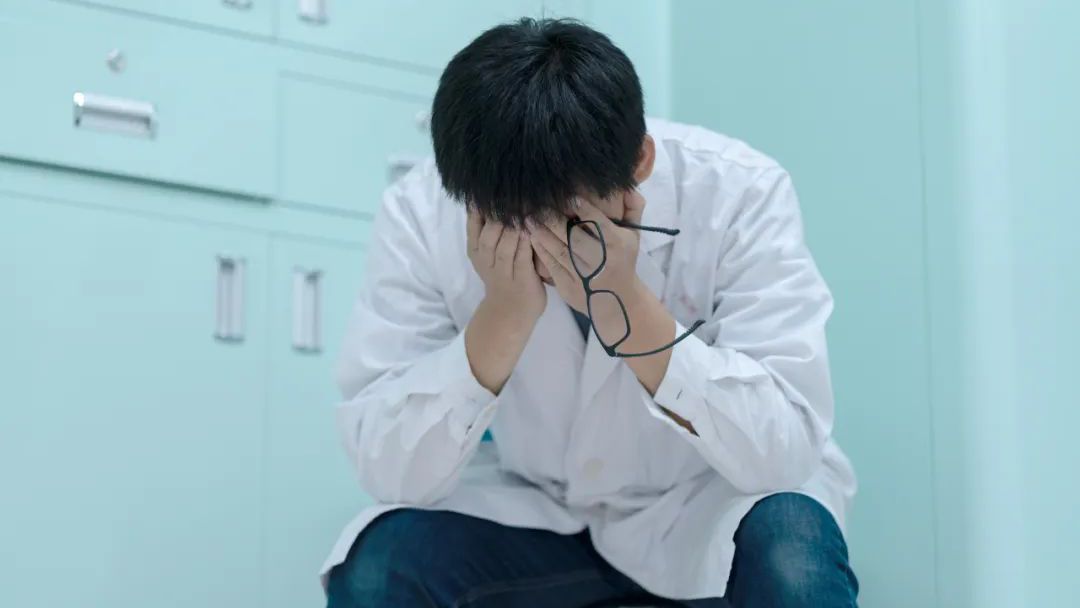
那些放弃晋升的三甲年轻医生
38岁的黄芳在硕士毕业论文接连两次被打回后心态崩溃,她作为三甲医院超声科医生,原本计划通过取得硕士学位申请副高职称,却因科研能力不足面临晋升困境。

当消费遇上AI|人工智能向医疗设备渗透,医疗行业的“寒武纪”要来了?
AI对医疗设备行业的颠覆,正从效率工具转变为“智能协作者”。但医疗AI的发展仍任重道远,大模型仍很难替代医生,目前在数据获取、学习能力、问题的可学习性上依旧存在挑战。

王小川发全员信:聚焦医疗AI,减少多余的动作
王小川发全员信:聚焦医疗AI,减少多余的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