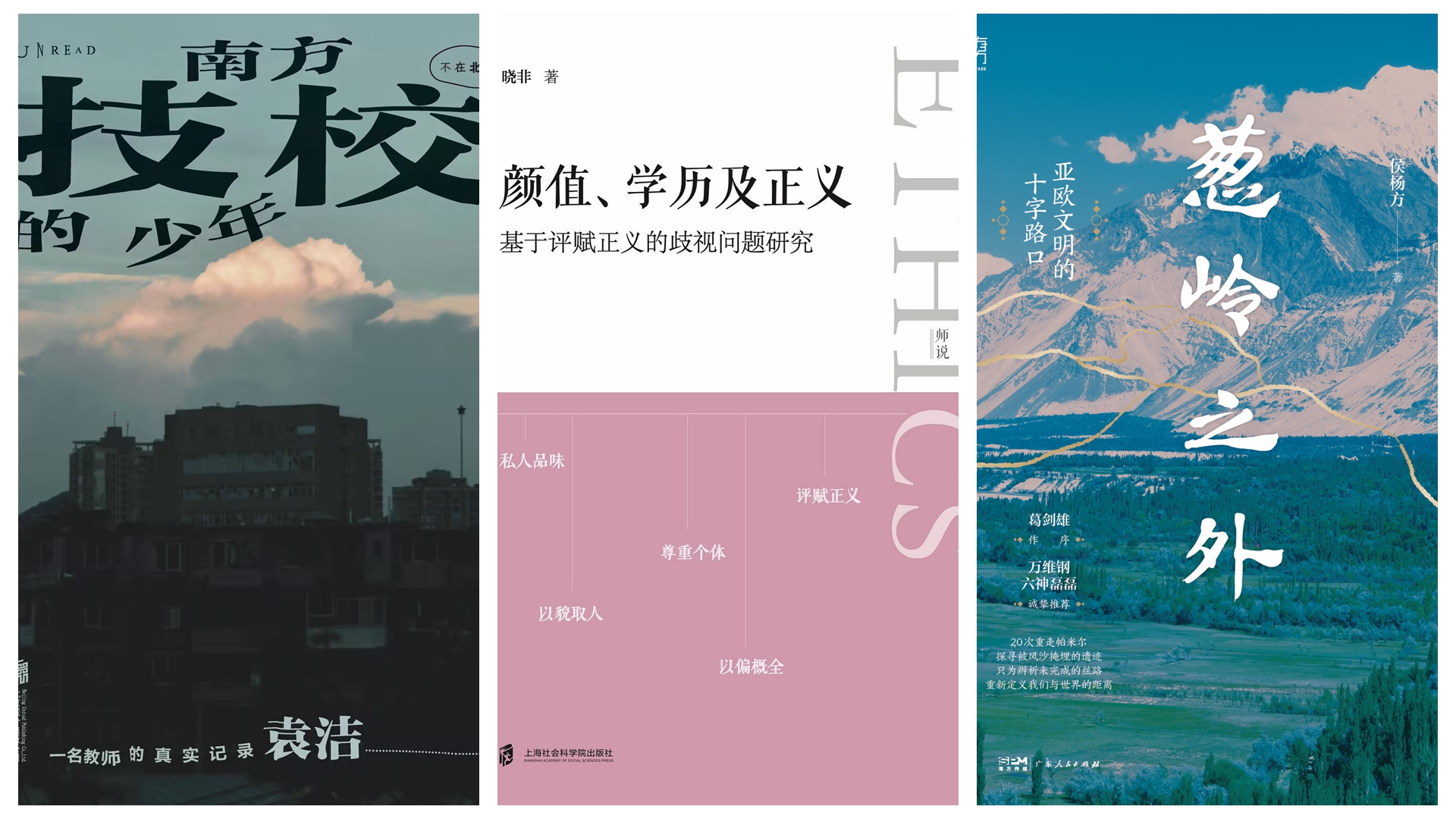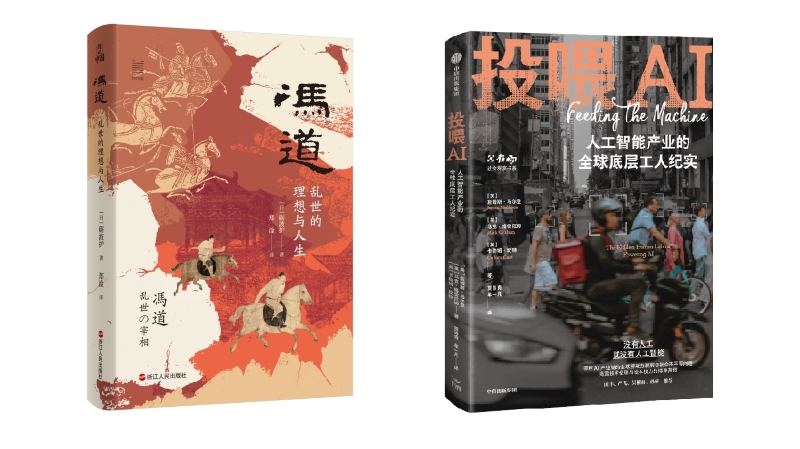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作为拥有200万粉丝的人气大V,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教授张良仁被称为“最会吃的考古学家”。他的短视频活泼接地气,又能结合美食把背后深奥冷僻的考古知识娓娓道来。但少为人知的是,他更重要的目标是筹集考古经费,重新启动他搁浅的外国考古项目。
考古发现大部分与饮食有关
第一财经:我因为《吃的中国史》这本书,第一次知道饮食考古,这算是考古里一个很细分的领域吗?
张良仁:饮食考古是比较新的领域,国内做饮食考古的学者很少,目前就是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王仁湘和我,另外有些硕士、博士,所以我们不好意思大张旗鼓地讲什么饮食考古。植物考古、建筑考古等领域动辄几十号人,我们这个领域的人太少了,这也说明,考古界对饮食还是不够重视。

实际上考古发掘出来的东西大部分都跟饮食有关,只是过去没有从这个角度思考。在考古发现的文物中,最平常、数量最多的是陶片。我当年在二里头遗址和郑州商城遗址都待过,里面发掘出来的陶片能装几辆大卡车。那些陶片都和饮食有关,准确说叫厨房用品,有煮饭的、吃饭的、装水的、装粮食的、洗手的、加工食物的,等等。我后来到甘肃西城驿遗址考古,也发现了大量陶片,起码有5吨以上。
过去考古学界关注陶片的分期断代、器型纹样,很少去琢磨它们作为饮食器具的功能。饮食考古打开了考古的另外一面,让考古更加贴近生活。
第一财经:研究饮食考古的重要性在哪里?或者说,可以为历史做哪些补充?是不是就像《吃的中国史》新书发布会上王仁湘说的,让历史更有滋味?
张良仁:其实不光是让历史更有滋味,还让我们对食物有更深的理解。现在有些人搞什么轻食,仿佛食物成了累赘。其实在中国几千年历史里,每隔几年就有一场灾害,水灾、旱灾、蝗灾,或者战争,有灾就有饥饿。中国人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挨饿的,我小时候在农村,家里大米不够吃,就吃玉米。我们吃饱饭没几十年,一定不要忘记曾经挨的饿。粮食在历朝历代都是头等大事,《齐民要术》里有一句话“食为政首”,就是说粮食是政治的第一要务。
不断变化的中国饮食历史
第一财经:我看书还有你的短视频,印象很深的是,有些饮食或者饮食习惯,几千年来都存在,比如7000年前考古就发现了泡菜罐子,古人吃的小米、小麦、大米,我们现在也吃,秦汉人也喜欢吃动物内脏。是不是在这样一个相对快速变化的时代里,饮食方面某些比较稳定的存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了解历史?
张良仁:饮食跟人的生活一样,也在不断变化,本土饮食在改变,外来食物也在引进。比如中国以前是南边吃水稻,北边吃粟米,后来北方小麦慢慢占据上风。到了北宋,越南的占城稻传来了,占城稻是早稻,这样南方一年可以种两季水稻,水稻产量就上来了,南方的经济地位就上去了。
又比如玉米、红薯、辣椒,等等,都是外来食物。辣椒可以说给中国菜肴带来一场革命,北宋的时候川菜叫川食,但《东京梦华录》里面记载的川食,今天一样都没有,里面还有好多关于面条的记录。我就很好奇,川食里面怎么有好多面条,和今天的川菜比起来变化很大。
第一财经:书里还有一个细节我印象也很深,说从宋代开始铁锅才大量普及。在那之前古人怎么炒菜呢?中国人喜欢蒸菜,就是因为铁锅出现得晚吗?
张良仁:中国人早就蒸馒头蒸饭了。以前用釜煮肉煮菜,还有一种器皿叫甑,也是用来蒸东西的。两汉的时候大家吃羹,就是把肉、菜、小米等放到一起煮。唐朝以后开始有炒菜。古代冶金技术比较落后,所以铁非常难得。铁一开始很昂贵,更多是用来做武器、农具,做炊具应该是宋代以后,因为宋代开始用煤炼铁,铁的产量一下子猛增。铁锅可以出口,在南海一号沉船上面就出土了很多铁锅。当时周边国家和民族还没掌握成熟的冶炼技术,宋朝的铁锅在日本、东南亚都是非常畅销的。
第一财经:以前历史书上说,北魏孝文帝推进汉化政策,促进了民族融合。但是你说,孝文帝能够汉化成功是有社会基础的,从当时饮食就可以看出,南北方民众有了很多融合。是不是饮食考古这个角度,可以帮助我们对这段历史有新的理解?
张良仁:所谓的融合就是各让一步、折中。孝文帝是鲜卑人,有些鲜卑贵族其实是守旧的,孝文帝改革也不是百分之百汉化,但他做了改变,饮食和政治方面都带来一些鲜卑习俗。被北魏统治的汉人吸收、接受了一些鲜卑生活方式,比如吃羊肉、奶酪。这个饮食习俗影响了隋唐,一直到北宋,北方人都喜欢吃羊肉。到了南宋,《武林旧事》记载,临安城里好多人也吃羊肉,每天早上一开城门,就有人赶着羊群入城,然后宰杀、售卖羊肉,他们也吃奶酪。有人说中国人乳糖不耐受,其实不是。只不过明朝以后随着猪肉的普及,大家改吃猪肉为主,生活习俗又一次大改变,才产生乳糖不耐受。
认识世界,认识自己
第一财经:国内大多数考古学家都是在国内接受从本科到博士的教育,你不一样,从北大毕业后去美国读博,学的还是俄罗斯考古。你在书里说“想打开中国公众的眼界”,这句话该怎样理解?
张良仁:这个话是有所指的。我是2000年出国留学的,那时候没有中国学者做外国考古,我可以说是第一个到国外去学外国考古的。因为当时我没有灵感,写不出论文来,一气之下改学了外国考古。到了美国以后,除了我自己学的俄罗斯考古,还听了很多外国考古课程、讲座,希腊考古、印度考古、土耳其考古、埃及考古都听过,真的是开了眼界,天然的就有一种比较,对我有很多好处。
我们天天讲创新,创新灵感从哪儿来?来源之一是传统的文学、哲学、历史等典籍,另一个灵感来源就是外部世界。每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艺术不一样,通过对比就很容易找到灵感。我还经常举例说,好莱坞导演不是只拍美国题材,而是全世界找素材,《花木兰》《功夫熊猫》都是中国题材。我们中国电影导演也可以拍一些欧洲、非洲题材的电影,它们的历史也很丰富,也可以拍拍拿破仑、彼得大帝、亚里士多德或者卢梭这些历史人物。但是从来没有人做过,就是眼界打不开。
其实不光是考古,影视、文学、艺术等方面也是一样,如果大家都打开眼界就不得了,我们的创新能力一下会提高很多。
第一财经:做外国考古,相当于也是从外部世界重新看中国历史吧?
张良仁:2009年我回国后想做外国考古,那时有人不理解,说中国考古还没有研究明白,你怎么能拿中国的钱和人去做外国考古呢?但是我认为,没有什么是能研究明白的,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来。需要有人去研究外国,这样开学术会议的时候,我讲外国考古,你讲中国考古,大家听了才有启发,有很多火花碰撞出来。
我有个口号叫“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要理解、研究中国历史,不能仅仅聚焦中国本国的考古资源和资料。在考古领域,中外是联通的。我们在中国经常会发现罗马的货币、波斯的银币、印度的佛像,等等。要理解、研究这些历史文物,需要了解外国的考古资源和资料。
比如我在伊朗的考古,那个遗址位于丝绸之路上的土丘,发现了一件青花陶。它看起来很像中国的青花瓷,但仔细一看是伊朗当地仿烧的陶器。这说明中国的青花瓷外销到了伊朗,得到了当地人的欢迎,刺激了当地的仿烧产业的繁荣。其实伊朗从唐朝开始就仿烧中国陶瓷,直到12世纪出现一种合成新材料,在伊朗陶瓷史上是新突破。以前我知道陶瓷是中国的外销品,很受欢迎,仅此而已。通过伊朗考古才知道外国人对中国瓷器是如此喜欢,以至于大规模仿烧。
但是现在做外国考古,还面临很大的阻力。看看社科基金就知道了,有一些关于外国研究的项目,都是世界史、世界哲学、外国文学之类,没有外国考古。同时呢,考古还是一门容易跨学科的学科,跟化学、生物、建筑、经济等学科交叉。我的不少研究生在做陶瓷、土壤和经济考古。但是做跨学科研究需要采集样品做实验,很烧钱。我们开玩笑说,考古是“操着理科的心,但是文科的命”,就是拿着文科的钱做着理科的事。
为筹集考古经费做“网红”
第一财经:《吃的历史》新书发布会上,主持人说,你之所以在抖音上做短视频,是想为外国考古筹集经费,真的是这样吗?
张良仁:是的,原先我在俄罗斯、伊朗都有考古项目,疫情以后,项目因为缺乏经费就停顿了。我在俄罗斯的考古项目是为了追寻中国冶金技术的起源。中国的额尔齐斯河,从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发源,在俄罗斯境内汇入鄂毕河。我认为,额尔齐斯河可能是古代人群迁徙与文化传播的通道,因为中国长城沿线那边出土的青铜器,跟商周时期的中原青铜器不一样。中原的青铜器都是鼎、簋之类的青铜容器,也是青铜礼器。但长城沿线的青铜器都是一些小件器物,比如刀、耳环、手镯、斧子、装饰衣服的铜扣等。
我一直怀疑,北方的青铜器冶金技术是从欧亚草原那边传过来的。在俄罗斯的考古现场,我们也发掘出了两处古代的冶金遗址,其中一处遗址出土的铜矿石、铜器,经铅同位素分析,与古代新疆地区的铜矿有着联系。现在我很想恢复这些项目,以后再到希腊、埃及等国家去做些考古。
搞外国考古要培养人才,我已经培养了一些,也需要钱。我们做外国考古发论文,基本上都在外刊,中国还没有世界考古方面的期刊。中国考古界要想在国际上有足够的影响力,需要有自己的期刊,这更是一个大工程,所以我想通过抖音来扩大影响力,有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来帮我圆这个愿望。
第一财经:现在经费筹集得怎么样了?
张良仁: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筹集到。我抖音上粉丝有近200万,要是前几年经费已经很充足了。但是去年到今年,因为大环境的影响,流量变现就不太行。做自媒体收入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广告,一个是流量奖励。我也接了几个广告,收入不多,无法覆盖成本,所以没有盈利。直播带货也可以,但我还没有带。后面再想想如何变现,如果有符合我身份的,关于考古的书,我可以带带。

《吃的中国史》
张良仁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贝贝特 2025年4月版
如需获得授权请联系第一财经版权部:banquan@yica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