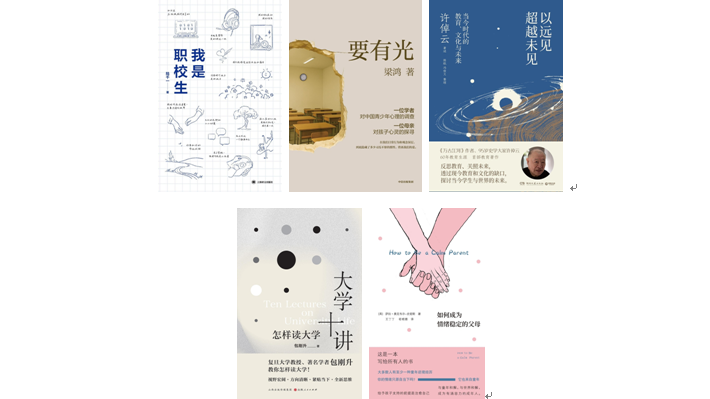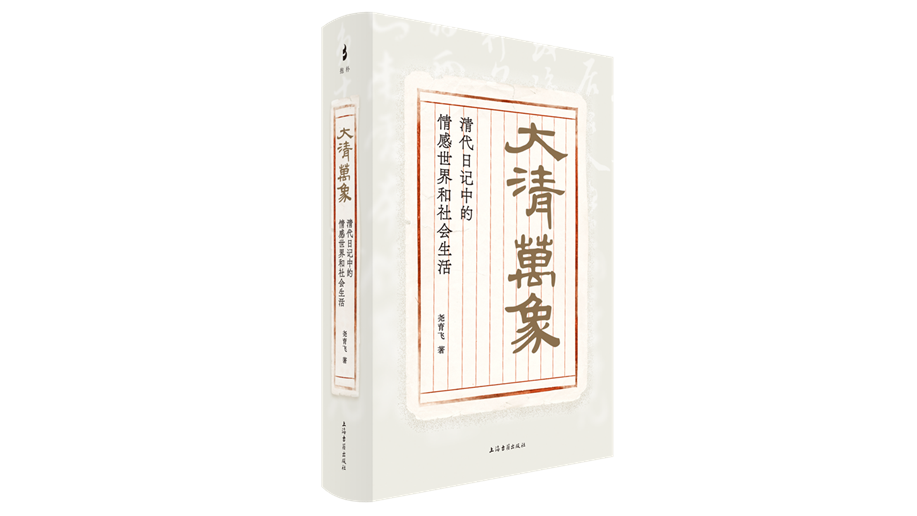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aisd}}
AI生成 免责声明
聆听西蒙·沙玛的演讲,应该是一件很爽的事。以往说起写作者,落笔洋洋万言而开口不能成句的,似乎不新鲜,但西蒙·沙玛却把口才、思维、写作技巧以及热情统一得如此之好,写书动辄50万字起步,在各种节目上亮相并侃侃而谈,时不时在离题中显示自己过人的广博,这难免会使人觉得,参与“同台竞技”的基准线,已经被他拉得太高了。
沙玛是艺术史家,有在各种名校执教的履历,也是一个媒体人,有串联起各种知识、“夹叙夹议”的本领,更有随意抓取信息,将它引到令人意想不到的主题的能力。语言,在沙玛的笔下自带一种“能量”,好像它们能自动滚滚向前,抛开了笨重的“知识储备”;如果你对“神来之笔”有些仰慕,那么一旦进入沙玛的写作,你立刻就知道这是稀松平常。当《伦勃朗的眼睛》中译本在面前翻开,我立刻切身地感到:在艺术史这条“赛道”上,一辆装甲车正隆隆驶来。

伦勃朗,17世纪荷兰大画家,其生涯覆盖了荷兰的黄金时代。在那时名家辈出、蔚为大观的荷兰画坛,伦勃朗脱颖而出,成为名字被后世最多人熟知的一位。沙玛告诉我们,伦勃朗在他的时代,是被一个名叫康斯坦丁·惠更斯的人发现的,此人把他领上了前台。那么惠更斯又是谁呢?
“齐射三十发之后,大炮被迫冷却下来。或许在那时,康斯坦丁·惠更斯才发觉自己听到了响彻炮兵队的夜莺啼叫声。”
这就是全书开篇的第一句话。自从一本名叫《百年孤独》的小说来到这个世界上,大概有不下四位数的作者,想模仿“许多年以后,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面对行刑队的时候,准会想起……”来给自己的作品开头。到了西蒙·沙玛这里,这种技巧已经泛化,已经和其他的文体,特别是那种很讲究夸饰的文体,混杂在了一起。如果对《百年孤独》开篇铺陈的那种种古里古怪的东西有点印象,那么,你将如何看待接下来的这一番描写呢:
“但他(惠更斯)也知道,尽管看上去是一场溃败,但实际上这样的节日游行自有其严格排列的阵仗:第一排是吹笛手和鼓手;随后是鞍甲无可挑剔的马匹;往后是江湖骗子和披着狮皮的人;再往后是纸板做的海豚与龙;最后是古色古香的凯旋车队,由佩戴花环的公牛拉着,有时由骆驼拉着。”
这仅仅是惠更斯想象中的凯旋画面,实际的画面是另外一番,当然,也充满了离奇古怪、五花八门的细节。1629年,荷兰独立战争进入第60个年头,在斯海尔托亨博斯这座被围困的城外,一名英国亲王率军攻打,而惠更斯,是他身边的两名秘书之一(“级别较低的那一个”)。那么伦勃朗呢?西蒙·沙玛在结束了第一段后,突然让伦勃朗出现:
“伦勃朗曾身披盔甲给自己画像。他穿的并非全身套甲。没有人愿意穿那样的成套盔甲,除了骑兵,因为骑兵极易被长矛兵从马肚子底下刺到。但是,伦勃朗会经常性地戴上他那副护喉……”
伦勃朗在莱顿,惠更斯在斯海尔托亨博斯。两个人,像两根藤蔓,顺着自己的道路向前延伸。亲王获胜了,他在荷兰执政,着手打造自己的宫廷,于是惠更斯去为他在荷兰本土物色合适的画家……就这样,他们开始彼此走近,但是走近的过程,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某日,惠更斯来到伦勃朗的画室……”或者“惠更斯先收集了一些伦勃朗的作品,他觉得……”事实上,谁也不知道这个过程是怎样的。西蒙·沙玛也不知道。他是围绕一幅画作,即1629年,23岁的伦勃朗的一幅自画像,做起文章的。画像中的伦勃朗,在一间光线阴暗、陈旧的房间里,正站在画架前看一幅画。
沙玛把它想象成为一幅“自我推销意味的习作”,但是随即发问:这一画作“究竟有多少谦逊的成分”?他告诉我们,伦勃朗想要我们看到此画时,心中想到“不炫耀”,但其实,“这幅画上充满了矫饰……”他的议论在继续,品评随时生发,引用和联系,千丝万缕,唯独清晰的因果联系是找不出来的——到底惠更斯做了什么?他如何最终选择了伦勃朗?他看过这幅自画像吗?
我们都不知道,或者,在得到明确答案之前,我们已经在沙玛那重重叠叠、四处蔓延、随时离题、明显过度的描写、分析和议论中,对获得答案失去了兴趣。
读沙玛,不可能只看他写的内容,而无视他的风格。“哥特式语言”是他的标志性风格,让人在叹为观止的同时也暗暗诟病:怎能如此夸饰?何必如此夸饰?作为艺术史家,沙玛对夸饰风可是太熟悉了,事无巨细,栩栩如生,纤毫毕现,欧洲画家的笔触,在17世纪的荷兰就已达到了如此高的水平,今日的观众,除非专业研究者,在每一家此类绘画扎堆的博物馆里,只有审美疲劳的份儿。2008年,西蒙·沙玛在一次讲座里,说到了J.M.W.透纳。他说,约翰·罗斯金的绘画,就像透纳一样,带着一种“华丽的放纵”。
他说,罗斯金在评价一幅透纳的海景画时,是一位“激情澎湃的指挥家,控制着由拟声词、同音词、典故、突如其来的隐喻组成的交响乐团,文字和它们所描绘的水相互滚动”。作者和他所写的对象之间的鸿沟,在这样的文字面前不断地坍塌。
那么我们发现,沙玛对此种风格,好像也是甘之如饴的。在《伦勃朗的眼睛》的许多段文字里,他描写一幅绘画,都倾尽文字之全力,画作本身有多么繁复,他的文字就亦步亦趋地繁复。不管读者如何审美疲劳,他,沙玛,绝不允许自己放松对画作的责任。在第三章,谈到鲁本斯对瑞士木版画家施蒂默的学习时,沙玛先是连篇累牍地描写施蒂默画中的人物,然后连篇累牍地写了鲁本斯学习施蒂默的风格后,在自己的绘画中刻画的人物的种种特点。他甚至连“梨花木屑在他的凿子前卷起”,这种细节中的细节,都要写入其中——他完全以绘画的方式,想象施蒂默在制作木版画的时候,刻刀与木板之间发生了怎样的物理关系!
不过,沙玛这样写,有一个最为雄浑的理由,那就是:他所钻研的17世纪荷兰画家就是这么做的,他们无穷地观察眼前所见的人,所见的物,无限地探究,探究对象的堂奥,也探究表现这些人和物的方法。只有如此,伦勃朗之类的画家,才能达到如此深刻的程度。视觉是直接的,任何有视力的人,都能瞬间看到被看之物,也正因此,荷兰画家的创作,才应该引起今日之人的充分敬畏:他们对面前一眼可见的场景,下了无穷的功夫去刻画。
而进行这种工作的人,达到了怎样的境界?书中有一番话,初看真的使人昏乱。它说:人们通常认为,伦勃朗不是一个学识渊博、深奥难懂的智者,而是“一位情绪的作曲家,一位激情的演奏家”……但从一开始,他也是一个狡诈的思想家,既是诗人,也是哲人——此时此刻,伦勃朗除了绘画外,无所不能,兼职多到突破了使人疲惫的限度。
无疑,这些描述还是过度的。或许,沙玛在心里抱怨过,文字太容易过度,而绘画却很少有这方面的烦恼。怎么办呢?可伦勃朗给我的感觉,的确是如此丰富啊!诗人、哲人、作曲家、演奏家,这些都能在他的画中看到。我们且随着他洋洋洒洒的笔,来一幅幅领教伦勃朗的全面,且看他怎样一寸一寸地丈量伦勃朗的脚步,对这幅画里的“粗糙”发表成千上万字的分析,对那一次抉择下的背景,做出成千上万字的勾描。当沙玛写到伦勃朗离开莱顿,来到阿姆斯特丹时,他首先做的,是把伦勃朗本人扔在一边,而自己拿起画笔,去亲身当一回伦勃朗——去画出1628年阿姆斯特丹的样子:
“这似乎是一座努力保持着锋芒的城市。这里的磨刀匠们从来不会缺少客户。他们有马刀和长矛,有长戟和阔头枪,有冰刀和镐,有匕首和挖煤铲,有剃刀和手术刀,有锯子和斧头,所有这些东西都需要时刻注意防止钝化和生锈……可是,阿姆斯特丹也不总是直愣愣、尖溜溜的。三条新修的住宅区运河,绅士运河、国王运河和王子运河,像一条三环项链一样,优雅地围绕着老城区的核心地带。而沿着运河建造的那些形制壮美的房屋,顶部的山墙已经放弃了过去阶梯状的样式,而采用钟形的流动曲线,微微带着城堡般的气质……”
沙玛自己先成为伦勃朗。我们把一个“倾囊相授”的某领域研究者称为慷慨之人,可是沙玛的库存怎么也掏不完,因为他是像伦勃朗一样在“写”,穷尽一切地写,在已经写完的地方写出更多,在一个人身上牵引出更多的人。
在这本书中,“眼睛”是一条线索,不论沙玛多么旁逸斜出,他都没有离开过“眼睛”。画眼睛固然是最难的,是决定一个画家成败高低的关键。在23岁的那幅自画像里,伦勃朗在自己肖像脸上眼睛的部位,画了两团黑色。
这是一个谜,也是他被视为智者、思想者的有力理由之一,沙玛继续追踪他各种作品里的眼睛,有的凝视,有的斜睨,有的傲然,有的凄惶……你若没有工夫去观摩文字,就看看书中的那些画,伦勃朗的,还有其他人的,看看画中的眼睛:你便能领悟眼睛和眼神的奥妙无穷,它们容纳了无边的情感,画家得无比郑重地去刻画眼眸,而写作者,不论花费几多文字,都不足以把一双如此描绘出来的眼睛的内涵把握完整。
“毕加索,”沙玛写道,“这位脑洞大开的现代主义画家,他把情感从绘画中剔除,却对伦勃朗——这位每一个笔触都饱含情感的大师充满思念。”这话的语气里不乏挑衅,他想说:亏毕加索还说他欠伦勃朗最多,我只看出来毕加索的背叛。

《伦勃朗的眼睛》
[英]西蒙·沙玛 著
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 2024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