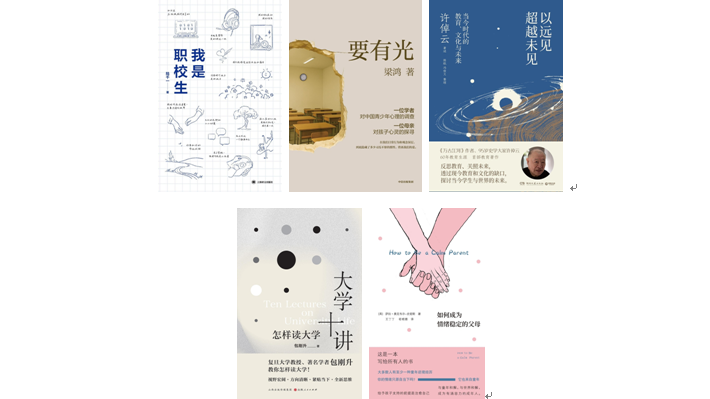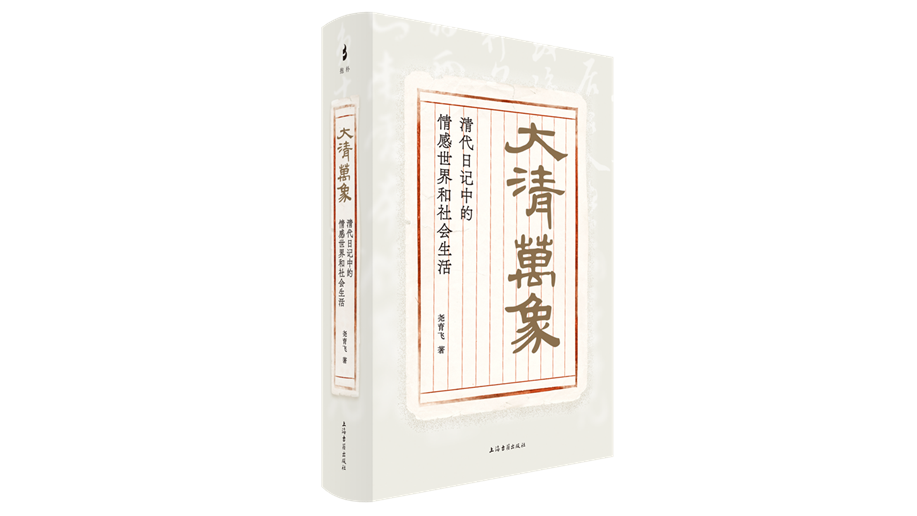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aisd}}
AI生成 免责声明
2017年8月至2018年9月,李昀鋆完成了106次对中国内地丧亲者的访谈,其中44位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人成为她博士论文的研究主体,包括33位女性,11位男性。他们多为独生子女,父/母离世时平均年龄19岁,27位父亲离世,15位母亲离世,有两位是双亲都离世,接受访谈时的平均丧亲时间为5.37年。
他们对李昀鋆坦露了原本深藏的丧亲经历和感受,李昀鋆也通过他们的讲述,了解到哀伤背后一层层复杂的情感表达与家庭关系羁绊,以及传统社会文化观点的种种影响。李昀鋆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又修改整理成新书《与哀伤共处: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
针对这一很少有学者深入研究的领域,第一财经记者与李昀鋆进行了对话。
给对方一个接纳哀伤的空间
第一财经:通过你的研究,我意识到对丧亲者来说,没法“节哀”也很难“顺变”,那应该怎么样真正去安慰丧亲者呢?
李昀鋆:关于安慰的话,有一个大前提,是我们实在是太不知道怎么聊死亡、聊哀伤了,所以我们对死亡和哀伤充满了恐惧。因此,当我们想去安慰一个丧亲者时,第一,不要害怕哀伤,人有喜怒哀乐是正常的,哀伤本来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只是太多时候我们没有见过别人讲自己的哀伤,也害怕别人说起这个话题自己接得不好,会让对方失望或者难过才不谈论。这时你不要害怕,正常地把谈话继续下去,倾听他/她的哀伤,给他/她一个哀伤的空间,这是最重要的。
第二,我们要接纳自己面对哀伤无能为力,因为丧亲者的哀伤会不断出现,我们不是要把对方的哀伤解决掉,千万不要在对话中说,希望倾听之后对方的哀伤少一点,这对丧亲者来说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丧亲者更希望获得一个能接纳自己哀伤的空间。

第三,我们也不一定要对丧亲者说什么,一些非语言性的情感表达,也会让他们接收到你跟他同在的感受。比如他们会一直记得某人来参加了自己父亲的葬礼,在很痛苦的时候陪伴了自己,或者有人约他/她出来吃饭,关心了他/她的情绪,即使那时你没有谈哀伤,但是他们也依然能感受到你的关心。
第四,如果你真的超级在乎这个朋友或者超级有心,可以记下一些特别的日子,比如说父亲节、母亲节、春节,甚至是对方亲人的忌日,提前给他/她发一个信息,关心一下他/她。
“借题发挥”地与家人谈死亡
第一财经:面对重病、死亡、哀伤,很多人想谈却不知道怎么说,所以得知家人患上不治之症后,第一反应是选择隐瞒,怕对方经受不住打击。家人去世后,根据你的访谈,子女和另一位健在的父/母,哪怕都很难受,也不愿正面谈论死亡,彼此都在掩盖情感。你觉得我们应该怎样与家人谈论即将离去的亲人,以及怎样谈论亲人的死亡?
李昀鋆:很多人不敢和老人谈,怕他们接受不了,其实不是这样。香港大学在2007年访问了792名香港华人,做了全港首项跨代死亡态度调查。调查发现,香港三代华人中,年轻人、中年人比老年人更害怕死亡,更逃避谈论有关议题。老年人更可以开放地讨论有关遗嘱、死亡的准备、丧礼安排,等等。
关于和家人谈论死亡,我的建议是:第一,不直接谈论,而是借题发挥,借着一些公众人物的死亡或者是别的情境,和对方谈论他/她对于葬礼的看法、对于重病时是否告知病情真相的看法,从侧面了解亲人对于疾病、死亡的态度和意愿。
我了解到我母亲对死亡的一些态度,也是借由谈论我外公、外婆的时候知道的。我母亲觉得,外公最后在棺材里面是有笑容的,看起来很慈祥,意味着外公安详离去。最后我看到我母亲的遗体时,也很安详,我会觉得稍微有点安慰。
第二,和家人聊死亡时,真的不能有一个“完成任务”的心态,更不能希望一步到位,而是应该通过日常慢慢探索,一步步对话,一步步了解对方的想法,再去做准备。当家人主动提到一些死亡的事情,比如邻居或哪个亲戚去世了,家里怎么安排,他/她可能也是在借题发挥,这时子女不要害怕、忌讳,应该借此跟他/她多聊一些。
我在香港地区非营利组织赆明会实习时,看到一个很感动,也让我学到很多的案例。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她妈妈工作很忙,爸爸是长期照顾她的人,很不幸爸爸得了癌症。她父母没有把这件事情隐藏,而是一点一点告诉小姑娘,做了很多准备:陪伴她了解爸爸的病情、帮助她理解爸爸要离开的事实。这其实也是一个引导孩子明白死亡、准备告别的过程。最后爸爸要火化的时候,小姑娘做了一根手链放在爸爸身边,跟着爸爸一起烧了。
我在小女孩身上看到她的哀伤,谈到爸爸的时候她有很多眼泪,还画了好多跟爸爸相关的象征性的东西,但是她对自己的哀伤处理得很好——她可以表达、可以流泪,也有机会去纪念和告别,这一切都让她的哀伤有出口。对比之下,我接触到另外一个年纪相仿的小男生,他的爸爸也去世了。他母亲完全不愿意跟孩子讨论哀伤,也不愿意跟孩子讨论他对父亲的想念,小男孩的哀伤就变得很痛很压抑——他没有哭,也没有说,但你能感受到,很多遗憾堵塞在心里。
这两个孩子的不同状态让我特别深刻地意识到:如果我们勇敢陪伴家人,一起面对痛苦的部分,家人去世之后,丧亲者可能会适应得更好一点,那份哀伤还是会痛,但他们还会记得亲人活着的时候,有很多快乐的、充满爱的时刻。
等不到最后的道歉怎么办
第一财经:临终关怀里倡导家人临终前应该和他们“四道”人生。但现实生活中,很多原生家庭对子女确实也造成很大的伤害。你的访谈者谈过原生家庭的伤害吗?他们在丧亲后,怎么处理曾有的伤害呢?
李昀鋆:这是个好问题,但我回答不了。我的研究里面有44个人,只有一位姜先生提到原生家庭伤害。他在接受访谈的时候一直说对不起,怕影响了我的数据,因为他跟父亲生前关系紧张且充满冲突,父亲对他限制很多,父亲去世之后,他终于可以自主选择人生了,去哪里读研和工作,都是自主决定。我对姜先生印象很深的是,他很长一段时间的微信头像都是《肖申克的救赎》最后的经典镜头,成功越狱的安迪在雨中张开双臂,迎接自由。
博士论文答辩之前,我当时的男朋友、现在的先生也问了我这个问题。他说,当我们谈论哀伤时,是否忽略了原生家庭中那些破碎、暴力、控制甚至背叛的情感经验?这真的是目前哀伤研究中的一个“空白地带”。幸运的是,赆明会有社工跟我分享过一部分人的感受。
这些子女也经历哀伤,但他们的哀伤很独特。第一,父母离世后,某种关系的压迫与痛苦终止了,他们和姜先生一样有种解放的感觉;第二,他们也会有哀伤,但是不明白为什么竟然会这样痛苦,还要处理自己不能接纳的那份情绪,他们的哀伤变得更复杂;第三,他们要面对一个永远不可能修补关系的结局:那些等待道歉的时刻、期待被拥抱的瞬间,永远不会到来了,对于丧亲者来说是巨大的打击。很多人可能选择压抑自己的情绪,认为时间过去了会好起来,但也可能会爆发,甚至变成代际传承的部分。
对于这样的丧亲者,我的建议是,死亡结束的是对方的生命,而不是这段关系。这段关系无论好坏,依然存在于你的生命中,需要你去面对。你可以去了解为什么自己会有复杂的情绪,而不是把情绪全部糅在心里面。理清这些情绪,也是理清跟去世的亲人的关系,然后接纳自己——即便也许你的结论是:其实我不想跟对方和解,对方再也不会跟我道歉,我可能就是一直恨着他。带着这份恨意,你也可以继续走下去,变得越来越坚强。
“有车有房,父母双亡”?
第一财经:网上曾经有个说法流传得比较广,有些单身女性觉得婚后婆媳矛盾难处,认为找伴侣最理想的状态是“有车有房,父母双亡”。但你的研究又指出,父母介入比较多的婚恋中,有人对丧亲的人有偏见、污名化。两类人虽然都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问题,但是否也折射了某些对丧亲家庭的社会心理?
李昀鋆:以前我做研究的时候发现,丧亲家庭孩子进入婚恋会面临一种偏见:有人会觉得,如果有一方的家人去世,就少了照顾后辈的人。
我最近接受了一个采访,记者拿丧亲身份在婚恋市场的污名化做标题,我去看了一下评论,看完打开了我的新视野——原来丧亲子女还有一个被嫌弃的角度是基因,觉得这样代表着后代的基因不太好。
所以不管是对丧亲家庭的污名化,还是有些人希望“有车有房,父母双亡”,背后有一个相同点,很多人会认为:只有得到家庭的托举,才可能有好的经济资源、养育资源、教育资源。像韩剧《苦尽柑来遇见你》里说的,要不是外婆在海里面游,妈妈在路上跑,女孩最后能在天上飞吗?
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对丧亲家庭各种看法背后的社会心理。
第一,对关系中的控制焦虑。“有车有房,父母双亡”这种说法背后,反映的是年轻女性对男方家庭介入感到焦虑,尤其是在婆媳问题被不断放大的语境中,某些年轻女性将“去除长辈变量”视为掌握关系主控权的理想状态。这并不意味着她们真的希望对方丧亲,而是社会长期将家庭冲突“女性化”“媳妇化”的叙述,让她们感到自己必须为可能出现的婆媳矛盾提前“防御”。
第二,对家庭完整性的幻想性预设。“父母双全”被视为婚恋市场中的加分项,根源在于我们对原生家庭完整性有一种理想化想象,认为那样的伴侣更值得依靠,情绪更稳定,未来也能提供更多育儿和经济支援。但当这种幻想被丧亲打破时,不符合理想模板的人就容易被贴上“心理不稳定”“缺乏支撑”“负担过重”等标签。这就是我在书中指出的“丧亲身份被污名化”的典型机制。
第三,把丧亲等同于风险的社会性误读。有网友将丧亲与“基因有问题”画上等号,这种说法的背后,是一种对不可控风险的极端回避心理,把生老病死这种自然事件妖魔化,并推向个人责任化的方向,比如“是不是你家有遗传病?”“是不是你命不好?”这是对丧亲者的深度污名,也是对死亡议题的集体否认。
总之,在现在的社会文化风气里,对有些人来说,婚姻的选择不再单单是关于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而是要控制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可控因素,再来确定对方是否值得爱、可以托付。
母亲去世对家庭的影响更大
第一财经:你的研究中还提到性别与丧亲的关系。我印象很深的是,如果去世的是妈妈,对年轻子女的情感伤害更大。很多人发现,独自和爸爸相处的时间大大增多,反而会产生对他的陌生感。尤其是大部分爸爸还会再找伴侣,子女和爸爸的关系变得微妙甚至对立。从这些访谈,你怎么看待父亲这个角色在中国家庭中的存在?
李昀鋆:我先澄清一个前提。一开始我也有点假设,因为从经验看,母亲去世好像子女更痛苦。但这次我的44位访谈参与者里,有27位是父亲去世,我的感受是,很多父亲去世后,子女的哀伤也很强烈。所以回到丧亲的源头,就像研究表明的,哀伤本质是和关系有关。
为什么在很多情况下母亲去世对家庭影响更大呢?因为父亲在中国家庭文化里的角色还是蛮固定、僵化的。父亲长期以来被赋予供养者与权威者的角色,负责赚钱养家,关心、陪伴子女的功能给了母亲,父亲“在场”,却没有真的“在身边”,不管情感支持还是陪伴,都是一种缺席状态。
母亲在家庭生活里是情感连接的核心,她是照顾、包容、倾听你的人。因此,一个家庭一旦失去了母亲那样一个中介桥梁,很多年轻子女才意识到,从来没有单独和父亲相处过,以往相处的都是“有母亲在场的父亲”。
父权文化下对男性情绪的压抑,也使得父亲难以与子女共同哀悼。母亲去世后,很多父亲选择沉默或快速恢复,甚至会说“别哭了”“要坚强”。在年轻子女看来,这是一种回避、无情,也加剧了对他的疏离。
后续更加糟糕的是,中国文化里,当一个中老年男性经历了丧偶,身边除了子女,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认为,应该再有一个妻子来照顾自己。他如果很快相亲甚至再婚,对子女来说会出现一种“情感背叛”的感受,不只是失去了母亲,也失去了父亲。这种情况甚至可能影响到有些子女对亲密关系的看法:原来男人是这么不靠谱,我死掉了之后很快就会被替代,那我为什么还要像母亲那样结婚,对家庭奉献一生?我有很多位女性受访对象,都因此没有选择进入婚姻。
有一位访谈对象,他已经40多岁,有自己的家庭,不是年轻的丧亲者,母亲去世对他的影响依然非常大,他甚至保留了陪伴母亲去看病的所有火车票,全部展示给我看。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一个家庭的姓氏其实是母亲的姓氏。”因为他觉得母亲在家庭里扮演的角色实在是太重要了,母亲去世家就散了的感觉会很强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还蛮认同丧亲研究里面的一个说法,一个家人的死亡,对这个家庭来说也是经历死亡。

《与哀伤共处: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
李昀鋆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 2025年3月版
如需获得授权请联系第一财经版权部:banquan@yicai.com